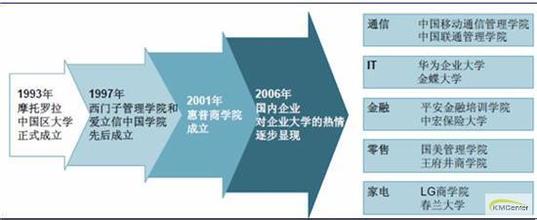企业大学它是个帽子,背后要达到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文/本刊记者 梁莹莹 王喜军
《当代经理人》:国内兴建企业大学掀起了新的潮流,是否有跟风的嫌疑? 王:我不这么看,实际上很多企业大学是着眼未来的,我们经常讲一个思路,就是问题背后的问题。我觉得很多企业大学已经过了盲目跟风的阶段,尤其是做企业大学的往往都是很多行业里的领军者,它没有什么跟风可言,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战略驱动。 虽然很多企业叫企业大学,但是不同的企业背后扣发扳机的动机,是不一样:有标准化的培养产品,培养关键人才的动机(比如餐饮企业),有企业内部知识沉淀的问题(比如房地产企业),有企业统一自己的战略和价值的动机(如多元化的企业),有产品迅速覆盖一线的动机(如汽车企业)。在成立人才标准化培养体系的基础上,很多企业希望把握好变革,老总希望不断把新的东西传递给大家。推动组织结构和管理改善。跟风的,不能说没有,但是我看到过很多企业更多是行业里的领军人物。他是想明白企业大学去做什么了,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当代经理人》:中国的企业大学存在哪些误区或者没有想明白的地方? 王:主要体现在三个地方。 第一,企业大学的校长是谁?现在我们很多企业大学的校长是董事长,但准确来讲,他是个名誉校长。很多企业大学做不好,我们经常听到抱怨说领导不支持。其实不是,领导很支持的。给了你钱,让你干,大学没做好,那你要反思是什么原因?我们缺少好的大学校长和教务人员。 第二,反正我能买各种各样最好的课程,我就可以把企业大学都做得很好。其实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为什么还办企业大学?你把钱都给清华、中欧不就完了吗?他们有学校,有教授,为什么还要费这个劲呢?这里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企业大学能解决那些商学院不能帮你解决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清华、中欧、长江,或者外面咨询公司能帮你解决,你就让他们解决。但是你会发现,在企业内部,有很多的课题是外部人无法帮你解决的。你可以想象一个清华教授,即使他理论水平再高,他也没有空去就一个问题深入一个企业内部,去分析他的前因后果,去帮你解决。所以一定要自己培养自己的讲师,挖掘自己的案例。这个事情,不是投钱就能解决的,教务人员、成果、文化是需要沉淀,需要时间的。 还有一个误区,企业大学有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也有很多事情是自己做不到的。不要让企业大学去做自己不能做的事情,而有的老总恨不得什么事情都让企业大学去做。在这里要想明白一个问题:企业大学究竟能做什么?否则,你什么事情都要企业大学去做,那他会什么都做不好。期望太好,定位也不准。 《当代经理人》:原本企业大学的设置初衷是为企业的战略服务,但是现在有人评价,有的企业大学发展到目前阶段,已经开始影响到了企业本身的战略决策,这种做法是否本末倒置? 王月:我觉得不是本末倒置。一个企业大学,我从来不认为它的价值是对外的,它最大的价值还是对内的,就像心脏一样,没有一个人老是跟别人炫耀,我自己的心是最好看的——心脏的作用是让自己很健康,而不是心自己蹦出来,说你看我长得多漂亮。现在有很多企业大学,是离了位,蹦出来,去给外面做咨询,对外去做培训。我觉得,这不是它本来的使命。如果这样的话,不会长久的。如果企业大学变成一个对外的咨询服务机构,甚至是一个培训机构,那就丧失了它的本来价值,但这个不能怪别人,是沟通的问题——国内的很多企业大学的人,跟高层没有对话能力,理解能力不够,不明白高层为什么要设立企业大学,不知道企业大学要教什么。 《当代经理人》:跟国外顶级的企业大学相比,国内的企业大学认识和理解有哪些差距,以及偏差? 王: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中国和欧美企业大学的成长路径不一样。原因在于整个商业社会本身成长的路径不一样。人家成长了100多年了,企业内部的各个模块都成熟了,外围的生态系统也很成熟,这个时候再往上一层,把自己叫做企业大学的时候,可能会增加一些功能,比如说推动企业文化,推动研发,是这样的一个衍生过程。 而中国的企业大学的发展是倒过来的,先叫了企业大学,然后给它很多的想象空间,它能干这个,能干那个——但是很多事情它还没干。,这是中国人的习惯,做什么事情之前先扣一个很大的帽子。我们中国的企业大学要课没课,要讲师没讲师,这样下去企业大学的路是非常难走的。 《当代经理人》:外部环境对企业大学的发展有哪些影响? 王:外围的财经媒体、管理书籍,包括外围的培训公司对于企业的影响很大。出一本《细节决定成败》,全公司都在研究“细节”。出一本《赢》,全公司都在讲“赢”。当外围的环境很浮躁的时候,很难沉淀出很多东西。 现在的培训机构在全国应该有几万家,但真正能够讲课的老师就几百人。很多老师现在都不应该叫老师了,叫流行歌手是最合适的。他一年要讲300场,而在国外研发一门课程要很久的时间,用好几年的时间把课程设计得很完美,要通过实施部门的认证,去试验,然后让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人去讲课。而中国是老师自己做几张PPT,从网上攒几张图片,靠着自己口才比较好就冲出去了。跟国外成熟的市场环境相比,我们可能更属于一种侏罗纪时代,但是这个成长的过程我觉得应该是很快的。不是在管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中国年”吗?中国1年的发展变化大约相当于印度和新加坡的2年,美国、日本和英国的4年,德国和意大利的5年,法国的6年,瑞士的7年半……
而且我还是看到了一批人真的静下来去思考了,这批人某种意义上集中在企业内部,看到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而且知道没有现成的答案,他们希望在实践中找到答案。 《当代经理人》:现在企业大学跟企业之间的责、权、利是如何区分的?有哪些惯用的模式? 王:我看到的有一种是把企业大学放到HR部分下面,还是培训的一个升级,或者,本身就是一个培训部分;还有把企业大学和HR部门并列起来,但还是会归一个副总裁管;还有的企业大学下边有一个研发和HR部门,但这个比较少见。 从财务上划分,要看企业内部是不是利润中心。非利润中心不考虑结算,利润中心会考虑结算。 《当代经理人》:中小企业要不要建企业大学? 王:其实我觉得中小企业是需要企业大学的,但是他并不需要一个操场或者房子,他并不需要这种形式。而且中小企业的企业大学,还有这么一个特点,可以把研发的工程放进来,不断地用企业大学带来一个前沿的东西,甚至企业大学可以只有一个技术学院。可以不断地解决问题,沉淀知识,让工程师不断看到新的知识。去看到这个行业有新的方向。企业大学它是个帽子,背后要达到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当代经理人》:现在据你们了解,国内大概有多少企业已经建立了企业大学?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大学的比例? 王:我的研究组光找出企业大学的名字,大概有三百个,但是我看了看,划掉了有三分之一,大概有二百多家吧。如果真的要按照成熟起来的标准,那几乎一家也没有。标准放低一点,虽然现在还踢不了英超,但是你看他是个职业球员的样子了,至少能踢个中国联赛了,我看有15%到20%。 《当代经理人》:哪些行业企业在建立企业大学的尝试上表现得比较积极? 王:目前来说,还是比较大的行业,每个行业在中国也就有个两三家,比如中海油、中移动、一汽、宝钢等。另外在快速新兴的行业,往往更多,比如东软、文思、腾讯、百度、俏江南、真功夫等等。 大型企业做企业大学,不单是带来自己的人才垄断,更多是强化自己的企业影响,新型行业则更多是由于它迅速的膨胀。 《当代经理人》:有没有看到一些中国特色的东西? 王:我看到最多的是好多企业大学的牌子挂起来后,一直没有动静。 还有一种,企业大学变成了老板的一种个人“情结”。很多民营企业的老板是草莽出身,自己没读过书,做了企业大学他发现自己的读书情结得到了满足,他当上校长了,虚荣心也得到了满足。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应该把企业大学变成形象工程。企业大学属于心脏,不是外在的东西,不是梳个头型什么的。 还有我看到培训部借此把原来的培训场地盘活。国家是有明文规定,要求不要盖培训中心了,但是国家没说不能盖企业大学啊。大家都知道公司在人才培养上是愿意投钱的,那借这个时机,把公司对人才培养上的很多预算,挪到了那些改造度假村上。 《当代经理人》:那有没有一些中国特色的优点? 王:中国企业接受一种管理方法的速度很快,而且能够自己再次创新,把握住了中国的实际,比如我看到了宝钢人才开发学院的培训,在国外的企业大学是看不到的,因为分工太细了。 第二,在中国很多企业做项目,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老板上来搞了个一百工程,那个老板上来,搞了个二百五工程,肯定是这样的。但是任何一个老板上任,都不会在人才培养这块说我都不做了。中国人真是重视教育。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大学,即使老总不干了,这个项目还可以很好的延续。甚至有些企业,内部很多项目都停掉了,唯独企业大学这个项目还可以得到更多的支持。这一点我觉得跟我们中国传统有关系,无论一把手是谁,对人才的投入,只要公司的财务状况允许,还都是不会太吝惜——如果他真是想做一个企业,而不是做一门生意的话。这是我们最独特的东西。 第三,还有很多企业大学,迅速地意识到,这些东西不能靠外来人。这一点倒逼着很多企业大学的建设者不知不觉自己开发了很多很领先的东西。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一种探索,而不是坐等。 《当代经理人》:那你觉得不错的,能代表中国先进水平的企业大学,能举出几个例子吗? 王:国内的企业,我看到,中移动公司的河南移动和广东移动是我觉得做得很不错的。我确实看到了很多很创新的东西,比如行动学习,高管的讲师开发,情景剧的开发,这些东西在国外也是很流行、非常好玩的。还有比如说,腾讯学院,我觉得马化腾是一个思想非常前沿的人。还有我看到比较好的是阿里学院,他把阿里巴巴很多文化和特殊的东西放在阿里学院。而现在国内一些其他的明星企业大学,没有上述企业大学的那种活力和创新。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