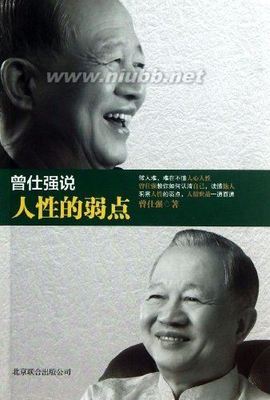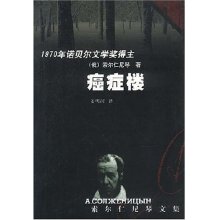翟东升
中国各驻外使馆举办例行的国庆招待会,某些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前往祝贺时不约而同地提出“中国的发展经验”值得他们学习借鉴。放在今天的国际经济力量迅速消长的背景下看,他们的表态显然不仅仅是客气话。那么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有必要阐述“中国的经验”?如何阐述?以何种方式? 有人主张中国还是应该低调韬晦,因为已经有不少美欧学者和政客提出了“中国模式威胁论”,担心中国利用自己的成功与西方争夺国际政治影响力,所以千万不能在国际上谈“中国模式”。我对此不以为然。假如自己闭口不谈,那么话语权就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自西方记者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以来,中国模式已经被西方舆论贴上了“政治专制+市场经济”的标签。这非常不利于塑造和维护中国的国家形象,而且一下子就把中国定义为某种非主流群体的代表,迫使我们不得不去论证和说明自己的良善与无害,由此可见将话语权拱手相让的危害。至于我们如何总结和宣传,我个人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应当涵盖的经验和教训不仅仅是改革开放这30年的,而应当能够涵盖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就、贡献和教训,这对于历史、客观和全面地理解中国的发展轨迹是必要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外实现并巩固了民族解放和大国地位,对内实现了社会整合和政治革命,消除了特权阶级,改造了传统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取得独立之后并未进行深入的政治整合和社会革命,缺课的代价往往需要此后很长时间来支付:它们或者没有走出被外部大国操纵和控制的新殖民命运(一些中东和拉美国家),或者因为传统社会的顽固保留而限制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空间(比如印度),或者在取得经济发展成绩之后由于迟到的政治和社会革命而陷入动荡并将此前的建设成就归零(比如津巴布韦)。新中国的头30年,尽管其错误众多代价巨大,但是至少完成了比较彻底的社会革命,消灭了阶级,并确立了大国地位。没有前30年的国际博弈纵横捭阖,上世纪70年代末的对外开放是不可能的;没有广泛深入的社会改造与整合,此后持续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战略也无法取得今天的效果。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前后的路径差异甚大,但精神内核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一个落后了的古老文明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刮骨疗伤,自强不息,以求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假如我们仅仅将中国经验放在后30年而不是整个60年的框架中去理解,那么我们党乃至整个民族自身的历史、价值、合法性将是断裂的和脆弱的。所以,当我们向发展中国家展示中国的经验时,不能忘了强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比较彻底的民族独立、政治动员和社会整合。事实上,无论是战争、建设还是改革,都离不开社会与政治动员的体制性功能,所以我把政治与社会动员作为中国经验的首要因素。 第二,中国模式应该重在“破”而不是“立”。我们不能去建构一个具体详尽的政策清单,那是推广“华盛顿共识”的人干的事情。我们不妨把力气放在解构而不是建构上。中国的经验(和教训)都在于“不能迷信别人的经验”,在于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因时因地制宜。所以,如果说真的存在一种“中国模式”,那么这种模式的核心内涵就是不相信任何现成“理论”与“模式”。这一点,我们可以借用卡尔·波普尔的哲学来说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手里握着绝对真理和终极答案,所以在面对未知的前途时,我们必须充分地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犯错误,进步的关键是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随时准备接受现实的教育。只有在这种理念的基础上,渐进策略、增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先试点后推广等策略才可能成为现实。毛泽东领导的革命获胜,在哲学上可以归功于他所主张的实事求是;邓小平掌舵的改革成功,仍然是由于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我个人认为堪称中国模式的哲理内核。 第三,中国模式的总结和理论化,应当有利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长期目标的实现,或者至少与之不矛盾。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与“中国模式”相关性而言至少有三个部分:稳定中国和世界主要大国的关系,确保世界市场的开放性,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和威信。出于上述三者的考虑,我们应当强调中国道路的“开放性”特征,当然既指现实意义上的开放,又指哲理意义上的开放。现实意义上的开放主要是指拥抱全球化,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而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哲理意义上的开放是指保持政策与理念的务实与弹性,一定意义上接近卡尔·波普尔说的那种“开放性”,即不试图寻求或者声称掌握绝对真理,而是直面自身理性的有限,更直面客观世界中不确定性的永恒与无处不在。 我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是:靠动员体制来获取民族解放与发展的超强动能,实事求是而不迷信理论,以开放务实的心胸拥抱开放的世界市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