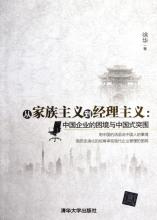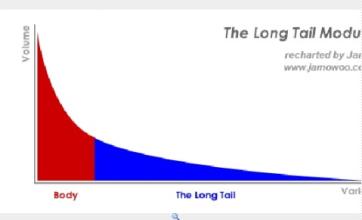王军 CCTV经济半小时节目播出“沪市十公司年报造假悬疑”以后,对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提出挑战的夏草一夜成名。他使我想起了另一位曾经非常著名的“打假人士”王海。 夏草和王海都在“打假”。王海打的是假冒伪劣商品,夏草打的是虚假财务信息。在证券市场上,证券其实就是商品,上市公司发布的各种证券信息就是商品的“说明书”,而各类投资者则是这些商品及其信息的消费者。发布虚假信息如同贩卖伪劣商品,都是欺诈行为。 可是,夏草与王海还是有许多不同。王海出名后,神州大地很快涌现出无数个“王海”:向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商家主张双倍赔偿,一时间成了时髦的消费者维权行动。王海成立专门的“打假公司”后,同样有许多人仿效而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应忘记这位“社会企业家”,他的创造性活动改善了中国社会的制度性事实。 与王海相比,夏草的仿效者在哪里呢?证券打假人士目前似乎只有两位:除夏草之外,另一位是中央财经大学研究员刘姝威女士。2001年,刘姝威对号称中国农业第一股的蓝田股份财务信息的揭露掀起了证券市场的打假风暴。但事隔7年以后,我们才听闻夏草。夏草不仅难觅追随者,其揭假的博客上甚至充斥着反对和漫骂。不仅被质疑的公司和专业机构抵制他,许多投资者也不买他的账——原因是,证券的消费者也是投资者,一旦购买了某支股票,他们至少在持股期间便与上市公司荣辱与共了。 王海的易于复制还与一般伪劣商品打假不需要太多专业知识有关。证券市场的两位打假名人均是会计专家——看起来,仿效夏草是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然而,具有此种专业知识的人士现在不好说多如牛毛,但也肯定不是凤毛麟角。许多在投行工作的人对夏草不屑一顾。有人说,任何一个在投行做过三年项目的人都能作夏草。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是夏草呢? 当然是“利字摆中间”了。券商、机构投资者、会计师、律师等都是上市公司的利益相关人,他们为上市公司服务,上市公司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证券发行上市的成败关系到他们的收入。这种利益分配模式决定了参与其中的专业人士不可能自揭其短,除非他想告别这个行业。况且,他们还有一个自我标榜的美妙说辞:为客户保密是会计师的职业道德。可惜,“为客户保密”常常变成“帮客户造假”,职业道德成了某些人不道德执业的借口,即便世界一流的会计师事务所也未能幸免造假丑闻。

不幸的是,连夏草本人也对会计师的“大义灭亲”抱有幻想。他认为,会计师行业有义务发现和揭发财务造假,并对会计师们没能这样做深表惋惜。在我看来,这一幻想如果实现,会计行业将不复存在。企盼会计师监督信息披露完全是在浪费资源和感情:违法嫌疑人花钱物色的保密员怎么可能铁面无私地揭发违法行为? 王海被群起效法,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激励了打假维权行动。尽管这个激励机制还不够充分,尽管对王海是不是所谓“消费者”、知假买假是否构成受欺诈还存在争议,但惩罚性赔偿的激励作用已初步显现。 围绕证券发行上市形成了利益共享的俱乐部,财务造假具有足够的激励。可是,发现财务造假的激励在哪里呢?法律中不乏打击证券违规行为的行政和刑事手段。但是,这些手段都是公权力机关的专有武器,普通公民不得染指。行政处罚和刑事追诉对违法行为的威慑力取决于公权力机关的执法能力。现在看来,这种能力显然被大大高估了。王海现象的启示是,治理证券欺诈也必须建立发现虚假信息的激励机制,否则夏草不仅没有追随者,其本人的孤军奋战也很难长久维持。 证券法规定了证券发行人及其董事等高管以及专业机构的民事责任,但都不是惩罚性赔偿,与“上市俱乐部”的激励机制不可同日而语。更严重的是,投资者的赔偿诉讼受到极大限制。法院目前只有限受理虚假陈述赔偿案件,对操纵市场和内幕交易的民事诉讼“暂不受理”。投资者针对虚假陈述的起诉还必须以虚假陈述行为已受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判决为前提条件,而且不允许集团诉讼(见最高法院2003年1月发布的《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这些限制使得投资者诉讼维权举步维艰,更谈不上激励会计专家和律师加入打假行列。 要避免证券市场沦为“欺诈竞技场”,就必须给民间打假足够的“奖励”。如果这种“奖励”可以市场化(例如通过惩罚性赔偿和集团诉讼制度),也就是将打假变成一项有利可图的、可规模“经营”的产业,那么,清除证券欺诈的行动就无须政府动员而自动声势浩大了,财务造假等违规行为想逃过广大群众雪亮的眼睛就没那么容易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