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混蛋”:孤客张弓惊鹊燕
文/张弓惊 张弓惊,1971年出生。英语言文学学士。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职研究生。现居北京。 曾供职于陕西华商报集团。任该集团所属的《华商报》(西安)、《新文化报》(长春)、《华商晨报》(沈阳)新闻中心主任、总编辑助理等职。 2001年主持了广州日报报业集团《信息时报》(日报)的成功改版,任副社长、常务副总编辑。 2001年下半年到2002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公益时报》总编辑。 2002年5月至2003年9月,任中国中信集团(北京)中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中信传媒集团)报业投资规划组组长。 2003年至2004年任厦门元通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并任《生活新报》(昆明)执行社长。 2004年到2005年参与创建清华紫光集团紫光传媒有限公司,任紫光传媒公司投资委员会副主任。 2005年9月入股内蒙古太阳晨光传媒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兼《内蒙古晨报》执行社长。并与投资伙伴一起参与北京等地多家传媒项目的投资。 赚钱,是支撑我选择这份职业的重要原因 六月的午后,空气有些燥热,似乎在酝酿一场雨。西安市的一所中学里刚刚结束了一个全体教师会议,会议主题是参加工作满一年的新教师转正的问题。会议刚刚结束,一个激动的男青年(也就是当年的我)闯入了校长办公室,冲到校长面前大声质问:“为什么不给我转正?” 校长是一位50多岁的女同志,她平静地看着我说:“你不是要调走吗?” 我愣了一下,心想她是从哪听说的?心里的愤怒并未平息,我继续说:“是不是我现在写调动申请,你就给我批?” “行,你写我就批。” 盛怒的我匆匆走出校长室,一位老师追上来对我说:“校长已经给你办转正了,她只是吓唬你,想让你以后好好工作。你怎么还当真了?你别这样,我知道你刚到西安工作人生地不熟,你看你调到哪里去?” “不行,我就要调走!” 我首先给《童话世界》编辑部打了一个电话。因为在大学时候就喜欢儿童文学,并写过几部连载童话(有一部还在地方的儿童节目里连续播放过),当时还任该杂志的总策划;该杂志的某位领导曾经认真地跟我谈过调我过去的事情。那边的负责人说:“年轻人你怎么这么着急啊?是不是稍微等一下啊?我们这边好几个人安排不过来啊……” 第二个电话,我打给了《华商报》。当时《华商报》的老总李涛听完只说了一句话:“行,你赶紧写申请吧,就来我们这里。” 那是1995年的夏天,我24岁。在此之前,我是西安44中一名不太称职的英语老师,在此之后,我走上了职业报人的道路。 如果再往前追溯,选择这个职业也许是注定的。 在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喜欢写东西,当时主要是特别爱诗歌,也写散文之类。那时候文学热,我发表一个小豆腐块赚几块钱,这对于来自农村生活拮据的我来说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事。 赚钱,一直是支撑我选择这份职业的重要原因。有人说做新闻是为了理想,这种东西当然有,但鼓励我有勇气一直做下去的,还是赚钱。连我爱人都说我,骨子里是很俗气的。 没办法,小时候的经历就决定了我注定是要走市场化道路的。从前我们家的生活非常艰辛,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年年有人生病住院,一家人永远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 到了大学,我除了自己的专业英语还在好好学之外,其余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赚钱上。那时写文章赚稿费,比当家教赚钱更容易。别人做家教一个月能赚几十块钱,我写文章一个月就能赚到一两百块钱。当时《当代青年》的固定栏目每期都用我的稿子;稿费比较高的《女友》杂志也曾经登过我的稿子。 大学毕业后,我和我爱人(也就是当时的女朋友)被分配到西安中学里当老师,但是需要交6000块钱的“进城费”。此时我上学时赚的钱都折腾完了,这6000块钱全是借的。我刚毕业一个月工资才280元,我和爱人商量,等还完这些钱再结婚。 那一年,我一个人干了八份工作,其中就包括在西安市委宣传部机关杂志《西安宣传》做编辑,以及做《华商报》的特约记者。 因为在西安市委宣传部兼职,他们给我发了一个工作证,我拿着这个工作证到哪里都可以去调查。我就拿着这个工作证去采访各个地方,回来给《华商报》写深度报道,一写写好几个版。 急着挣钱啊。我的兼职几乎囊括了所有我能够找到的挣钱的职位。不到一年,6000块钱全部还完了,但我的教师工作却走到了尽头。我知道不能怪校长,我的确是个不称职的老师,这一年从没给学生好好批改过作业。也许从另一个角度,她的确是想成全我;客观上也确实成全了我。 当我把调动申请拿到教育局的时候,教育局又让交三千块钱,我又打电话给《华商报》,李涛什么也没说,直接从他私人的钱包给我拿了钱。 如果说我的传媒从业经历要感谢什么人,第一个就是李涛,因为是他,把我从学校“买”出去了。 西安·北京·沈阳:亲历《华商报》的转型和腾飞 到了《华商报》,我着手组建记者部,招了好多记者,直接做了主任。直到现在,《华商报》好多干部都是我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当时一些记者最初连新闻是什么都不知道,几乎要我手把手地教。 在《华商报》,我精力充沛,喜欢干活,当时《华商报》一个星期出四个版,有三个版的内容是我自己采写的;我脾气不好,如果弄的东西不好我就爱骂人,别人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我性格比较野,跟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人交往比较多,甚至因为搞社会新闻跟公检法的很多人都成为了哥们。实际上,我也觉得奇怪,我这些年脾气并没有变好,但是一路走来却一直没有缺过朋友。 当时《华商报》出了一点特别的状况,总编李涛也被停职了。此时的《华商报》群龙无首,大家人心比较浮动。我跟编辑部主任老搞不到一块去,矛盾激烈的时候,我曾当着副社长的面一脚把编辑部主任从总编室里踹出去了……在《华商报》内忧外患的当口,我被当时的社长李大灿安排来北京创办《华商报》北京记者站。我就这样来了北京,住在了北京安定门外的京宝花园,地坛西门的正对面。现在有时候路过那里,还是特别亲。 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但是,因为是属于被“流放”,我根本没有心思跟这个祖国的心脏、古老的文化中心亲近。我一到北京,就一头扎进了采访中,既然是《华商报》,那就多做经济的稿子。我因为几个同学在北京,就通过他们介绍,接触了一大批经济学家。当时好像很多有名的经济学家都是从陕西出来的,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张军扩、北大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人民大学的李义平、当时国资委研究中心的魏杰等等,我打听到地址电话,直接骑着自行车就去了。从安定门骑自行车到北大,我一路不带喘口气。认真采访,然后回来就熬夜写稿子,都是“大篇幅”。还有就是请这些教授们的一些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到记者站开研讨会。我把《华商报》北京记者站简直办成了一个财经俱乐部了。 现在想想,实际上那时我就跟那些经济学家在一起聊西部大开发的话题,比中央后来的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提出都早;也聊企业上市等一些很专业的问题。记得当时与宋国青在北大三角地的食堂,一边喝啤酒一边聊“游资问题”,还争得脸红脖子粗。当时我实际上不懂经济,但经济学家懂。有一次采访香港来的一个人,他讲买壳上市,我就写买壳上市,回去以后《华商报》头版发了,甚至惊动了证监会的人打电话给华商报,要求报材料过去。 本来北京搞记者站,是作为华商集团在北京的公关办事处,也没指望写稿子。我写了稿子,社长兼华圣集团的董事长李大灿就让我把文章直接传给他的秘书,结果我每周几乎都会把他的传真纸都用光了。 当时我一个外交部工作的同学跟我说互联网好,我就弄了一台电脑,学习上网。DOS状态下进入NETSCAPE系统。当时的互联网上中文材料不多,有很多英文的财经类的信息。我恰好本科学的是英文。所以,除了那些采写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我还不断地给《华商报》发互联网上的经济信息。结果《华商报》几乎成了北京版了,从头到尾都是北京站传过去的消息。 我来北京快三个月的时候,我接到了社长的电话。那时社长要到长春办事,在北京转机,他让我去飞机场见他,说有几句话要跟我说。我跟社长在机场的停车场里见面了,我们坐在车里,他跟我说:“张弓惊,你这几个月干得好!《三秦都市报》有一个人叫张富汉,我想请他到咱们报社来。他现在要去成都见席文举,我明天也过去。你今天先去成都,跟张富汉见见,聊一聊。”我问:“我要不要先回西安?”他说:“你不要回西安,直接去成都吧!”我没来得及回去北京的住所,直接坐上飞机到了成都,见了张富汉和席文举。 那次的成都之行改变了《华商报》的命运。我们参观了《华西都市报》,也和张聊得很投机,我对他的想法也比较认同。张之所以请李大灿社长到成都,是因为他就想让大灿知道,我们《华商报》要做就做成《华西都市报》那样的报纸。第二天,社长到了。也就是那次成都之行,让李大灿终于下定决心,让张富汉到《华商报》任总编辑,报社实行总编辑负责制,全面主持工作。《华商报》的腾飞也就从这次成都之行开始。 而我,就这样直接从成都回到西安。直到《华商报》在张富汉的领导下改版后半年,我才有机会回到北京取行李。结果,我的行李早就被丢的不知去向了。我存在安定门地铁站的自行车,也找不见了…… 在《华商报》报系里,我的最高职位是总编助理。记得那次在成都的时候,我偶然给张富汉讲互联网,《华西都市报》正好也有互联网。张就对我说:“互联网这么好,回去咱们也搞!”结果,一回西安,张让我做了新闻信息中心主任。 那时的《华商报》除了记者采访的新闻,其他新闻就都在我这儿出。一期八个版,有五个版是从我们部门出来的。这确实能锻炼人,现在《华商报》的很多干部都是出于我的部门。我这人比较喜欢揽事,一揽揽一堆,然后张富汉就把它一个个剥开。 张富汉说我的能量比较大,因为我干啥就一门心思想干好;不懂就学,就琢磨。我甚至当了一阵子《华商报》技术部的主任。现在《华商报》的域名还是我当时申请的,包括《华商报》早期那套基于互联网的发行软件都是在我的主持下做成的。当时《华商报》的发行系统各个站就能联网,底下订一份报纸总部即时就能看见。后来沈阳和长春那个系统也都是我做的。 后来我们部门分出来成为五六个部门:国内部、国际部、技术部、特稿部,还有法律协调小组,其他部门收不进去的,全放我这儿了。 实际上,进入报业,我最感激的人就是张富汉。应该说,是张富汉让我知道了什么是报纸。而且,越到现在我越明白,《华商报》的成功不仅是作为报业在技术上的成功,更多的是作为企业运作上的成功;说到底,实际上也是张富汉做人的成功。有很多的报纸,在报纸的新闻运作、发行运作、广告运作上都比较优秀甚至比《华商报》更优秀,但是都没有达到《华商报》现在一样的成功,我认为就是因为在企业运作上不如《华商报》的缘故。 所以如果我的一生能够在这个行业有什么成就的话,首先应该感谢的人就是张富汉。他不仅领我进入了真正的市场化报业的门,更让我知道了,一个成熟的企业,应该怎么成熟地对待所处的市场和行政的环境;作为一个想做点事情的人,应该怎样成熟地对待所处的各种艰难和荣誉。 就在大家都干得不错的时候,《华商报》又出了一件事情,一篇报道引出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正好出在我们部门。 实际上那个稿子根本不是我发的,正好周末我休假,回老家去了。记者是我派出去采访的,但是发稿子却基本不关我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经历了很多人生第一次的事情,比如接受有关机构的讯问、在笔录上面按指印等等。还有各种各样的调查,调查我的短暂的人生历史,调查我与个别敏感的历史事件和组织有没有关系等等……那时候我觉得恐怖极了,但是跟家里人也不敢说,怕父母担心,怕爱人上火,那时候小孩刚一岁,我就一个人忍受这种痛苦。 处理的结果就是:大年初一,老张给我打电话说:“张弓惊,是这样,咱们在沈阳要办一张报纸,你去沈阳吧!” 我就这样到了沈阳的《华商晨报》去了。老婆孩子在西安,我孤身一人过去,一去就是一年。当时我做总编辑助理,主管采访;抓采编当然也不松劲。天天比照几家竞争对手的报纸。他这个头条,我这个头条,我一定要比他强。搞“有奖新闻热线”,并天天把昨天谁提供线索并奖了多少钱的表格在头版登载。结果,有些事件,现场我们比警察都去得早;因为群众看到突发事件,往往先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再打110,因为我们有奖励嘛。 然后就是搞活动,抗美援朝五十周年纪念,图书馆搞展览,征集纪念品。甚至主办电影首映式;张艺谋的电影《幸福时光》首映式就是《华商晨报》主办的。中央电视台曾经都专门报道我们主办的一些活动。 还有,我和发行部主任杨凡青关系好,我也很爱钻研,爱揽事,就开始掺和发行的事情。策划召开发行大会,亲笔给发行部主任起草极富煽动性的发言稿,洋洋一万言,一个通宵写完,会场上杨凡青念起来简直像气功大师的“带功报告”。开发行大会发奖,最多的时候五千人卖报人员开会,大会上奖摩托车,发行状元奖一万块钱,当时得奖的人领到大奖激动得都哭了……“黄马甲”一下子在沈阳搞成了一场“黄色风暴”,刚创刊4个月,期发行量已经40万左右了。 广州·深圳·昆明·北京·内蒙古:开始从投资商角度进入 沈阳这边搞得比较火之后,有朋友把我介绍给当时的广州市委宣传部长、《广州日报》社长的黎元江。他正要创办一份新的都市报《信息时报》。当时是12月了,沈阳是零下二十几度,到了广州是零上二十几度,下飞机以后我简直像是外星人,那一次还中暑了。 当时黎元江就跟我谈,请我过去,给的条件也不错,给一套一百四十多平米的房,老婆孩子的关系也都给解决。但我没直接答应,我说我得回去跟我们老板商量,我总觉得该给张富汉一个交待。 我回去把《广州日报》的事情跟张总说了,他说:“广州那边肯定是个好地方,而且条件又这么高,《华商报》肯定达不到;那你去吧,去了以后,如果有问题你随时可以回来。” 这样我就去广州了,爱人从学校也辞了职,带着小孩一起过去了。举家搬迁。我爱人心也比较细,弄了两个集装箱,连我们家花盆也用集装箱装走了,所有碗筷,一草一木,全部搬过去了。 黎元江号称要拿一个亿来做报纸。我们搞了一个全国巡回招聘,声势搞得比较大。但是没想到,三四个月之内,黎元江就被双规了。于是,我被通知回《广州日报》上班;我不愿意去,就在家里待业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我辞职以后,有人在互联网上骂我“报业混蛋”。有次在北京碰见《华商报》第一任总编辑李涛,他给我总结说:张弓惊,你小子,做事情太猛了。那时候年轻,急于建功立业,想用成绩向对我有知遇之恩的人回报,也想证明自己的能力,所以做事唯恐力度不够,难免照顾不到左邻右舍。我认为李涛总结的有道理。 当时实际上可以回《华商报》,但是我还是选择了凤凰卫视,做其所属的《凤凰周刊》。就这样打道回府到西安《华商报》上班,这不是我的性格。当时《凤凰周刊》在深圳上班,我就住在深圳,跟现在《凤凰周刊》的主编师永刚住同一宿舍。在那边事不多,一周就上两三天班,每个周五回广州,周一才过去,工资还给得挺高。我这人耐不得闲,就觉得总想干点活……在那待了三四个月以后觉得这样下去也没意思,又离开凤凰了。 后来又到了好几个地方,有做起来的,也有没做起来的。从那时候开始,我进入报社的角度不止是总编辑或者社长,而已经开始从投资商角度了。 因为熟人介绍,我认识了《公益时报》的社长刘京,并进入了《公益时报》做总编辑。家这时候还在广州的丽江花园,我孤身一人前往北京。就住在三里屯南边白家庄路《公益时报》的办公楼里,风风火火地干。现在这张报纸主办“中国慈善排行榜”,在公益事业圈内小有名气。现在它的LOGO还保留我当时的设计呢。可是由于我当时对公益实在不熟悉,一年左右,就离开《公益时报》。刘社长非常重感情,我离开的时候,召开欢送会,一起吃饭。他虽然为人低调,但的确是个大格局的人,现在各项事业发展都非常不错。 离开《公益时报》后,我去了中信集团旗下的中信文化体育产业有限公司,做报业投资小组组长。后来这家公司改名为中信文化体育产业集团。这个时候,我开始正式像一个投资商一样看待传媒投资。当时公司总体框架设计非常大,老板一下子想做十几个报纸杂志项目。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都没有能够做起来。 后来又到了云南《生活新报》,这个老板是房地产商,他叫我过去做他所有的一家股份公司的常务副总裁,主管两家报纸,一家是福州的《东南快报》,一家就是昆明的《生活新报》。我觉得在上边做主管太空洞没有意思,就兼做《生活新报》的执行社长。 在《生活新报》,一手抓内容,一手抓发行;最后主抓广告。当时我全家其实已经定居北京了;一个人在昆明。白天开会,抓发行到各个发行站转;晚上,在宿舍支了个传真机,还天天看头版大样。一天上班时间平均18个小时。当时发行推出“订一份报纸送一个小电视”活动,就是那种很小的黑白电视,非常受欢迎。由广东的小工厂生产,一个厂子生产不及,好几个厂子给我加工,每个电视上都有我们的商标,上面打的“生活新报”字样。几个月的时间,《生活新报》一下子火了。 手里有钱了以后,我给报社改善了一下硬件,把报社从昆明有名的“红灯区”(酒吧、歌厅扎堆的地方)搬到一个春城路上比较高档的一个办公楼去,全部实现网络化办公。 但是,我辛辛苦苦装修出来的新办公室,没有坐多久,我就因故离职了。老板当时让我先回厦门休整一段时间,可是我还是直接回北京了。《生活新报》的事业发展此时正如日中天,我就义无反顾地走了。 对于这次离职,我也不埋怨谁。我的解释是:李嘉诚讲过,不要和企业谈恋爱。我更加职业化了。记得我大学刚毕业在广告公司做创意总监的时候,一个创意正做的起劲,客户说:对不起,我们不需要这个创意了,我会说:没关系,你先让我做完。这个时候我已经不会再这样傻了。 回到北京后,多少有点心灰意冷,就希望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前段时间在昆明确实忙坏了。而且,在报业一头扎进去,这么多年了,也确实需要反思一下了。实际上说,说是休息,也没有多长时间,闲不住。然后就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上在职研究生。新闻与传播学院崔保国教授对我特别好,和崔老师一起创办紫光传媒公司,我做投资委员会副主任。还参与了他主编的2005、2006年中国传媒产业报告的撰写,后来这两本书都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 继续做投资。和在中信文化做传媒投资的时候认识的一些投资伙伴一起,搞一些传媒项目的投资。和中石化合资做《车友报·星期5》,当时刚从《北京娱乐信报》退下来的崔恩卿做总经理,我做董事兼副总经理。《内蒙古晨报》和太阳晨光传媒公司,也是其中一个项目。 在内蒙古,老百姓本来是没有看报纸的习惯,认为只有开个小生意或者当领导才需要看报纸,普通百姓人家订报纸简直是败家子的行为。我们在内蒙古做了“马上送”社区服务连锁机构,刚开始先招人,拉人头,你这个发行站站长只要你多招人我就奖励你,20个发行站一个站就一两百人,一下子好多人开始订报纸;而且,对老百姓,订一年《内蒙古晨报》送大米和食用油。《内蒙古晨报》一下又火起来了,当地人也开始有了在家里看报纸的习惯。这件事情还被《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过。 看看,这个世界是个心想事成的世界 这些年投资,都算不上成功。股份进进出出,偶尔也参与媒体内部的组织再造。主要是传媒产权的问题,有很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烦恼。在文化产业之内传媒产业之外,也试图做一些其他的项目;这些项目产权相对清晰一些,政策面相对较明朗一些。有一个好处是:做投资之后,离报业第一线远了,但是离钱更近了。投资的单笔收益往往很高,所谓“几年不开张,开张吃几年”。可是,仔细算算,发现做投资这几年挣的钱,如果把通货膨胀算进去,平均起来,和当年在报社每月领工资其实也差不多。 很多时候,你失去一般的,将会得到更好的。这是我多少年来的经验。说“上帝关上一扇窗就会给你开一扇门”,这个是真真实实存在的。面对困难你用这样的心态对待它的时候,你就不会为很多东西焦虑了。 昨天我在我家所在小区的花园里跑步,突然有一个感觉:这个地方我很久以前好像来过。我回忆起来,可能自己在小时候就梦想过和这个场景一模一样的地方,真的梦想过。我跟和我一起跑步的爱人说,你看看,这个世界是个心想事成的世界。 基督教里讲“上帝的引导”,佛家讲“因果”,其实你也可以理解成你下意识里有很多能量。每个人对未来都要有信心,要相信这个能量,就像《圣经》里面说的,如果你有信心,哪怕像一棵芥菜籽那么大的信心,你即使让这座山移去,它也必将移去。 (本文由本刊记者翟羽佳根据采访整理)
更多阅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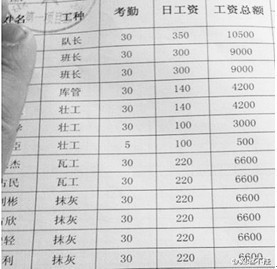
威客网络兼职:威客网是真的吗
威客网络兼职:威客网是真的吗——简介我们不可否认现在骗子很多,如果你不小心一点,很可能会上当,比如什么刷某某要先交会员费啊什么的,确实是不行的,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威客网,威客网络兼职:威客网是真的吗——方法/步骤威客网络兼职:威客网

陈丹青:孤露与晚晴——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发布时间:2014-01-27
陈丹青:孤露与晚晴——纪念木心逝世两周年发布时间:2014-01-27 10:00 作者:陈丹青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2630次向世界出发,流亡,千山万水,天涯海角,一直流亡到祖国、故乡。——选自木心遗稿去年仲夏送走母亲,回京翌日,就在书房圆桌摆上妈妈的
转载 《红楼梦·葬花吟》黛玉 朗诵践离视频蓑衣孤客 葬花吟简谱
原文地址:《红楼梦·葬花吟》(黛玉)朗诵践离视频蓑衣孤客作者:践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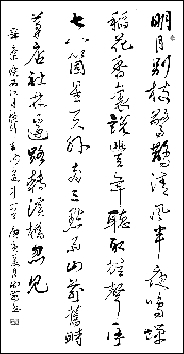
ABC雪地冰天“明月别枝惊鹊”,“别”是什么意思? 明月别枝惊鹊的意思
“明月别枝惊鹊”中,“别”字的解释——对《人民教育出版社》“一词双解”的质疑===========================
张弓惊:我们正经做生意就一定会垮台吗
——就《晋商之死》答本刊记者问 张弓惊,够优机构总干事。《中国传媒产业报告2005》(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中国传媒产业报告2006》(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课题组成员。中国第一本《中国慈善捐赠发展蓝皮书(2003-2007)》(中国社会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