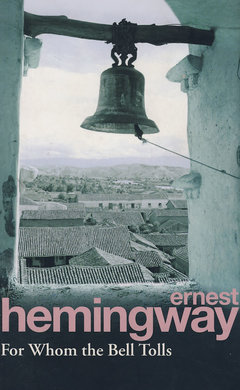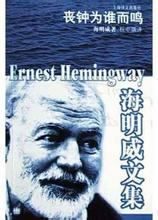记者/王以超
避免全局性水危机,除了要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定位,最重要的仍然是建立更加综合、平衡的利益协调机制
对于很多普通中国人而言,清洁的水正在变得不再唾手可得。
2006年春天,河北省经历了迄今55年最严重的干旱,与之毗邻的天津市也难以幸免。一国之都的北京,干旱程度赫然为50年来严峻之最;从1999年至今,这个人口已逾千万的大城市,一直笼罩在缺水的阴影之中。在水资源相对充足的南方,污染的幽灵挥之不去。无论长江还是珠江,整体水质都没有改善的迹象。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地区,2006年仍有超过3亿人无法获得安全的饮用水。 专家们预测,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030年,中国的水供应能力将达到极限。 失衡的中国 中国是一个缺水的国家,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中国也是一个水资源极度失衡的国家。以华北地区为例,据水利部统计,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只有大约500立方米,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 在中国,“三河”(黄河、海河和淮河)流域几乎供养着一半中国人口,灌溉着四成农田,创造着接近三分之一的GDP,但水资源量只占全国的8%。 在过去50年中,中国主要河流的径流量都在下降,这三条河流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气候学家的预测,随着全球变暖,中国北方地区河流径流量下降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 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去年11月正式发布的《2006年人类发展报告》,人均1700立方米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满足农业、工业、能源和环境用水需求的“最低门槛”;低于1000立方米,就意味着出现了“用水短缺”;低于500立方米,则表示“绝对缺水”。 若按照这个标准计算,中国无论黄河流域、海河流域,或者淮河流域,都应该处于“绝对缺水”状态。 地下水也许是一个可以替代的选择。但问题在于,在过去的40年中,华北地区的地下水水位已经普遍下降了50米-90米——谁也不知道,这些宝贵的地下水还能支撑华北多久? 如果说这种失衡更多是由于地理因素造成,另外一种失衡则源于城乡之间横亘的鸿沟。 衡量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居民能否获得安全的饮用水。在中国,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已经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人口可以获得安全水源,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超过3亿人——其中绝大部分都生活在农村——却仍然无法享受到这种福祉。 据悉,在2006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经要求水利部门争取在十年之内(到2015年),而不是联合国“千年目标”设定的15年之内,基本解决这些人口的饮水问题。按照这一计划,仅2007年就要解决3200万人的饮水问题。 污染的天平 如果不断恶化的水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或许上述种种努力都将付诸东流,已经存在的失衡也将更加不平衡。
根据国家环保总局公布的整体情况,2006年,海河、黄河、淮河以及松花江、辽河等北方主要河流的污染仍然相对严峻。其中,海河流域全境以及黄河、松花江以及淮河的不少支流,更是普遍呈现严重污染态势。 这并不让人惊讶。例如北京,主要河流的径流量本来就相对偏少,加上过度抽取利用,这些河流稀释污染物的能力早已大大降低。如果工业和生活污水未经净化处理就直接排入,丧失了自净能力的河流出现“病态”乃意料之中。 对于本来就缺水的北方地区而言,这种污染势必进一步扭曲早已经高度紧张的“水生命链”。 若论吸纳污水总量,恐怕哪一条河流都无法与长江相比。专家估计,每年排入长江的污染总量当在200亿吨以上,而且还在以大约每年10亿吨的速度增加;长江全流域生活污水的处理率还不足七分之一,其工业污染物的处理现状也难以令人满意。 尽管长江干流水质到目前为止还处于良好状态,但随着不少支流陆续被污染,长江已经事实上处于“亚健康”状态的警告,在过去几年中已经不绝于耳。早在2005年,长江领域就有超过500个城市不同程度出现过因为污染而取水困难的情况。 中国南方的另一条主要河流——珠江,也在面临着同样的考验。即使全流域、长时间的污染事件不会很快出现,局部、短时间的污染事件频发同样会打乱两岸居民的正常生活。 一方面,国家每年斥资数十亿元,希望解决数千万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另一方面,每年的环境污染,又把数以千万计的人重新推向灾难的边缘。 寻找新出路 面对“水荒”,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入手也许是最自然的选择;启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则是改善供给的主要渠道。既然天下之水南北不均,用人工来“损有余而补不足”岂不美哉? 经过半个世纪的争论和筹备之后,规模浩大的“南水北调”工程的中线和东线均已经开工。如果一切顺利,西线工程也将在2010年左右正式开工。 不过,单纯寄望通过调水工程来解决供求矛盾也许并不现实,这早已有史可鉴。专家们警告说,以中线工程为例,沿途省份仅拟上马的新项目年耗水量就可能超过整个工程的输水量。 最大的挑战,或许仍然在于如何切实有效地控制需求。在需求端的管理上,最有效的手段也许仍然是通过市场化的价格机制,引入用水权制度,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 但是,正像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在拉美不少国家演绎的“水权风波”那样,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有效地发挥市场手段的功能,不是一件轻松的任务。如在玻利维亚等国家,水的私有化过程都曾经沦为某些权贵以及政府部门、垄断利益阶层谋利的工具。我们是否有信心避免这一幕的重演? 迄今为止,农业仍然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用水大户,每年几乎耗去了三分之二的水资源。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农业用水的比重也仍然接近半数。 如果说,工业企业以及城市的生活用水定价已逐步形成一定的规范,那么,如何调节农业用水,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因为这不仅涉及市场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公平问题。 如果仅以象征性的价格来交易农业用水权,也许难以起到设定的激励目标;按照充分补偿的原则来制定用水权交易价格,则意味着在中国最为底层的农民将负担沉重——他们既缺乏资金,也缺乏必要的技术能力,去选择节水型农业。例如,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固然让人羡慕,但在中国要全面推广这些技术,需要的资金将不啻为一个天文数字。 一个方案是选择给最贫困的5%人群提供相应用水补偿。但在中国这样一个还缺乏完善的法律体系以及严格透明的运营、监管制度的大环境中,任何设计都必须充分考虑到可能增加的成本。 国家战略 政府治理结构上的无力,在水污染上表现得或许更加充分。 不断上演的地方和中央的利益纠葛、长期和短期的政策权衡,以及“以邻为壑”的“双输心态”似乎都在表明,仅在目前的监管体制上做一些小的修补,并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单纯苛责水利部或者国家环保总局的无作为,也并不公允。毕竟,全局性的危机只能寻求一个全局性的解决方案,这显然都超越了这些具体部门的权力范畴。 要解决主要江河的污染问题,一个很重要的设计是引入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这样,上游才有经济动力,去保护水源的洁净;下游也才有压力去约束用水量。但如何建立一个保证生态补偿机制真正得以运作的“政府间谈判机制”,以更加综合、平衡的视角来协调其中的可能冲突,对于决策者而言,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问题仍然在于,水危机还没有真正被提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上来考虑。“十一五”规划中,我们设定了宏大的单位能耗目标及二氧化硫排放目标,但单位水耗等同样紧迫的目标却滑出了太多人的视线。 在民间,众多的草根NGO组织及先行者早已默默行动起来。1999年,一本名为《中国水危机》的书籍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本书的作者、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在2006年秋天推出了中国第一个“水污染地图”;在即将到来的2007年,他们的目标是联合各地的NGO,更精准地确定污染中国之水的各个污染源的具体位置,并且以各种方式对这些污染者施以压力,让其付出代价。 机会总是存在,但是迟是早,意味着付出截然不同的代价。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