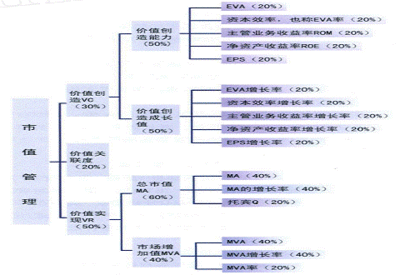记者/曾焱
1.5亿港币买一只清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1.16亿港币成交明永乐释迦牟尼坐像,8533万元一件古董屏风,4260万元一幅傅抱石……2006年国内拍卖场上这些一掷千金的世界纪录,以一种最直观的方式,把传说中的盛世收藏景观在我们面前放大到了极致。可是比照历史,如果这个时代最终产生不了真正有文化传承的大藏家,这种景观就缺少风骨,不过是热闹的数字游戏。
中国的古玩收藏风气,公认以北宋末年、清康熙年间以及清末民初三个时期最盛。有说“古玩”两字自清代始,在这之前称为“骨董”,字面上“骨”取肉腐而骨存的意思,“董”即知道了解,存的和晓得,自然是古人所遗留的精华。这种解释更像是文字游戏。骨董作“古董”沿用至今,“古玩”两字也非清代才有,《元曲选·武汉臣·生金阁·楔子》的戏文中就出现过,一个“玩”字,写尽藏家们举重若轻的庞杂的生活意趣,却也消解于历史文化传承上的那点郑而重之。 旧时收藏,能沉浸其中的不外两类人:有钱人,雅人。新晋的官、贾玩收藏,不经年头难有雅名,一句“树小墙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讥讽的就是这种。收藏四个层次:一藏、二赏、三玩、四鉴,多了要好,好了要懂,还要有将所得传给后世不至埋没的心气,所以最终收藏能达上境的,多为有钱的雅人。从古代到近现代,书画、瓷器这些门类的大藏家历来首见于世家子弟。民国“四公子”:袁克文、溥侗、张伯驹、张学良,个个在书画、诗词、戏曲、古玩上有过人之处,其中张伯驹和袁克文便是近代史上留名的大藏家。袁克文虽是袁世凯次子,却对政治不感兴趣,“志在做一名士”,很多回忆文字都说他工诗文,精金石,玩古籍善本,宋版藏书竟过百种。宋版书珍罕,从明代起就是以页来论价,百种宋版可见袁克文藏书之精,近代藏书史上没几个人能比,现存北京图书馆的宋刻本《鱼玄机集》就是他的旧藏。袁对宋刻本《水经注》的校勘虽被一些文人学者贬为“谬论”,但在当时也成一家之说。 同为贵胄入收藏,张伯驹的境界又高出许多,据说他当年将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300多卷《资治通鉴》能从头篇讲到末尾,收藏字画则以眼力、魄力过人闻名,自认“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用现大洋4万块买下晋陆机的《平复帖》,黄金240两购隋展子虔《游春图》卷,一件天下第一帖,一卷存世最古的画,归属都轰动一时。4万块大洋是个什么概念?有文章记民国时清华法学院的院长陈岱孙先生,说他月收入400多块大洋,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4万元,那么仅从面上数字折算,70年前张伯驹为购长不足一尺的《平复帖》用去400多万人民币,这真是普通人不能想象的天价。 文人是承继收藏传统的另一脉。历代著名文人,收藏古籍善本有大成的居多。文人财力不如世家,不少却能由藏而鉴,成大家学问,在文化传承方面体现了收藏的重要一脉。民国傅增湘,官至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下野后闭户研书,人称二三十年代北平文化界雅人的标本,“所居有山石花木之胜……聚书数万卷,多宋元秘本及名钞精椠”。他收藏宋代至清朝古籍善本总数在20万卷以上,其中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和宋刻本《资治通鉴》被视为绝世之宝。傅增湘同时还是目录学家、校勘学家、版本学家,“海内外之言目录者,无不以先生为宗”。 民国时期大文人里,鲁迅、郑振铎也是古籍大藏家,1933年两人曾一南一北,合作编印了《北平笺谱》。郑振铎每日到琉璃厂淘找笺样,整理后用包裹寄往上海,鲁迅勘选了再寄回北京,由郑振铎交老字号荣宝斋刻印。这本《北平笺谱》,加上1936年出全的《十竹斋笺谱》,把我国濒临失传的传统木刻水印工艺从故纸堆里抢救出来。郑尔康在《我的父亲郑振铎》中还写了一件旧事:郑振铎研究宋元以后平话小说,想看看《西湖二集》,写信问鲁迅先生有没有藏书,没想到随回信收到大包裹,里面是半部明末插图本《西湖二集》,鲁迅信中说他现在不搞中国小说了,这书留在手边无用,于是相赠。两大文人之间这样的遥相唱和,和名士雅集共赏唐诗宋词晋文章的境界并无不同。
当代大收藏家王世襄老先生说他自己对任何身外之物都抱“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态度,“遣送得所,问心无愧,便是圆满的结局”。藏家的最高境界应当也在这8个字上。“由我得之”不易,眼力、财力、魄力都需齐全,“由我遣之”更不是一般藏家能做到,有了私藏为公的心气,才有千金散尽的大气。1952年张伯驹将《游春图》捐给国家,1955年又将《平复帖》和多年收藏的唐杜牧《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等罕世珍品一共8件全部捐给故宫博物院,奖金分文未取,留了一纸奖状。1942年,大藏书家周叔先生在他手订的书目上留书子孙,“数十年精力所聚,实天下公物,不欲吾子孙私守之”,10年后平生所藏2000多册珍贵的宋、元、明清刻本、抄校本全部捐给国家。如今拍卖场上那么多志在必得的面孔,不知道有几人日后对周书先生的留书能够感悟。 听大藏家的故事,看他们的心得之作,即便是不专此道的人,也能从中感到一种沉着的趣味。古董对于不识其品质的人,仅仅是与其历史价值、市场价格相关联的奢侈占有,是身份的标识,在专家掌眼下,藏家跳过了淘选过程的历练,日后如不能续接把玩回味的日程,古董的“懂”或古玩的“玩”也就难有体现,这种境况中的古董往往会让占有者心随物乱,得失皆输。而对于识得的人,必定不只是千金万银可以衡量的,能寻得一宝虽然也怦然心动,但那是见识的修养所至,更有延续性的修养还是在日积月累的把玩中、在同道的相互品评中滋养出那种怡然会意的趣味。历来的大藏家似乎都能在收藏把玩中感受到那些古董向外渗透的一种沉着自定的历史力量,那是一种传衍和召唤的力量,最终成就的是识物知天的心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