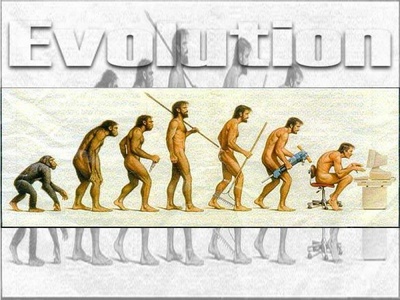文/吴戈
超耐力选手能达到近乎不可能的体能目标,这是一种少有的遗传基因,还是人类进化的遗迹?

自我折磨
徒步跋涉125公里,骑车250公里,划船131公里,再穿越97公里的峡谷,在波浪中游泳13公里,最后还有骑马和登山。所有这些都要在犹他州的酷暑中用6天时间完成,别想停下来睡觉。这就是每年一度的“原始探险”挑战赛的疯狂规则,如果你觉得马拉松和铁人三项还不过瘾,可以试试这种最极端的耐力挑战。在2006年夏天参加“原始探险”赛的90个四人小组中,只有28个熬到结束。获胜小组中的迈克尔·图宾说:“这更像是一次酷刑。” “撒哈拉沙漠马拉松”的参赛者、新加坡30岁的业余选手陈文潇说:“每一站,每个参赛者除了休息,个个都忙着清洗伤口。脚趾、脚底都起泡,必须把水泡刺破,剪掉茧皮,然后把脚伸在营帐外头曝晒,到了第二天就没事了。”该项赛事另一位参赛者,ITT公司中国总裁马克·斯梯尔说:“最困难的时刻是我们必须在凌晨5点起身,这时我们全身酸痛,难以站立,脚板布满燎泡,腿部血迹斑斑,满是纱布。” 罗宾·贝宁卡萨是美国圣地亚哥的消防队员,也是出色的超耐力运动员。她还记得自己最精疲力竭的时刻。1998年在厄瓜多尔安第斯山脉比赛时,她马不停蹄地跋涉了两天两夜,又是一座超过6000米的火山等着她。“我的指甲根部已经变紫,嘴唇也是紫色的,整个身体都在发紫。”她回忆说,“我在雪地中手脚并用,边爬边哭。”到底是怎样爬到顶峰和队友一起获得胜利的,她根本不记得了。 炼狱也不一定只有雪山之巅。每年夏天,在闷热的纽约,一条周长883米的水泥跑道上,都会有一群人周而复始地绕圈。这种长跑要持续不是一天,也不是一周,而是近两个月,每天从凌晨6点直到半夜,长达18个小时。他们的目标是跑完3100英里(4988公里),累计达5649圈。 这是世界最长的长跑比赛——奇莫伊自我超越3100英里赛。参加者必须在51天内跑完,相当于每天60.8英里。目前成绩最好的是德国人沃尔夫冈·施韦克,用时42天12小时,平均每天能跑72.8英里!女子冠军、美国的苏普拉巴·贝克约德在过去10年参加过一次2700英里和9次3100英里比赛,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了8次。 相比之下,2006年12月23日国内历时半年的“全民急速大挑战”集体徒步赛不过是一场电视游戏而已,走遍全国20个省市区,行程才1万公里。每站淘汰最慢者,连成绩也不必公布,年度总冠军就能获得百万元人民币代言费。 异秉之源 奇莫伊赛事创办者、印度人奇莫伊的目的是用运动表达他的自我完善理念。这也是越来越多运动员参加超耐力比赛的共同目标——拓展自己的极限。与他们相伴的还有对超群体能充满好奇的运动生理学家,他们有时甚至不打折扣地赛完全程。 有的科学家认为,超耐力运动员有特殊的基因或生理结构,使他们可以超出常规的极限。另一些人认为这些运动员在生理上与马拉松运动员等选手差别不大,独特之处在于大脑,这使他们可以在身体大声叫停的时候坚持下去。不管怎样,他们都发现:在人体被延展到崩溃点时,也是研究人类生理的绝好时机。“科学家天生迷恋极限。”斯坦福大学的心脏病专家欧安·阿什利说。 这样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迄今为止,运动生理学的焦点大多放在著名的职业运动和奥运会项目,而不是这种业余选手之间冗长的折磨。同时,超耐力比赛也很难在实验室研究,有几个人愿意在跑步机上不停地跑24小时以上呢? 不过,超耐力运动员和普通运动员之间已经有一些重大差别显现出来。比如,在1万米长跑等相对短的项目上,冠军往往是20多岁的选手,而超耐力赛的优胜者多半30出头,因为后者的身体经过了更长时间的训练,才达到这种比赛要求的肌肉强度和代谢效率。超耐力冠军也非常善于在很长时间内只释放最大体能的60%到70%,而最强的普通运动员都是那些在接近100%体能时用氧效率最高的人。 瑞典斯德哥尔摩卡洛林斯卡学院的科学家米凯尔·马特森和约纳斯·恩奎斯特最近有了更新的发现。他们的小组请到了9个世界级选手,在实验室的机器上不停顿地跑步、骑车和划船,持续达24小时以上。根据运动员的心脏和代谢数据,马特森等人初步发现:超耐力运动使运动员肌肉中生产能量的线粒体更善于利用脂肪而不是葡萄糖作燃料。每千克的脂肪产生的能量比葡萄糖高,但身体在剧烈运动时一般不能燃烧脂肪。耐力运动员的身体可能有办法更快地利用脂肪,使葡萄糖储备留给比赛后段使用。“这是这些运动员在生理上与其他运动员不同的原因之一。”马特森说。他的计算表明,这些运动员在一天的比赛中要消耗约2万大卡的热量,这是一个用饮食几乎无法补充的数量。 马特森不明白的是,超耐力运动员的特殊生理能力是与生俱来,还是通过训练形成的?根据开普敦大学分子生物学家马尔科姆·柯林斯对超过400名南非铁人三项赛选手的研究,也许基因至少发挥了部分作用。他们研究的是制造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的基因,它能使血管变窄,减少能量消耗。在1998年,科学家就发现这种基因与登山运动员和陆军士兵的耐力有关。最近,柯林斯发现:成绩最好的南非铁人运动员中有77%携带有这种耐力基因的一两个变异,而普通人中只有67%。 还有别的基因吗?柯林斯将目标集中到两种与ACE有相同生物化学途径的基因上。这些基因的变异影响血液流动和肌肉代谢效率,那些铁人三项成绩平均在12小时30分之内的运动员,携带的这两种基因变异较为合理,携有“较慢”变异的运动员,成绩平均只能达到13小时4分。 也不能把一切都归于基因。柯林斯的同事蒂姆·诺亚克斯认为:超耐力运动员的身体实际上与其他运动员并无太大不同,一再被忽略的不同之处在于大脑。他说:这些人是“精神异类”,而不是生理上的。运动生理学一般认为,肌肉、肺和心血管系统决定了运动的极限,但所有这些外围器官的生物化学信号是由大脑来协调的。当收到表示疲劳和组织损伤的信号时,大脑会无意识地命令停止运动,以防毁了身体。诺亚克斯认为,也许在其他人早已瘫倒时,超耐力运动员的大脑使他们可以忽视警告信号。正如奇莫伊所言:“我是用肉体完成这些运动的,但力量来自内心。” 为此,诺亚克斯正在研究大脑使用何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信息来决定理想的运动节奏。他们最近对两组运动员进行了实验,一组准确地知道还要跑多长时间,另一组则受到欺骗。两组都以同样节奏运动,但前一组使用氧气更加合理,并且不会释放全力。 意志有那么神奇吗?哈佛大学的生物人类学家丹尼尔·利伯曼认为:哪怕是“沙发土豆”,也会有一些耐力运动员的特质。他认为,人体天生适应长距离奔跑,这是远古时代为捕猎和搜寻食物而进化出的能力,现在依然残存在体内。他说:超耐力选手能够出众,也是因为进化得来的能力作基础。一个能一次慢跑几十公里的身体帮助我们的祖先生存下来,只要有足够的水、能量补充,加上更多的训练,人体完全能够完成90公里以上的超级马拉松。 如果真是这样,研究超耐力选手的科学家也完全可以亲身重启我们的进化史。加拿大学生保罗·劳尔森因为沉迷于三项全能运动,第一年就功课不及格,离开了西蒙·弗雷瑟大学的机能学专业。现在,他的身体达到了脂肪比例10.6%、安静时心率每分钟48次的完美状态。2006年12月初,他吞下了一个微型温度计,参加了在澳大利亚西部举行的铁人三项赛。这次他不光是运动员,也是原来参与过的科学项目的研究对象。虽然成绩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差,但试验获得了成功。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