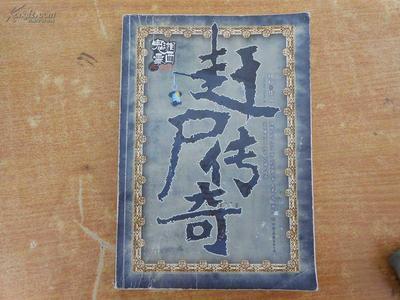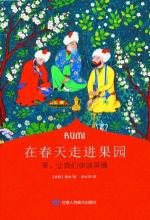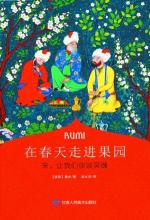系列专题:《三个博士姐妹的家庭教育:玩学习》
我觉得,一个人的兴趣也是如此,一个人总会对某一些事情发生兴趣,这是必然的,但对哪一个具体的事情发生兴趣,则是偶然的。比如,一个孩子总会对这事或那事发生兴趣,这是必然的,但是孩子是对书发生兴趣,还是对打球发生兴趣,这也多少有些偶然性。? 说是偶然的,并不意味着只能听其自然,不能进行控制,相反,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促使事件向预定的方向发展。照此看来,在孩子还很小的时候,小得你认为他还是一个小糊涂虫的时候,在你认为孩子对书还一无所知的时候,你就让他多多接触书,让孩子对书产生兴趣,我以为这是一个让孩子爱读书的办法。? 我以为,“先入为主”在培养孩子的兴趣上,也是一样起作用的。如果有意识地让孩子先爱上书,使其兴趣先在书不在其他。或许,日后想要孩子不爱书,都成为不可能的事了。相反,如果无意间使孩子爱上了游戏机,日后想要孩子不爱游戏机而爱书,就又成为不可能的事。? 俗话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教育孩子爱书,或许也有一个最佳时机。家长应有意识地抢占“先机”,这样才能有主动权。? 在中央电视台《新世纪科学论谈》节目第二期中,袁隆平院士回答了一位女士的问题:你是解放前教会学校上的中学,你是怎样决定学农的?袁院士很爽朗地回答说,在中学时学校组织学生到江夏一个什么地方参观了一个农场,那个农场里满地里都是红的、绿的花果,使我大为兴奋,于是对农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1951年就考取了西南农学院。? 当时学校的这次参观,不经意间种下了一粒大农学家的“种子”,这是当时任何人所无法料及的。? 我是江夏人,出于对地方史的兴趣,我对新旧江夏志略有涉猎,我在此可以为袁院士年深月久的童年记忆作一点注脚。袁院土当年参观的这个国营农场,位于武汉市江夏区金水乡。这个国营农场始建于1935年,武汉市江夏区在辛亥革命前称江夏县,辛亥革命后民国时期,占了地缘之利,沾了“首义”之光,更名“武昌”——以“武”而“昌”,1986年又改成今名。1935年,当时的政府搞什么“建设模范县”,武昌县地近武昌城,自然是“模范县”的建设对象,为了建设“模范县”,当时的政府拨款在武昌县金水乡建立了一个国营“示范农场”。? 一个人在幼年、少年时的一次偶然的经历,给一个人的一生都带来极大影响的事,成名的人有此事,不成名的人也有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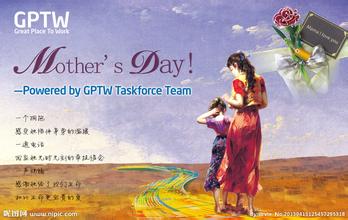
我喜欢读书,也是偶然的。解放初期,进行土地改革时,我有6岁多,但还没上学。武昌县解放前已经有官立高等小学堂,但我的家乡——大屋陈乡没有。解放后,我的家乡已经有小学,但我的父母没送我上学,我是1952年才开始上学的,那时我已有8岁。? 我们村有一家人家,有很多书,划成了地主,属于斗争对象,其家人全部赶出门,家具、衣物、粮食统统都没收了,但那些书,被视为不值钱的东西,没有搬走,因为是地主的东西,门开着,也没人敢拿。我年幼无知,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拿得拿不得,我先是觉得那些字帖很好玩,书纸是黑的,而字是白的,与别的书不同,我从那间房里拿了几本,也没人看见,我怕父亲骂,拿回家就藏起来了。过了两天,我又独自一人到那间堆满书的无人房间里去玩,房里空无一人,多少有些怕人,但我还是大着胆子走了进去,那间房有一层楼板,上面堆着好多好多书,又有一架木梯,我这是第一次爬木楼梯,一个人怯生生地爬上去,一看,哇!真多书呀!那一幕,我至今未忘。? 我又在那间房发现了一本很厚很重的书,我一个人拿不动,我将小我两岁多的小弟弟喊来帮忙,经过一个小巷时,我觉得有些害怕,后来,两双小手硬是把那本书抬回了家。后来,我开始上小学,我还时常翻一翻那几本“偷”来的书,1953年我上小学二年级,见其中有一本书上有个外国人头像,下面写着人的名字,叫牛顿,我觉得真稀奇,怎么会姓“牛”,名字也怪,叫“顿”,名字中怎么没有“辈分”,他的亲人怎么知道他是什么辈分?我见一本书上有许多图案,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就问我的祖母,祖母不识字,大概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党旗,觉得家里有这样的书是不好的,她后来把这几本书都作为引火纸烧掉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