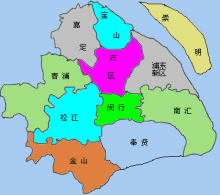一个文化最大的愚蠢就是以效率为指导原则来让自己生存下去
摘自《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文《财经》杂志/总191期
纠缠不清的问题,倔强地盘旋下坠,又聚结更多问题,成为更大的下旋模式;这些问题是很让人沮丧,但也并非超自然的怪事。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各种错误与不幸的实体结果。无家可归、让人买不起的住房,及其各种衍生问题,都可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及其后的战争年代中找到实体的根源:在30年代人们也盖不起房子,而大战期间建材与技术工人都投入紧迫的战事之中,而不是投入较不急切的民间需求之中。 …… 悲观地看,我们必须记住,穷人的住房短缺、具包容性的社区之消失,及对于汽车的过分依赖,这相互纠缠的恶性循环,它的源头就在大萧条和“二战”的那十五年里。想解开那恶性的循环需要和平与繁荣;人民必须要能接受改变城市扩张区的密集化和重建过程。假使经济大恐慌、战争、停滞型通货膨胀和预算削减要再重来一次的话,足可让北美洲人民正式且永久丧失解开这恶性循环的机会。 企图修补城市扩张的各个办法都具有一项优势,就是城市扩张太明显是浪费且无效率的。北美人民崇尚效率。北美的关于规模效率的民间英雄,如埃利惠特尼、亨利福特及步其后尘的一大批效率专家,早早就已经说服了北美的政客与人民:规模经济是美国的高水平生活的成因。 这的确是个部分真理。当生产处理的物品是个个完全相同的,比如玻璃丝袜或是轧棉机、汽车,或其他机器的零件,它们的研发与设计都已经完成了,如此,则规模经济很容易达到。加工处理越多相同的物品,每件物品的经常性费用就越低,每件物品的成本也就越低。然而,效率并非解开文凭主义、科学心境萎缩,以及职业自审失败所形成的恶性循环之钥。这些是文化失败的交错盘结的证据,值得我们教育与学习。 教育界的错误转向之细节线索很快地就被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们指认出来,他们抱怨自己的大学教育被欺骗了,因为自己像原料一样被灌入无人性的生产线中。在培育人的过程中,效率和规模经济就不适用。要使一个人成为社会中能被认可的、成功的一分子,是需要一大批慷慨细心照顾别人的人。许多自传和回忆录都满怀感激地指证这种救命的、激励志气的关爱。 会计师、牧师,以及其他高学识的专业人士,他们其中有的已经拥有了梦想中的事业,但却未能负起道德上职业上的责任,在他们向前辈的学习过程中,他们并未受到足够的教导,让他们能遵循社会所期许的文明准则。这些职业人士就像孩子们一样,需要人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为什么如此。 在大学教育文凭化之后不久,工作负荷过重的教授们发现很多小学生中学生已经被大批地(应该也是高效率地)处理过,但处理得甚为不当,以至于需要补教他们数数字、阅读能力,议论文写作,不然没法在大学里颁给他们文凭。在一个复杂的文化中教育人需要大批甚至充裕的师长和模范。这虽然昂贵,但绝对必要。或许这也只是生命本来就昂贵的一个例证吧。仅为了生存下去,生命就需要能量供应生命体之内、之外;这比起死亡与衰败的低开销来说,确实是胃口极大的。而一个文化单单要继续生存下去,也就大量需要来自许多人的亲身教导的这种能量。
当我们的社会处在比今日要穷很多的过去时,它还是有办法应付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必然伴随而来的开销和低效率。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今天的穷而旺的文化又是怎么生存下去的呢?答案是,所有的文化一向都大量依赖社会区中自然存在的重复性:不同的个人,以不同的方式适应社会并为它做出贡献。即使是贫穷的社会也能养得起师长和模范,因为社区里这样的人是附带性地扮演这种角色的,一边享受生活或是以他种方式谋生;讲故事的能干商人与工匠、乐师、赏鸟者与其他自然爱好者、艺术家、冒险家、女性主义者、世界主义者、诗人、志愿者与实干家、棋士、玩骨牌的、道德家、从生活中学习与从书中学习的哲学家——他们在社区中是有形可见的,但在社区变得已不复可见时,他们在年轻人的眼中也不复得见。 在文化败坏到培养和教育下一代都成问题时,大部分的思想上和其他的优势就变成是精英阶级的专利了。这就是在罗马帝国崩塌后的黑暗时代——封建欧洲所发生的情况。重复性不够用的时候,就被当做奢侈而以定量配给。少数幸运的人能有家庭教师和文化导师,其他人也就只有那么过了。即使那些幸运的少数,其中有许多也是与所学的格格不入。一个文化最大的愚蠢就是以效率为指导原则来让自己生存下去。当一个文化足够富裕也足够复杂到明明可以负担重复的培育者,而却以奢侈为由铲除他们,或是因记忆丧失而失去了他们的文化服务,那么结果就是自戕的文化集体灭绝。之后就等着看恶性循环开始运作吧! 摘自《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参见“本刊8月荐书”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