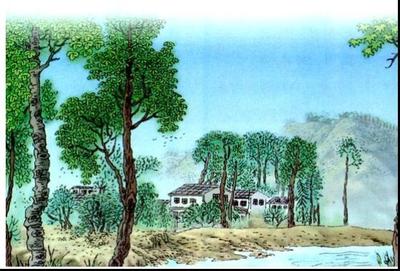◎朱文轶
稻玉村的白天也少见人烟,人们大门紧闭,用这种方式来彼此告诫要小心。这个背靠秦岭的陕西周至县村落其实从来没有面临过什么大的危险,但现在,每人都认为自己身处险地。十几天前,又一个6岁的女孩被离奇毒倒,西安的一家医院才把她从死亡边缘拉回来。人们把此事和去年村长朱景林之死联系起来,过去6年里村里共造成3人死亡的数十起中毒事件让人不寒而栗。 投毒者的幽灵 刘春凡在村子里已经没法待下去了。今年3月,她愤怒的二嫂点燃堆在刘春凡家门口的稻草垛,大火把刘家的大门烧成了枯炭,被烟熏得漆黑的房子看起来像一间无人问津的山庙。刘春凡只有躲出去了。 一开始,人们相信村子被某种邪气下了蛊。位于丘陵地带的稻玉村,被一条下雨才有水的干河分成河东和河西两块。2001年开始,接连的“怪事”都出现在河东。几户人家的孩子突然犯病,抽风、口吐白沫。河东因地势平缓,住户和人口略比河西密集。人们先没有往“中毒”上想,只是猜测河东的风水出了问题。稻玉村的老村长周来宏说,2002年,村里的老人出面集资了1.2万多元从外面请了戏班,搭台唱了3天大戏。 村民请的“药王神”并没阻止“怪事”。2006年底,“邪气”降到了村长朱景林的头上。朱景林的四弟朱景云回忆,11月19日,朱景林跟老婆王叶叶说他想吃点粉蒸肉。王叶叶把肉蒸在锅里快熟的时候,去正在盖房的妹子家帮忙打杂,朱景林叫住在老五朱海功家的母亲一起吃饭。“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中午刚过,二哥就倒地抽搐,家人急忙把他送到医院。回来后不久,我妈也出现情况。一家人急忙把老太太推进县医院急救室的时候,医生已经出来说,我哥不行了。” 人们于是开始注意这些偶然事件背后的联系,他们发现,受害者最终都能和朱景林一家人扯上关系。村里第一个中毒的女孩经常跟朱家老五朱海功的女儿在一起玩,女孩死后第6天,朱海功的女儿就出现了和她同样的症状,因抢救及时而得救。 在周至县稻玉村,这个家族的恩怨几乎早就家喻户晓了。 家族恩怨的社会背景 刘春凡的男人叫朱计功,朱计功是朱家五兄弟中的老三,在稻玉村是一个爱寻衅吵架的家伙。村里喜欢他的人很少,但没人敢惹他。 这个家庭也不大与他人交往。他的对门仅隔几步路,住着他的大哥和二哥。他每天都要和他们碰面,却很少主动打招呼。他们没什么深仇大恨,村里人说,朱计功对他老婆基本上言听计从。在他看来,自己的兄弟属于另一个利益集团,和他针锋相对。 表面上,朱家五兄弟的隔阂源于朱计功小时候他父亲把他过继给了一个远房亲戚。尽管这只是名分上的,朱计功和其他弟兄4人还是吃住在一起。但据说,长大后,朱计功和其他几人的关系就生疏了。朱家其他人坚持认为,老三在家庭里地位变化导致了他的心理落差。 1979年,朱计功就闹着要“分家”。80年代左右,在稻玉村,父权仍然是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里最有威望的一种权力。没有特殊原因,比如,家中住房紧张,老大要给老二腾出新婚住房,分家在一个被视为和睦的家庭更是无法容忍。 朱计功敢于提出分家,老四朱景云说,这里的确多半是朱计功受到了老婆刘春凡的鼓动。在公社体制下,一个家庭一年在生产队挣得的工分都在年底统一交到家长手里,由家长统一分配。“朱计功两口子结婚后一直就在算账,算来算去,他们觉得在这碗大锅饭里吃不划算,自己负担太重。” “父亲刚开始也不同意,但后来发现不分没办法了。老三在外面干零活的收入也不上交,自己攒私房钱。他还经常听两口子在背后埋怨这件事。父亲看管不住了,与其吃一锅饭,生两样心,不如分了算了。”朱家人说。 当年朱计功闹着要分家时候,他有无法掩饰的优越感。他和刘春凡两人挣的工分要供养两个正在上学的弟弟,那时他的确是家里的顶梁柱。80年代,像朱计功这样两口人务农的家庭要更吃香,整个分配制度仍然偏向劳动力。直到1981年,稻玉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村委会都还是统一了“照顾劳动力”的过渡方案。 “稻玉村没有手工业,它的全部收入来源于农业。其他一些县和一些生产队直接采取了按人头分地的方法,但是我们不行,要照顾劳动力。”稻玉村原村长周来宏说,“人8劳2”的过渡办法在稻玉村延续了3年。这种所谓“人8劳2”分配制度,是指将全村土地的80%拿出来按人头均分,剩下的20%在农业劳动人口间进行二次分配:劳动人口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 朱计功是这种制度下的受益者。但随着政策过渡期结束,朱计功和刘春凡家里多分的地被陆续收回;完全依赖务农,两人的经济优势也不再明显。他于是成了稻玉村“转型”里的失意者。 分家后,随着时间推移,朱计功的状况更是急转直下。几个兄弟都比他有出息,二哥做了村长,四哥是县里文体局干部,在县里还有自己的生意,他对生活的挫败感与日俱增。他把他对家族的控制感和少许仅存的心理优势都集中到他的大舅子门口那块地上。他和大舅子刘智玉之间倒组成了“阵营”。这块7分地成为朱家后来无休无止的争吵、纠纷以及更大悲剧发生的根源。 “7分地” 朱计功和他几兄弟现在住的房子是在河东一块宅基地上。在稻玉村人看来,这是一块难得的好地,因为在坡地很多的村里,这块地特别平整,是盖房的好地方,并且地两边还邻着出村的两条主要道路。 稻玉村的“联产承包”比陕西其他村要晚一年。1981年分地时候,这块地上只有两户姓王的人家,很多住在河西的人都想搬到这里。周来宏说,作为生产队的预留地,谁都可以申请,“谁的申请提得早,谁就拿到这块地”。 第一个申请到的就是刘智玉,他的房前拥有一块完整的7分地。后面很多人接着把房子盖到了这里,包括朱家老大朱占功、老二朱景林。先入为主的刘智玉给这些后来者制造了麻烦。 稻玉村三组组长王文玉说,稻玉村的土地相对丰裕,一开始对住宅用地和农业用地的比例规定不像其他村那样严格。在很多村,都实行“宅田挂钩”,一户农民的住宅多了,就要相应缩小农田面积。“稻玉村就有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很多人家宅基地都修得很大,如果按照‘宅田挂钩’的方法,他就分不到田了。这样,稻玉村没有一刀切,而采取‘庄、田分离’,以1970年为线,1970年以前,村民超过标准的大宅仍然保留。1970年以后的房子,一律按照‘前三后二’的标准修建,就是保证前面留三丈空地后面两丈。” 朱家两兄弟80年代盖房时因此留下了心病,门口全是刘智玉家的地,他们的房子连基本的“前三后二”也没法实现,“出门只有两三米地方是自己家的,更何况,朱景林后来还当了村长”。 只是刘智玉实在不是个好打交道的人。朱景林几次找刘智玉商量换地,都被他拒绝。朱家老五朱海功回忆,1992年,两家再次坐下来谈判,当然有求于人,朱景林尽管是村长,姿态还是放得很低。“我哥问他如果把门口块地对通,他想要什么条件?刘智玉说,‘这10年来,我这块在你家门前的地就没有好好长过庄稼,就因为你家的房子欺了我家地,我还没跟你要补偿呢!’我哥后来说,那我们给你300元补偿,你把地让给我们。”两家最后不欢而散。朱海功说,他觉得7分地本身并不是大事,但刘智玉心里认为,凭这块地,刘家就压过朱家一头。 1995年,老三朱计功打算从河西老宅搬到河东,和亲戚们住在一起。朱计功本意并不是想挑事来,但他的到来确实让朱家陷入了纷争。 尽管分家后,这个弟弟并不受人欢迎,朱占功和朱景林两兄弟还是爽快答应了他的要求。这里面当然有俩人的私心。朱计功的房子盖在朱景林家的对面,而朱计功那块宅基地的对面正好是朱景林的田。朱计功这样就面临着和朱景林同样的困境,如果朱景林不给他让地,他的房子就只有后院没前院。如果二哥把地让给他,当然会有条件,就是朱计功要说服自己的舅子,以那块7分地做交换。 现在看,朱家俩兄弟简直是“引敌入室”。朱计功不仅没有履行当初的“君子协定”,还跟刘智玉站到了一块。“7分地”成了他们的“武器”。大哥和二哥越是想要那块地,他就抓得越紧,他要时刻赢得并享受这场战争的控制权。2000年,朱家的老父亲去世,朱计功和其他兄弟的矛盾就尖锐起来。 争端与祸害 这是个人口流动性极小的村子。照老村长周来宏的说法,1981年他主持全村分地的时候,稻玉村三组是250个人,到1997年分地,15年间,人口变成了317人,仅多了67人,人口的增数完全来源于出生人口、嫁入人口与死亡人口、嫁出人口相抵后的净增长。周来宏说:“这里的社会关系极其单纯。” 稻玉村的集体生活尽管从80年代就已经瓦解,人们有了各自的小家庭和自我利益,这个过程并不是一步完成的。很多人还没脱离计划分配的习惯性力量,另一方面,这个偏僻山村资源的有限使人们仍要寻找某种集体生活和个人生活并存的折衷方案。它们给村子里未来的争端埋下了祸害。 稻玉村的用水问题就是一个常引发争端的领域。因为居住分散和地势原因,自来水在这里的推广并不顺利,大部分村民仍然使用深井水。比如,朱家、刘家要和其他30户人共用一个井。 由于其他普遍存在的偷水问题和水管老化使每个月的水价都有变化。“水要通过电泵抽上来,根据每个月耗电量的不同,水价随之调整。”一个村民说,如果一家故意欠费或者缺乏自律,其他家要为此分摊费用,由此引发的斗殴近年来在村里屡禁不止。 2002年,朱占功、朱景林和朱计功之间就遇到了类似争端。这30户人原先是雇用打井公司的人帮助抄表,每个月支付15块工资。后来,大家一商量为了省掉这笔钱,由30户人自己轮流抄表,一个月轮一次。轮到朱计功抄表的那个月,水费计算出了问题。之前几个月,一方水价是5毛钱,这个月一下子涨到了1.5块钱。用水的30户开了个会,认为要查一下各家水管,是否出现漏水。查到朱计功家,发现他家每月都少报了用量,水表一个月来积了80立方水。“30户都派代表讨论了,一致认为,朱计功要按多出的1块钱水价补给大家80块钱。”一个参与讨论的村民回忆说,“但朱计功坚决不交这钱。为此,刘春凡还跑到对门的朱景林家大骂,认为是朱景林以村长之权跟她家过不去,故意整她们。刘春凡的儿子还拎了把刀闯到朱家,虽然没动手,却把朱景林的老婆给吓昏过去了。”“这以后,这一家人的关系更是无法挽救。” 分地后患与修路 冲突更深刻的根源是当年土地分配遗留下的隐患。 在1981年那次对稻玉村最重要也是决定后来20多年利益格局的土地承包分配里,稻玉村的村民们用一种简朴的办法来做到分配里的公平 稻玉村的土地情况比其他村复杂。全村都位于丘陵地貌上,地势高低起伏,造成村里土地质量的差异非常大。“稻玉村没有外来人口,每一户几乎都是坐地户。这样,村里土地虽然面积不小,但对于稻玉村的人,就像是自己的儿子,哪里有个痣,哪里长个痦子,一清二楚。不能光按面积来平均,哪家分的地肥了,哪家的瘦了,肯定不行。”周来宏说,哪儿有一点做得不公道,都会出乱子,惹是非。 不过稻玉村向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这个略显沉闷的陕西村落是个疏离于财富、权势和影响力的地方,它形成了自己的智慧和规则。周来宏和村民们最后讨论出的办法就充满了原始数目字管理的精神。“我印象里没有哪一次分地,像1981年分得那样细致。”他说。 农民们最后以整整半个月用麦糠把每一块不同质量的土地都勾了出来,他们把勾出的上千块地根据产量分为四等:500斤以上的是一等地,350斤到450斤的是二等地,200斤到300斤的是三等地,150斤到200斤之间以及少量50斤的是四等地。他们算出全村所有四等土地的面积,得出总产量。根据1981年的人口,当时每人分到的产量是700来斤。700斤产量的土地组合则由抽签来决定。这样的公平分配带来的弊端,就是农民们拿到手里的地往往是极为分散的:运气好的,几块地还能邻得比较近;运气不好的,不仅土地分散甚远,还不成整块,极为零碎。 它的后续问题在于,根据土地政策对农村土地“三年一调”时,一些家庭因为增减人口的原因要退还村里一部分地,但因为地块过于零散,即使拿出这小块地也往往无法给别人耕种。周来宏说,这样,村委会决定拥有这些多余土地的农民可以不用回收村委,但是要按照每100斤产量上缴20块钱的比例每年给村里交纳承包费。 政策延续至今,这些地事实上缺乏有效管理。从1997年土地调整开始,那些多余土地已经基本就再也没有向村里上缴承包款了。它无形中,至少在承包者的心里,已经变成了私有财产。这些所有权不清的地,尽管总量有限,却迟早会引发冲突。它们像随时可能会被引爆的火药筒。朱家原本的家族恩怨和2005年村里突然开始的“修路”就成了那根引子。 刘智玉在1980年分地时比较走运,他分到的地比较集中,只有两块,最大的一块是果园,还有就是朱家门口那小块。 1997年土地调整时,按规定,刘智玉家有一个女儿出嫁,要退出一部分地。另外,照周来宏在任时定的政策,每家有小孩考上大学,不收回全部份额土地,应考虑上学用钱的因素,给小孩保留200斤产量的地。1997年,刘智玉家上大学的儿子毕业工作,当年保留地也要退出。两块加起来正好是7分左右大小。这块本应退回村里的地从1997年开始由刘智玉承包。这也是朱家坚信最终能要回那块7分地的原因。“本身就是多余土地,我们实际上只不过是跟村里置换土地。”朱海功说。 朱计功和刘智玉里外的强硬让这件事10年来僵持不下。直到2005年,周至县一则“各个村‘硬化出村道路’”的修路通知打破了平衡。如果不是修路,稻玉村的确很难会动到这些10年前的存量土地。村委统计结果,共有14家农民有村里的承包地,刘智玉家是其中之一。修路小组的负责人王文玉说:“村里想修路也是很多年的事情了。出村的道路泥泞、狭窄,因为村民的耕地,很多路段的实际路面不足3米宽。村民开会,大部分都是投赞成票的。” 王文玉说,一部分上级拨款和一部分村民集资都及时到位,修路遇到的最棘手问题倒不是资金。“3米的路面,要拓宽到5米,相当于把原来的村路延长的1.4公里,这部分道路用地需要占去农民用地4亩,村里需要拿出相应的地补偿给被占农户。”王文玉说,“因为土地质量的参差不齐,我们在补偿地问题上也承诺,‘占近地补近地,占好地补好地’。”
做起来并不容易。14家农民的承包地都比较分散,“让他们把吃进去的地再吐出来,动员工作并不好做”,王文玉说,态度最为强硬的是刘智玉。 刘智玉的抵触有明显私人恩怨掺杂在里面。他当然知道,朱景林将自己在路西的地腾出来给村里修路了,而朱的意图很明确,希望村里把刘智玉的地换给朱家。 刘智玉在反复交涉后做出让步:可以退出多占地,但只能让出果园的一块,不让门口的。“果园那块地很远,朱景林当然不答应,也不符合我们一开始讨论的补偿原则。”王文玉说,修路小组向村、乡、县逐级申请了土地强制执行令。2006年2月,王文玉和稻玉村副村长带人到刘智玉和朱家分界线上栽了“界石”,正式确定了那块“7分地”的所有权。“没想到,第二天,刘智玉的儿子就跑到我家,在我屋子中间挖了个坑,放块石头。”王文玉说。 这只是稻玉村一系列冲突的开始,朱家和刘家的矛盾再次升级。几个月后,刘家带了十几个人砸了朱家,双方在这场被称为“周至县建国后最大规模的械斗”中两败俱伤。朱家的几个人受伤被送进医院,刘家的三个人被警方抓了起来。 之后不到一个月,朱景林死了。警方在随后的侦查中确定,让朱景林致死的是一种常用有机磷农药,基本判断是人为投毒。刘春凡于是被警方传唤协助调查,25天后,她被释放,警方找不到足够物证。一名村民说,比起已经有了明确凶手,不知道凶手究竟是谁,他们现在内心更加不安。流言在私下里盛传,大家都怕祸及自身。他们担心,这个家族的仇恨已经失去了控制。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