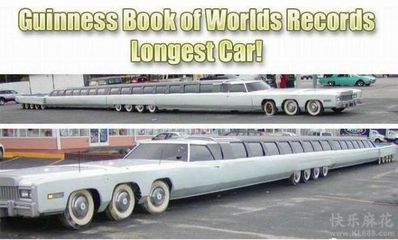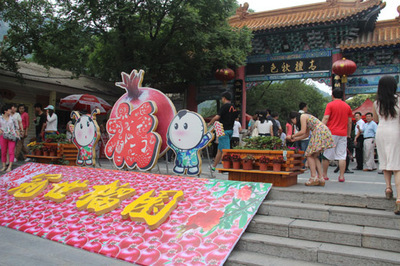诺曼人现在在地图上是找不到了,这是征服者的命运,但你不知道这颗星球有多少人身上流着他们的血液,那条基因的河流边界在哪里?
撰稿/边芹 旅法作家
顶着时间为我预置的沉默,我已经不以年作希望的代码,我的思绪是百年一个台阶,千年一个槛。我也说不清在第几个台阶上,总之文明城堡被攻克时,从来是无声无息的,大众在庆功的歌舞升平中陶醉,他们在血泊中也同样会陶醉,他们看不见早已暗中设计好的棋路,也意识不到被偷换掉的棋子,他们只有他们的本能:站在胜利者一边。 我最近连看了几部欧洲考古纪录片,多半是偶然挖到个远古墓穴,一般都在纪年前一千年,甚至更早。以为消失了甚至根本不知其存在的文明,却深埋在某处,我对这样的谜百嚼不厌。看多了便发现文明的裂口——新涂油漆下面的裂口:掘出墓穴的地区现今生活着的人群,与墓葬里的精制文明挂不上钩。你只要把眼睛从地下向上挪,便看到了惊人的裂缝:这些浑浑噩噩的人群,数千年前创造过那样的文明?事物与轨道有时会出人意料地错开,埋藏在地下的文明越辉煌,发掘的地区越落后,有些从文字到历史都与现今处在它数米之上的人脱了干系。真让人愁肠百转! 8月末,追着即将钻入秋景的暑气,跑到巴黎西郊圣·日尔曼·昂莱城堡,转了一圈考古博物馆。那地方游客是不去的,时常是我一人穿行在石、骨、铜、铁、金这些远古的遗存物间,有彻骨冰凉的醒悟,仿佛一身的血肉被卸掉,只隔着一副骨架,去拂拭构筑时间的那些无用物品。高卢这块地方,别看现在摆出这么副天下无物的架势,地下可没挖出什么宝。记得我从前在国内往西北跑,直遛到马步芳的旧宅才找着西宁博物馆,里面人影晃不出半个,灯都懒得开,我探进身子,一个乡下妇人从暗处站起来,迈着蒙古种特有的提不起的步子专为我开了灯。法国这家考古博物馆,若只算地下挖出的东西,也就差不多西宁的水平。卢浮宫、吉美博物馆的丰厚,都是从别人的地下搜罗来的。有很多地方是地下比地上富贵,这里正相反。千万年后,地上的翻到地下,那才是文明的一页,两百年论成败,还是心急和自负了一点。 我最后看的那部纪录片,讲保加利亚发掘的一个墓葬,距今也有三千多年,只是挖出的东西手工之精,尤其是金器,直让你扣心自问:人在三千年的淘洗中究竟光亮了多少?时间是无法为金器点上句号的,那专制的手随意涂抹其他材质,到了它面前就难下手。所以我看着挖掘者轻轻把它们身上三千年的尘土弹去,时间未能添加任何多余的装饰,那面具隔着千年隧道也没有收敛嘲笑世界的目光。你再看生活在地上的人,以及围绕着他们的物品,才意识到文明不知何时已被切断,切断的时候细语轻声,并非改朝换代那般突兀,时间跨度可能数百年之久,一点点褪去颜色,不知不觉就换了模样。野蛮人蚂蚁一样攻占了城堡,血液被稀释,城堡坍塌时,文明已经大半个身子入土,但攻占者继续在废墟上繁衍,然后又有新的劫掠者参与其中。基因的河流没有别的秘诀,就是纠缠、混杂,流向所有可以流经的地方。 这是所有清醒而精制的文明之结局——被偷梁换柱。这个世界有财富的战争,还有暗中进行的基因的战争。说文明越走越灿烂是痴人说梦,只是它的堕落没有几人看得见,那自由落体的感觉几乎让所有人迷醉,这让我时常有被时间岩石预先埋葬的感觉。基因的游走,在哪里被截住,又流向哪里?你以为确定的事,并不确定。法国有一个著名考古学家,他说自己一直自认地道布列塔尼人,因为母亲是那里人,但某天他的美国同行从他嘴里搜集了一点口水,拿去实验室,不久便告诉他,他的远祖来自亚洲。我那天听了这话,细看他的面相,每一根线条都好像远古先人走过的地方。布列塔尼这块伸向大西洋的尖地,分布着诺曼人的后代。读爱默森《英国人的灵魂》时,看过对诺曼人的描述,这是个强盗民族,查理大帝有一次望着打劫完的诺曼人驾船离港,直掉眼泪,因为他想到他的后人遭遇这样的民族,是要倒霉的。这个征服者民族是今天统治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远古先人的构成之一。后来的确大半个地球都遭了殃,可见查理大帝的眼泪之英明。诺曼人现在在地图上是找不到了,这是征服者的命运,但你不知道这颗星球有多少人身上流着他们的血液,那条基因的河流边界在哪里?看不到那暗流,你没法确定你从哪里来,你也不知道那些埋藏在地下的文明游走到了哪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