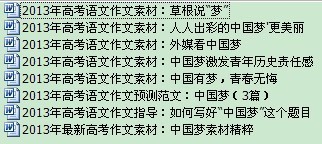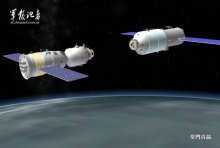通过拍摄艾滋病纪录片及公益广告,奥斯卡女导演找到了与中国新的心灵对话
作者:雷晓宇
杨紫烨不习惯穿高跟鞋。今年2月26日,当她从洛杉矶柯达剧院的最后几排座位上站起来,沿着台阶、红地毯和追光灯走上奥斯卡领奖台的时候,欢呼和掌声之类的声响都消失了,她只觉得,这条路怎么这么长,杨紫烨你最好快点走到头,别当众摔倒出洋相。 这个夜晚,杨紫烨凭借中国艾滋病题材的《颍州的孩子》拿到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奖。 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华文媒体《世界日报》说:“如果说,股市的一天暴跌,北京可以用庞大的资金来入市托股,第二天就可以全盘翻红,继续营造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的盛况,那么,艾滋病的防治,就绝对需要漫长的奋斗过程,才能出现成效”。 奥斯卡逼着杨紫烨回答一个问题——杨紫烨你到底是哪里人?香港?美国?中国?还是北京? 杨紫烨没有答案。 她出生在香港,但20岁就离开了香港。她没在香港工作过,不是名符其实的香港人。“我是在美国成为杨紫烨的,在香港我只是个孩子。” 她说自己早在20年前就已经“成为美国人”了,但她却在2004年和丈夫卖掉旧金山的房子到北京拍公益广告和纪录片。3年来,杨紫烨开始爱戴帽子。三次见她,她都戴着不同款式的毛线帽。“因为紧张,压力大,掉了很多头发。”虽然她说自己并不后悔,但是至今她的普通话还是很烂。她只要一开口,还是个外来者。 她说,如果自己的前半生要写自传,应该从两个时刻写起:1977年移民美国、2004年来到北京。前者是她的美国梦,后者是她的中国梦——做美国梦不如做中国梦,要成为美国人先成为你自己。 “如果今天我20岁,我可能根本不会去美国,我的梦在中国就能实现。”她说,“而且还更快,不用皓首穷经。我在北京工作三个月等于在美国工作一年,天上人间。” 香港故园 1977年夏天,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一年级学生杨紫烨开始了她的第一个大学暑假。她知道,她就要和父母一起离开香港,移民到美国旧金山了。 所谓乡愁,是很后来的事情了。美国令她兴奋,因为学商是母亲的主张,她自己根本不喜欢。她和父亲一样,喜欢写字、画画、披头士、猫王和好莱坞电影。她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但是她模糊觉得自己要做“艺术之类的事情”。她想,也许美国能够改变自己的未来。如果留在香港,自己会像母亲,如果去美国,自己会像父亲。 父亲是中山大学化学工程专业毕业生,但是一辈子爱好艺术。抗战的时候,父母从桂林逃难来香港。一开始,父亲在亲戚的一家工厂帮忙。1956年,父亲凭着专业知识和好英文开了一家小工厂,母亲管财务。 第二年,杨紫烨出生了。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和父亲最像,也最受父亲宠爱。后来的一生中,杨紫烨和母亲的关系总是若即若离。她从父亲那里得到了理想,从母亲那里得到了强势和固执的个性。 杨紫烨成长在香港的六十年代。“和大陆的八十年代很像,这是一个变化的、起步的社会。虽然贫穷,但是人情味很重,而且人们都是充满希望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头开始。” “香港在五六十年代开始有很多家庭工业,李嘉诚也是这样开始的,我父亲也是。”当然,父亲最后并没有成为李嘉诚。1967年,香港发生反英抗暴运动,示威者的“土菠萝”(一种自制炸弹)扔到了杨家附近,改变了这个家庭后来40年的命运。 这一年,杨家把大儿子送到美国旧金山留学,大女儿则去了澳大利亚。又过了10年,杨家把工厂生意结束,举家投奔旧金山的大儿子。 很奇怪,离开香港的那一天在杨紫烨的记忆里已经无影无踪了。在2007年冬天,她怎么也想不起来当时是怎么扰攘,怎么和同学告别,又是怎么登上飞机的。但是,美国在她脑海里留下的第一个画面却一直都在——“飞机直接飞到了加州,那是个夏天,天气特别好。一下飞机就上了Freeway,没有什么人,不像香港很挤。高速公路好长好长,好像路永远也走不完的感觉。” 20岁的杨紫烨满怀梦想,投奔她心目中的麦加圣地。“那里什么都有,你可以选择任何你想要的。那里什么都要,任何植物都能在那里生长开花。”那个时候的杨紫烨想不到,30年后她再次谈起香港的时候会激动到流泪。 现在,杨紫烨坐在我面前,跟我说她的纪录片处女作《风雨故园》。我不能肯定她是不是真的哭了,但是她的眼睛是湿的。她在自己的工作室里不停地调整自己的坐姿,似乎有些东西总也难以安放。
《风雨故园》拍摄于1997年,是杨紫烨的纪录片处女作。“我虽然以为自己早已成为美国人了,但是自己第一部作品还是去了自己的故乡拍,我还是和别的美国人不一样。” 那一天,她在九龙拍摄驻港部队。香港7月的第一场雨里,视线突然恍惚,镜头慢慢拉远。莫非这是小时候?那时候,父亲每年都带她去看英女王授勋游行。一二三四,立正,稍息,每一个都是精挑细选的好看的战士——历史在杨紫烨的记忆和镜头里重合了。后来,她把这两段相隔30年的镜头剪接在一起,《风雨故园》成为美国多所大学的亚裔研究教材。 归属感?“不知道。照理说应该有,但是我已经在美国住了20年了,我的家在哪里?我不知道。中国人说,关山万里,哪里都是我的家。” “我爸爸对于回归是很期待的,但是那时候他已经不在了。我妈妈在美国看电视。他们对于香港有感情,他们白手起家是在那里。但是他们真正的家在大陆,他们一辈子也不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美国人。你最好的时光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家。” 美国有多美 一到美国,杨紫烨做了两件事:和父母在华人社区安顿下来;选择去旧金山艺术学院学习艺术。前者是她不能摆脱的过去,后者是她必须面对的将来。 七十年代末期的香港正处于经济起飞的前夕,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但是一到旧金山的唐人街,杨紫烨仍然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旧,凝固,几十年没有改变过”。 “唐人街有很多孤独的老人,很多都是三十年代过来打工的,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不会英文,也没什么钱,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唐人街的10个Block(街区)。他们的一生再也没有将来,也没有根。” 杨紫烨后来嫁给了也来自香港的同学任国光。丈夫在唐人街工作,做摄影、艺术院线发行,所以她经常去唐人街,每天都和老人接触。1990年,她在讲述中国移民到旧金山的历史的纪录片《铭刻在心》中担任剪辑,该片获美国艾美奖。 现在,她正在制作一部关于唐人街老人生活的纪录片。她坐在剪辑台前面,一张张黑白照片在荧幕上飞快闪烁。 “这些老华人对我有很大的影响。香港虽然是个移民城市,但是有活力,你有很多方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要你努力工作就可以了。这点上,香港梦和美国梦是相似的,只不过在七八十年代的美国,这个梦不一定那么容易成功。” 其实,杨紫烨的美国梦在她刚到美国的那一年就迅速经历了一次破灭和重生——她从电视上看到她最爱的猫王去世。不久之后,她又看到头戴牛仔帽的邓小平。同一年,《星球大战》上映,她要和卢卡斯、科波拉做同行了。 1982年,杨紫烨大学毕业,开始跟着导演王颖工作,一开始她做剪辑,后来她成了好莱坞的“剪辑皇后”,她的作品包括《喜福会》、陈冲的《天浴》、《纽约的秋天》等。 杨紫烨的生活离父母的唐人街退休世界越来越远,《喜宴》和《喜福会》中的代际冲突一再发生。 写《喜福会》的女作家谭恩美最喜欢《绿野仙踪》,片中小女孩桃乐茜那双“能载主人到任何想去的地方”的红宝石鞋令她神往。杨紫烨也有同感,她一直在遥望中国,2001年拍了反映新一代年轻人及城乡不同家庭面貌的《中国一二》,2003年参与制作以美籍华人为主题的《成为美国人》。最终,“红宝石鞋”载她回到中国。 “海客”谈“颍州” 2000年的一天,一阵敲门声把杨紫烨从工作中拽出来。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年轻人站在门口问她:“你是中国人?会讲中文?帮我个忙好吗?我希望你帮我剪个片花,我好拿去找投资。” 这个年轻人是百度创始人之一徐勇,当时他想拉投资拍摄这部名为《走进硅谷》的纪录片,好回国卖DVD挣钱。事情的发展出乎他的预料。 “他后来老说,这个片子成了百度的历史之一,是百度成功的第一步。通过这个片子,他认识了很多硅谷投资人、VC,和RobinLee(李彦宏)也是这样认识的,从片子慢慢聊出来百度创业的想法。百度的第一个VC就是看了这个片子才投的钱。” 杨紫烨感受到了商海氛围。“当时是硅谷创业的高潮期,很多大陆来的华人都创业——他们和以前的华人完全不同,他们是北大清华的华人,新的华人,他们不用讲很好的英文就已经有人请他们工作。也没有歧视,因为IT业就是从华人起来的。” 真正影响杨紫烨生涯的是纪录片《成为美国人:华裔的经历》(BecomingAmerican,TheChineseExperience)。杰出美籍华人组织“百人会”协助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作家比尔·莫耶斯筹款拍摄,杨紫烨做剪辑工作,该片2003年在美国公共电视台(PBS)播出,反响甚大。 在杨眼里,比尔是一个有思想、有绅士风度的典型的美国南方男人。他老给她看当年他和美国第36届总统林登·约翰逊的合影——约翰逊正在签署一份文件,他的新闻秘书、年轻的比尔就站在身旁。这份1965年签署的文件就是“移民改革法案”,它促成了六十年代主要来自中国台湾的留学热潮,开启了华人移民的第二波。 面对贝聿铭、马友友、何大一等“百人会”成员,比尔在纪录片里提出了几个问题:你成为美国人了吗?你是什么时候成为美国人的?一个典型的美国人是什么样子的?为了成为美国人你要保留什么放弃什么?最后他问:既然你已经成为美国人了,为什么还是不断有人问你——你从哪里来? 这些问题,比尔从来没有问过杨紫烨,杨紫烨也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她只知道,“你从哪里来”是所有亚裔永远无法逃避的问题。她在美国生活了快30年,还是经常因为这问题感到厌烦。 “但是这并不重要了。因为今天的梦不一定是美国梦,也可能是中国梦。而且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美国梦,今天硅谷的年轻人可是个个都想做RobinLee、JackMa(马云)。” 杨紫烨的窗外是北京建国门的标准商业风景,这时候遥想30年前那个年轻女孩的夜晚——“一群旧金山的年轻左派,躲在地下室里喝酒,听披头士,念金斯堡的《嚎叫》。有一个美国朋友送给我一本英文版的《易经》,我现在还经常看,好平静下来。” 也是这个时候,杨紫烨看了《在路上》——“这本书无意之中成了我后来人生的《圣经》。” 世事变迁,当年的嬉皮士成了雅皮士,反叛变为救赎。2002年,杨紫烨无意中在美国报纸上看到了关于中国艾滋孤儿的报道,她有一种冲动。她很快写了一份到中国拍摄的策划书,给各种基金会写信申请经费,但未果。2004年突然有了转机:中国卫生部与美国NBA一起合作拍摄艾滋病公益广告,杨紫烨被邀请执导。 当姚明、约翰逊参演的公益广告播出后,杨紫烨的困境迎刃而解。她得到了前AIG主席莫里斯·格林伯格的斯塔尔基金会(StarrFoundation)及Give2Asia基金会的资助,后者获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捐助。 她也回到了中国,与制片人托马斯·列侬发起民间机构“中国预防艾滋病宣传制作(CAMP)”。在何大一的支持下,她到安徽阜阳市颍州地区拍摄了艾滋孤儿的真实生活。之后她还导演了感染艾滋病的女大学生的纪录短片《朱力亚的故事》,《彭丽媛携手抗击艾滋关爱儿童公益广告》也出自她之手。 至少到2008年,杨紫烨还会拍公益方面的纪录片,但也将拓展到卫生、环保等题材。已有内地企业家承诺对她出资捐助,她也将拍摄企业家的故事,从企业家口中谈艾滋病患者的工作权利,主题仍然是反歧视。 当初冒着“40岁时人生从头再来”的风险来北京,杨紫烨的冒险成功了。“可能以后会平淡过下去,可能几年后再回美国,都可能。我香港的同学们都是银行家和律师了,她们总问我,你怎么这么伟大,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可我还不够中产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