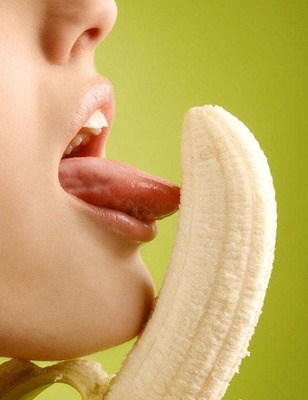BY马莅骊

第一次吃到蓝莓是在英国。Tesco促销哈根达斯的冰激凌,五镑两大盒,比上海卖得便宜多了。一咬牙,初来乍到的三个穷学生合买了两罐回去,其中一罐就是蓝莓口味。我真的,真的非常认同《蓝莓之夜》里诺拉·琼斯的选择,蓝莓那甜甜酸酸的口味,像极了久违的爱情。 对王家卫的电影,我一直都没有大的期待。不多的期待里,还有一部分是等待某个警句的出现。诺拉走了500多天,她不得不停下的时候,裘德·洛在咖啡店里守株待兔似地等待着心上的姑娘回来。在等待中,诺拉告别了过去的日子;而等待,造就了裘德现在的生活。思念让等待给人安慰——“当你离开的时候,关于你的记忆,创造了别人的生活。”这一句台词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该松口气了。 因为诺拉·琼斯,不由得想起王菲。因为王菲的表演,《重庆森林》的后半段流露出一种释然的天真,这种感觉很像是玛丽莲·梦露留给世人的印象:感官成熟,表情天真;虽然王家卫和梦露完全不搭调。可是诺拉·琼斯没有像王菲那样给人惊喜。她扎着马尾辫表情严肃地站在吧台后面。我忽然觉得她很像《迷失》里面的女警察安娜·卢希亚。这真是最适合诺拉的角色吗?也许王家卫搞错了,也许他成了一个对自己的模特缺乏激情的画家,剩下的只有技巧和他自己。 《重庆森林》之后,那种释然的天真感,在他的电影里却越来越找不到了。这也难怪,天真原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世界上只有一个玛丽莲·梦露,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同样的道理,世界上也只有一个王菲。在那以后,他越来越像经营一桩了不起的事业一样,经营着自己的警句。那些警句原是已经成为过去的诗歌在电影时代的余绪。靠着这些诗歌的残渣,他成功了。他把自己经营成了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底下,我们默许了那些孤独的人们,寂寞的眼神,夜景,路景,被强调了的数字、钟表或者钥匙,无意义的对话和有意义的独白,还有奇特的叙述风格。 《重庆森林》之后,我觉得再也难以去评价他的电影,因为那里面总有我看不明白的地方,他就像一个谨慎的男人,在爱人面前也要小心翼翼地选择自己的措辞。太谨慎了,就显得……刻意。 据说《蓝莓之夜》源自他多年前的小说。看来他终于决定突破,或者说妥协了。不再极力发挥诗的残章短句,破天荒在开机前写好了剧本,开始老老实实地讲故事。这个故事顺叙到底,情节简单(诺拉·琼斯绕了一个大圈子过马路),所以只讲了90分钟。 诺拉·琼斯、蕾切尔·薇兹和娜塔丽·波特曼都在戏里哭了,这似乎值得记上一笔。蕾切尔·薇兹展现了她难得的放纵和憔悴,人们有时需要靠互相折磨来证明彼此相爱。表演一贯收放自如的娜塔丽·波特曼第三次和裘德·洛出现同在一部电影里,这次却连对手戏也没有;而诺拉却和裘德吻得天翻地覆,我并不觉得那个被百般渲染的吻特别迷人,但我喜欢琼斯的绿色绒线帽…… 我们也不要追问为什么是蓝莓。对于美国人民来说,蓝莓不过是他们最熟悉、最心爱的水果之一,非常符合王家卫初次闯荡好莱坞的姿态。而对追捧王家卫的上海女观众来说,这个舶来词,让人平添了几分远距离的暧昧想象。舶来不舶来,差别是很大的。或者,人性就是这样,眼皮子再深,终究还是浅。我还记得有个下午不巧坐上了一辆陌生的公交车,在一个陌生的站头下了车,刚刚一抬眼,看到街的拐角处站着一座颜色寡淡的老式大楼——哦,原来上海也有重庆大厦……那一刻,尖沙咀弥敦道上王菲的重庆大厦顿时在我心里褪色了许多。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