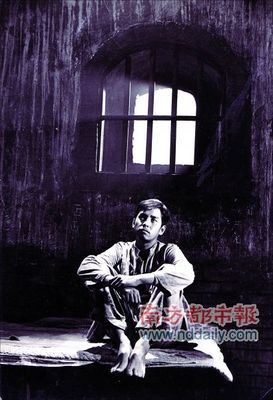◎罗四 在我最着迷王小波的时候,相信他说的一切。他说讨厌张爱玲,我就讨厌张爱玲。王小波是学理科的,学理科的人不承认有牢不可破的囚笼,更不信有摆不脱的噩梦,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我看到这句话禁不住热血澎湃,觉得他说得太爷们了。其实当时我也是喜欢张爱玲的,只是从此耻于承认。就像上学时耻于承认自己也看琼瑶一样。 我一直以为张爱玲够狠,后来看苏童的《米》,不得不承认,哪怕再阴柔的男人,还是比女人狠。南方作家气质普遍阴柔,当年看完《妻妾成群》,抬头看天都是油荫荫的,虫叫都透着湿气。《米》就像一把软刀,慢慢刺人肋下,冰冷不留半点温情。别人家里的饭香,别人房里的灯光,别人的心跳,别人的闲适,都能构成整个世界的敌意。在这种整体敌对中,只有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米是依靠,是温暖,因为它能让人不饿死,在这种状态下的人,已经承受不了任何思想,任何感情,这是另一种状态下的命若游丝。

张爱玲有一句话,中国处处是肮脏的角落,可也处处都有爱与忧伤。其实张爱玲并不狠,她只是一个小女人,她一直做的事,就是在肮脏的角落里捡拾爱与忧伤。可是苏童连这些也不捡拾,他只是带你去看灰蒙蒙的大地,灰蒙蒙的男人和女人,地上都是灰蒙蒙的灰,一层一层,扒到手指出血,灰里也不会开出花来,因为灰不是土壤。看完《米》我一度很苦恼,是不是人出生在什么阶级,就永远被打上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终生也摆脱不了。人们都爱讲“人性未泯”之类的话,其实人性与兽性相比,真的是暗流与杯水之别。人若能有片刻游移出人性,从另一个澄明和陌生的角度看自己,是不是得到的不是解脱,而是更痛苦的体验。看完《另一种妇女生活》,这种绝望到达了顶点,忍不住喊出来:本来不必这样的!喊出来之后,忽然清明了。就好像水池被堵到透透,一下子通了。在通透之后我有点想明白了,不管是《米》、《妻妾成群》,或是《一地鸡毛》们,它们的诞生,鸡毛的铺天盖地,也许只为逼出这几个字:本来不必这样的! 王小波厌烦海船一样的幽闭小说,可是现实中,大多数人都是待在船上的,肮脏、四处是幽闭角落的船上。假如澎湃的想象力是海,这片海也是能逼死人的。“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这句当年让我热血上涌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单纯的理科生的单纯想法。任何事都可以是无边界的领域,只是光有澎湃的想象力是不够的,还需要澎湃的行动力。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