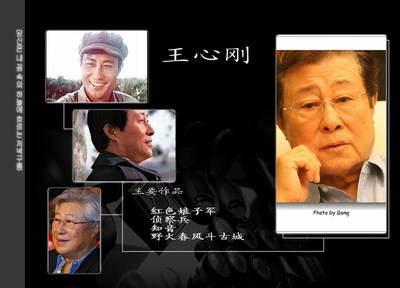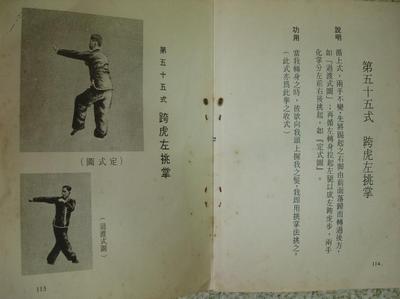不管是火爆还是阴噱,内核里面都是含有非常厉害的机锋的,棱角锋利,都包含了表演者对于生活深刻的观察和他自己的或针砭或褒奖的态度。
撰稿/陆幸生(记者)
草根的机锋 王汝刚拿着手机,人们熟悉的脸上没有呈现被唤作笑容的那种“松散结构”,他颇显疲惫地说着:哎,是的,我上趟电话托侬买火车票的事情,侬搿搭这里 一定要抓紧,哎呀,是个呀,我晓得老紧张老紧张的,老紧张才寻到侬;人家要回去过年的,爷娘在老家等着的,侬一定想想办法,想想办法。临了,王汝刚还要加上一句:帮帮忙,看侬的了。他看看等待中的我,摆摆手,以示对不住的意思,他继续拨了第二个电话:哎,侬跟我讲的车票的事情,我正在帮侬联络,今年车票实在太紧张了,太难弄了,人家答应帮忙,不过事体要做起来看的,有消息我马上会告诉侬的。 王汝刚终于收起电话,对我说:每年都有这样的事体托过来,人家打工难,回家也难,买张火车票,今年是“少有出见”的难,这张车票难弄啊。我对他说,真是老上海闲话了,少有出见,现在难板(很少)听得见。王汝刚大概是刚刚从买票难的“规定情景”中“醒过来”,脸上方才浮起一点笑容:这倒是的。 王汝刚白天开人代会,坐在主席台上,电视屏幕上出镜,面相规规矩矩,形体动作是一个也不能有的。晚上约定的采访主题是“上海的笑话”,他从会场直接赶过来,先是老派地抱拳致歉,对不住,让倷等了交关辰光;接下来就是打电话买火车票。 后来,王汝刚的儿子告诉我,类似“托过来”的各种事体,蛮多,我爸爸总是能帮就帮,能做就做,总归是人家相信侬;自家屋里人倒是不太能叫他办什么事体的,一个是看到他忙,想想他介吃力,就算了,实在有事体,告诉了他,弄弄就忘记掉了,没忘记,也经常拖得没有个时间。“不好照伊牌头的”。却原来,生活中的滑稽演员也经常在碰着很多并不滑稽的事。 话题就此开头。说到北边相声南方滑稽,“老里巴早”前辈人的叫法是“穷不怕”和“小热昏”。我说,好像北方人比较强悍,只要有口饭吃,就要荤的素的各种段子,都拿过来说说,一是泄泄心头之气,二是撩地摊,挤个小小的地盘,能挣几个小钱就挣它几个;还有个意思,人已经穷到根了,讲错几句也不要紧,“里面比外边强,还管饭呢”。南边的小热昏,听上去就比较胆子小,开口就是先认个自我错,嘲笑自己是有点小毛病“热昏”了,说点胡话是认不得真的。王汝刚微微笑道:比起有点拍胸脯腔调的穷不怕,小热昏就比较内敛,显得比较“策略”;还有,因为策略,就从容。我说,只是一个穷一个小,都表明了这是出身于平头百姓的谋生方式,都是很草根的,把这些说成艺术,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接下来,王汝刚就用行话来解说这两者间的一些区别。北边讲,相声是说学逗唱,南边讲究的是说学演唱;北方是逗,南边是演。逗的表演方式显得姿态主动、动作夸张,总体上气氛火爆,而演,就是演角色,是相对客观的一种模仿,是“不是我”,在舞台特征上就显得比较“温”,滑稽戏里唤作“阴噱”。不过,王汝刚话头一转,不管是火爆还是阴噱,内核里面都是含有非常厉害的机锋的,棱角锋利,都包含了表演者对于生活深刻的观察和他自己的或针砭或褒奖的态度。当然,更多是对于生活的描摹,有的是场景本身含有幽默的因素,“有荤有素”。 说到当年中国人抵制日货,滑稽前辈刘春山上台就说“东洋花布”。刘春山:最近市面上有种花布交关便宜。 盛呆呆:不用多问,肯定不是国货,一定是东洋花布。 刘春山:你讲得交关对。 盛呆呆:说明我们中国人都有爱国心,爱国的人不会去买东洋货。 刘春山:这倒不一定,也会有人去买东洋花布。 盛呆呆:还有这种人?哪能一点也不爱国。 刘春山:你冤枉人家啦,并不是他不爱国,而是家里死了人,死人临终吩咐过,东洋花布便宜,穿到棺材里合算。 盛呆呆:哦,原来买东洋花布的人,都是因为家里死脱人了。 刘春山:对,啥人穿东洋花布的就是死人,即使有些穿东洋花布的人,看上去还没有死,其实伊拉的头脑早死了,也只好算个活死人。 此地的对话,哪里是点到为止的讽刺和诅咒,这已是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抗议,以至抗争。在当年租界,在公众场合发出这样勇敢的声音,立即使其成为当年上海孤岛市民的流行语言。南方人何曾胆小,小热昏何曾热昏,“唱独角戏的,敢说敢为,人一横,心一横,凶啊”。 草根的坚持 作为1968届的王汝刚回忆道,阿拉小辰光,根本不用说是电视机了,普通老百姓屋里有只把无线电收音机,也已经算是有铜钿人家了。不像现在,电视机一日开到夜,根本不考虑电费开销,那时候是到辰光听节目,越剧有越剧辰光,滩簧有滩簧辰光,滑稽有滑稽辰光,评弹有评弹辰光,侬屋里开了无线电,声音一定要拨得响,好让邻舍隔壁都听得见,大家一道开心开心。噢哟,又是姚慕双周柏春么,噱格。上海是个商业城市,南京路淮海路店家门面连着门面,辰光一到,不同店家里收音机一起打开,听的是同一只节目。那时候还有人踏的交通工具三轮车,这段辰光车夫是不大肯拉客人的,做啥?车子拉到树荫里,听听店家里传出来的滑稽双档节目。“你看,滑稽戏场面大啊。” 王汝刚说,对那个时候的角儿,老百姓是只认得声音,不认得面孔的。所以,当年演戏会那样子轰动,“去看人呀”。现在电视机里的头像,比真人还要大,到电视台门口轰来轰去的追星族,都是年纪小来兮格,当初买票到剧场里的,都是上班族,有点年纪的,不是坐办公室的,就是车间女工,赚的都是辛苦铜钿。从薪水里拿点出来,偶然看场把越剧和滑稽戏,就是大消费了。 北方相声和南方滑稽,都有模仿各地方言的传统,从说话的内容追溯下去,节目中的各地方言似乎都带有自家最初职业的痕迹。绍兴衙门师爷、安徽劳动大姐、苏北剃头刀什么的,辛苦谋生的移民经历都凝固在这方言里了。北方相声学唱上海越剧“小别重逢梁山伯”,南方滑稽学唱京剧“坐在城楼观山景”,其中的地点、人物和故事缘起、场景,简直是千差万别,共同点是彼此都模仿各种各样的别样戏曲。只是,上海滑稽的“学英文”,却是任何别的地方戏曲都没有的绝活。王汝刚“左想右想”,然后肯定地说:外地就是没有的。 从19世纪开始,上海就是开放城市了。这是处于中国长江下游这座枢纽城市的必然命运,这是境外资本势力为追逐利益而扬起炮口下的被迫洞开,然史学有史学的记录,民间有民间的临摹。像“剥了皮吃,吐了核吃,剥了皮吐了核一囊一囊吃”,如流水一般熟练地倒背英文26个字母,上海市民对这些熟悉到了耳朵起老茧的地步,此中基石般的原因是上海地界一百多年来的华洋杂处,沙逊大厦门口站立红头阿三,国际饭店进出洋装瘪三,是彼此交流的需要从而诞生了这一幅世俗风景。有点陌生,有点追逐,有点洋洋得意,各种况味都在里面了。 上海滑稽从来就具有多副“面具”,有时西装革履,也有长衫马褂,更多的是升斗小民的生存百态。即使小热昏的闹猛有点拘谨,小热昏的讽刺有点躲闪,但是小热昏从来就不躲避反映自家生活的艰辛,从而以“远兜远转”的坚韧为长,以“面熟陌生”的勇敢著称。经典的滑稽戏《72家房客》就是这样的杰作。王汝刚就曾扮演其中小皮匠的角色,与同样底层的邻居一起,嘲讽和捉弄了有产阶级房东炳根与二房东。当年上海逼仄的空间,当年百姓不屈的抗争,在这出戏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也许滑稽在生活中并不“实用”,但是心理宣泄和按摩作用,显而易见。雅艺术和俗艺术的根本作用,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还有滑稽段子《三毛学生意》,讲的是剃头,实际体现的是进入上海的外乡市民,从头做起的谋生长途。在这个学习理发的段子“身上”,我们还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这个节目的长盛不衰,其实有着一个上海源远流长的“第三产业”背景。 草根的效应 在世俗生存的缝隙里,沪语滑稽在调慢着南方都市居民的步履节奏,有着一种落地而坐,喘息一下的放松姿态,在咀嚼回味包容在曲折和苦涩之中的点滴笑意。尽管,这种笑意有时有些勉强,有时的确就是自嘲,但只要是一种人生心绪的释放,过后跟着的就是站起身来,继续前行。 眼前的王汝刚说到老搭档李九松的一段经历。有一次,豫园商厦想成立一个豫园足球队,东打听西参考,讲好的说到了天上,讲孬的落到了地上,弄得领导心里七高八低,长久无主意。碰到李九松,叫他“谈谈利弊”。 李九松“低眉顺目”地轻轻一句:领导,阿拉豫园搞足球队,我看要弄得手忙脚乱的。也许是李九松讲得过于概括,领导要求“解释一下”,踢个球怎么就会手忙脚乱?李九松细细道来:豫园都是小商店、小门面,一手钱一手货,做的都是一元、二元,甚至只是几角钱的小生意,一天做到夜,手里忙是忙得来,做么做不多。弄支球队,从球衫裤子、袜子鞋子,要统统齐备,否则像个杂牌军;还有出行费用,踢了球还要营养营养,多吃掉点钞票。哦,赚么赚不多,脚底下动一动,交关钞票就出送了。这样就是手里忙脚下乱,弄来弄去一场空,我看是不合算的。 领导决定,从此不提足球队的事情。还说,东家长西家短,不及李九松一句闲话,“手忙脚乱”四个字。 王汝刚解说,李九松的这段故事,相当充分地说明了滑稽演员的职业素质,那就是敏锐的观察能力和反应能力,还有所谓的接口令,就是最充分的概括表达能力,要是啰里八唆,版版六十四讲不清爽一桩事体,吸引不牢观众,人老早走光了。 十年劫难过去,上海滩上流行过一只说唱“毯子身上盖一盖”。说到这里,王汝刚和我同时地笑出了声来。上海说唱曾被“四人帮”说成是“九腔十八调”,不入流,著名演员黄永生也就此被打入另册。时令翻改,节气转换,黄永生就是采用上海说唱这样通俗的方式,狠狠地揭示和嘲讽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说唱节目名字是老的,叫作《古彩戏法》,内容是崭新的: 锣鼓敲惊咚惊咚惊咚呛 喇叭响咪哩嘛啦咪哩嘛啦蛮闹猛 吹吹打打就是张、姚、王 一场古彩戏法开了场 主要演员是江青 她变戏法手段实在强 自编自导自家演 涂脂抹粉自家化装 今朝伊穿之吕后的百褶裙 披之武则天一件绣花蟒 慈禧太后的凤靴脚上穿 妖形怪状来亮相 毯子身上盖一盖 变出了黄金万两 只要紧跟老娘 包你有福同享 紧跟我可以当部长 大热天送你一个电冰箱 进进出出是小轿车 再送你一套花园大洋房
毯子身上盖一盖 变出了帽子钢铁两爿厂 啥人要反对老娘 也有礼物重赏 一要记账两要下放 三要帽子戴上 四要……哼哼请你去坐班房 其中最引人发笑的一节,就是“街头贴标语”,本来是上海民兵“坚决要求张春桥当总理”,在心急慌忙当中方块字被前后颠倒,贴到墙上的标语变成了“张春桥坚决要求当总理”。这样痛快淋漓一针见血的揭露和讽刺,南方滑稽的世俗小热昏,达到了针砭时政“大热昏”空前的轰动效应。 小热昏也好,大热昏亦罢,以上海方言为表述载体的南方滑稽,最便捷的这个“说”,当然成为了此地迅速应对上至时政经济,下到市井生活的表演形式。说到“热”,指的是此时当下“哒哒滚”的内容,至于“昏”,就是生活里从来难求难舍、表里相悖,一时前后矛盾、左右犹豫的外部形态展示。王汝刚也说到了现今创作滑稽剧目和段子的各种难处,生活中有大事,更有小情,如何观察和反映,这在考验我们专业人员的水准,更需要方方面面的宽松环境和支持。“有只电影叫《苦恼人的笑》,就是再艰辛的生活里也要有笑声,就像今朝晚饭,有点怠慢,小菜一般,不过饭要吃饱”。这个“小菜”,就是生活的五味,而这个“饭”,就是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