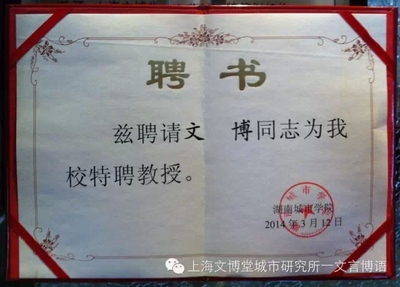他喜欢收集各种刀具,喜欢爬山,有人说他是个编剧,你会怀疑是跟你开玩笑。真的跟兰小龙坐下来聊起人生经历,会发现他跟《士兵突击》或者军人的距离更加遥远。这些外在的东西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
兰小龙的同学,另一个编剧史航说:“他在《士兵突击》里勾勒出了一个自己的状态和他想象中与朋友之间的那种状态。”文/王小峰
军队里的自由 见过兰小龙的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的形象跟《士兵突击》联系在一起。他大约有1.6米身高,而且很瘦,看上去有点病态,或者,他在一部反映吸毒者电影里饰演一个角色更合适些。采访康洪雷的时候,兰小龙突然闯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把手枪,戴着墨镜,对着康洪雷:“你都交代了没有?”这形象看上去更像一个抢劫银行的人。 4年前,第一次见到兰小龙,他在一群人中,不显山露水,瘦小的身体甚至能被周围人的声音淹没。他喜欢收集各种刀具,喜欢爬山,有人说他是个编剧,你会怀疑是跟你开玩笑。真的跟兰小龙坐下来聊起人生经历,会发现他跟《士兵突击》或者军人的距离更加遥远。这些外在的东西会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个错觉背后,用兰小龙自己的话讲:“我非常精明。” 聪明得有点过头的兰小龙,能写出《士兵突击》并没有什么稀奇,甚至,他不愿意再去谈论这部热播的电视剧,脸上丝毫看不出他有什么自豪感和成就感。 兰小龙是中央戏剧学院自费戏文班毕业,1997年,他被战友话剧团相中,老师告诉兰小龙,战友话剧团要人,问他愿不愿意去。兰小龙一听,忍不住乐了,老师也乐,因为这在他们看来像一出荒诞剧。因为平常兰小龙的书包里只揣着两样东西:杀猪刀和莎士比亚戏剧集。 兰小龙进部队却速度极快。“突然有一天老师把我叫去,跟我说有个地方想要人,那个地方是军队。我们那届当时混得很差,老师很内疚,他总想让我们尽量好一点,有点活路。我是他推荐到军队去的第4个,前两个是生存能力特别有问题的人,军队都打回来了。第3个军队看了挺满意,他自己又不愿意。我是第4个,老师把我放在第4是因为知道我有出路。毕业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可能做自己的专业了,我是自费生,连公费生都分不出去,自费生是完全不管的,我就自己联系到了广告公司,也还混得不错。而且当时跟我打交道的都是中国第一、二代的广告人。我老师补充说是话剧团要人,我立刻就严肃了,这完全是个奢望。我老师自己就是个戏疯子,他要我们每学期精读200个剧本,每门专业课每周3万字的写作量。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可能不热爱这个行业,所以我决定去试试看。当时心里还是挺抵触军队,我在学校那样自由的环境里都是最散漫的一个,自己后来想了想,也认为军队实在待不下去。我把手头现成的剧本给团长看,也没抱太大希望。后来突然一天接到话剧团的电话,说能不能来一趟柳州,我就去了,12天收拾出一个剧本,就很快进部队了,当时还没拿毕业证。” “我也挺烦军队的,因为我是一个混混,是逆反心理极强的人,完全是个叛逆者,为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愚蠢情结上了中戏。”兰小龙不喜欢中戏,他很敏感,所以在中戏的4年,心里形成了一种不安全感,“在中戏就学会了一件事,大家都活在灵感里面,所以要老老实实,千万别听别人的,我的不信任感是在中戏造就的。我对中戏没什么好感,完全生活在灵感里面对周围没有责任,这种敏感听起来是个褒义词,实际上是个贬义词,这个世界完全就是我一个人的”。 部队的环境恰恰让兰小龙从那种不安全感中走了出来,他仍然自由散漫,甚至至今没有受过军事化训练。他开会时候坐在桌子上,穿拖鞋,跟人没大没小。他去下面的坦克团,会把坦克上的机枪卸下来扛在肩上在军营里到处逛,或者把坦克驾驶员赶下去,自己开着坦克到处走。这是兰小龙对军队生活的兴趣点。一个人从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转换之快让他喘不过气来,这种生活方式对他来说却是一种放松。因为部队的等级观念比较强,兰小龙的级别在军营里也属于领导级别的,所以可以任他肆意妄为。 “我不管写什么戏,写聪明人还是傻人,都是一个命题,就是我们可以活得更自由,一个人是怎么让自己活得更自由的。”兰小龙说,“有两个戏到今天我看了还是会哭,《肖申克的救赎》和《楚门的世界》,都是讲人在挣脱困境争取自由,而且我特别喜欢加缪,生活本身就是困境,所以也没有什么困境,自己想开了就是那么回事。” 军队开始就是兰小龙的困境,回忆他刚到军队的时候,兰小龙说:“我姐夫曾经对我说:自由就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管你了,要对自己负责任。这是他说过的对我最有用的话。我刚把军装穿上时,觉得自己快疯了,我这种人到了军队里能有哪件事做得对?我一做就有人说我错,我怎么可能再给出好的回应?最后当然,大不了离开军队,但是外面又没有后路。读书时候我可以不把中戏当回事,但现在生活在军队里,所有对我的评价都由穿军装的人做出,我到今天仍然不能完全接受军队。在军队几年里,也写一些戏,也做枪手,做得很愉快,不用跟人打交道,仗着自己还能写,出来一个戏就拿一半钱,那样写一点责任感都没有。对自己没责任到把钱铺在褥子底下,铺满一层,懒得去银行存,那时每天晚上18点打车到三里屯酒吧把所有的啤酒喝一遍,喝到天亮再回家。” 单位领导看着兰小龙这样不着调,做事无组织无纪律,因为他到了部队后都没站过队列,所以决定让他去参加军训,但是兰小龙坚决不去。领导下了死命令,他仍然不听。“我是个不怕走的人,所以拿我真的没辙。”最后,经过妥协,把军训变成代职,就这样,兰小龙花了10个月时间去体验生活。 他去的部队正好有一个集团军的大演习,兰小龙便去了集团军。“那个基地大到我在那里待了两个多月没有看到一棵树。我到那里,把一个二级士官的衣服给扒下来了,穿在自己身上。团长不知道我哪来的,营长不知道我是哪来的,连里不知道我是哪来的。然后就背着登山包,做出一副非常沮丧的样子,因为我冒充被军部裁下来的打字员。因为我是深度近视,不可能不戴眼镜,只能冒充打字员,冒充不了别的。后来连长让我站队列,站了一个小时,我说,咱们能不站队列吗,聊天吧?”后来兰小龙的身份暴露了,总政艺术局的领导下去询问兰小龙的情况,部队里才知道这个人的身份,于是,又没人敢管他了。于是他换上便装,到处游逛,整个演习基地,只有他一个人穿便装,有人见他跟他打招呼:“你是哪儿的?”兰小龙回答:“部队的。”对方说:“搞文艺的吧?”这就是兰小龙的“军训”经历,实际上更像一次旅游。 兰小龙当时没有目标,很茫然。当然,这种状态早晚会出状况。后来团里的一个顶梁柱编剧离开,团里就希望兰小龙干点什么,但是看他整天吊儿郎当,便痛定思痛,决定让他提前转业。“正团、副团、政委、办公室主任4个领导表情严肃来找我,我知道这种场面,文艺团体让老人离开非常尴尬。文艺单位在野战部队的条令中又在条令之外,平常又有上下级关系又没有,所以非常难处理,要清退的这个人可能已经在你身边待了几十年了,很多话是说不出来的。我能明白他们这次是来让我转业,反而以一种挑衅的姿态,让他们有什么话就直说,说出这种过激的话又有点后悔,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为团里做什么,就跟他们说我想做些什么。他们就让我去做,终于踏踏实实写了一个话剧《红星照耀中国》,是一个诗剧,因为我非常迷恋莎士比亚和贝克特,我们领导看了都快疯了。” 兰小龙当然无法用美国人的视角去写《红星照耀中国》,他理解的埃德加·斯诺的心理是:“他接触了一些他认为他不应该去接触的一些东西,于是他变得自由了,于是他在中国待了13年,虽然他走的时候带着一身的病,但是我觉得他自由了。” 兰小龙平生最怕人夸他,在他看来,夸他就是对他的挑衅。他内心很敏感,是一个事先可以把对他的赞美过滤掉的人,平时他喜欢打打闹闹,如果有人夸他两句,他会把桌子上的一盘菜扣到人家脸上,嘴里嚷嚷着“看我怎么收拾你”。所以,在《士兵突击》里的人物塑造上,多少体现出了兰小龙的这个性格。 《红星照耀中国》让团长很高兴,立刻召开全团大会,老中青同事都来了,团长对众人说:“我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了一道曙光。”会后,兰小龙跑到团长办公室里,把团长骂了一通:“你还让不让我做人了?”1997年兰小龙进团,团里一直把他骂到2000年,突然受到表扬,兰小龙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一个代言人。“你做这种代言人,你就离走不远了。”兰小龙说。 但是《红星照耀中国》让兰小龙找到了自由,一种被认可后的自由。“我可能一生都会去这样写戏,我所有的戏可能都会去写一样东西,就是——人可以获得更自由。首先是我觉得我挣脱出来了,我在军队那种环境下,说真的,我活得很自由,我到今天为止,没有人强加给我。现在我的同事都能够理解我,虽然说还会强加给我一些东西,但是不会硬性强加给我一些东西,我说一些话,他们也会懂。现在他们终于知道兰小龙不能写小品,不应该让兰小龙写小品,这是你一步步争取来的。军队约不约束人?太约束人了。但我觉得我挣出来了,我觉得我比现在活在地方上的毫无约束的人要自由得多,比我的同行要自由得多,我思维不再受局限了。而且这种自由看你怎么去理解,是心灵能更加开阔,跟周围的环境几乎没有关系。有些人说《士兵突击》是中国的《阿甘正传》,对这个说法我极其反感。《阿甘正传》是用一个傻子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我这个戏是一个这样的人如何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生存,不全是许三多的眼光看世界的逻辑,我们不是给这个世界抹上许三多的色调,否则没有必要把这个戏里的绿叶做得比红花还要炫目,更多是说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方式。比如史今,他是走得非常自由。我去了离北京最近的几个部队,士兵退伍的时候经常会跟头儿提个要求,我们保卫北京能不能带我们看看天安门?一个9年的老兵临走提出这样的要求太自由了,自由得让人羡慕。伍六一也有他的自由方式,许三多在戏中跟这些人相比,感觉绿叶比红花还炫目,是因为这些绿叶都活明白了,知道自己该什么时候走。如果把军队说成一个社会,等级、服从,即使没有目的也要有方向的特点营造出的环境很像社会,又不像社会过于炫目,军队的环境可以简单得像个寓言,它就那么几个构成因素,全世界的军队都一样。” 励志与自尊 《士兵突击》热了两轮了,这在以往是很少见的,对于来自各方的评论,兰小龙并不在意,他说:“我不会把一件事情刻意做得和别人不一样,也不会刻意把一件事情做得和别人一样。我不会刻意地说,兰小龙是一个专门写积极向上励志东西的人。狗屁,我才不相信呢。但我是悲观的吗?我肯定不悲观。我写的戏,也可以说是励志的,但是这个励志励得有点怪。我是光明的吗?我才不是光明的,这个世界一片光明我觉得太无聊了。那这个世界是阴暗的吗?我是专门写阴暗东西的吗?杀了我也不是,我干吗要写阴暗?所以我觉得我非常自由。我不是光写男人戏,我会写女人戏,我不过是跟自己挑衅而已。我现在还剩下就是这个羁绊,这个羁绊我确实不敢扔,就是我得跟自己挑衅。我觉得跟别人比较没太大意思,人家从人家的思路来做,你从你的思路来做,没有什么可比性。你最后挑衅的东西,就是你自己而已了,而且这种挑衅是让你自己好玩一点,这种羁绊可能造就你一种有点变态的自尊心。这是有人跟我说的,兰小龙,你有一种变态的自尊心。我觉得做人最大的乐趣就是捅破窗户纸,这是最有意思的。” 兰小龙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很不正经,喜欢嘻嘻哈哈,但心里很清楚自己该干什么,这样他可以反过来去刻画许三多这个人物形象。谈到与人交往,兰小龙说:“打个比方,王宝强,应该说我们拍这个戏的时候,他还没现在这么火,他敏感吗?我一进剧组时候,有两个演员是我们团的,其他的我都不认识啊。但是我跟所有人可以立刻开始嘻嘻哈哈,因为我知道我们是同类。同类的意思是,我们有许多共同的话题;而且还有一个意思是,我有伤害你的能力,你也有伤害我的能力,但是我们不伤害。我觉得这是群居动物里一种共有的,大家都明白的一种东西。所以,我们为了在一起,互相不伤害,我们甚至要合作。唯独对宝强,这个戏拍完以后,我和他才走得比较近。我当时立刻就感觉到,我不能伤害他,因为他可能不会还击,我连玩笑都不太敢跟他开。我跟他说话特别正式,以至于我不太愿意跟他打交道,因为我不愿意跟人太正经地说话,因为他那时候确实是不知道怎么还击的,而且我知道他要还击的时候,我会无路可走。” 对于编剧这个职业,要么你相信自己有很多东西,但是却没法让别人相信;要么让别人相信自己的东西,但是自己心里却没有。兰小龙属于心里有东西也能让别人相信的那种编剧。谈到创作技巧,兰小龙认为自己编剧上根本没什么技巧:“我曾经遇到这样的导演,我给他一个本子,他认为自己一定能导好,那种信心膨胀到不好意思说出的地步。等拍出来一看果然很炫,但看上去似曾相识,不是说他抄袭,而是他从看过的很多片子中学到很多技巧,把这些技巧用在这部戏上,让我感觉风马牛不相及。这些东西不是学来的,是从自己感悟而来,自己在写的作品完全是属于自己的世界,前人的技巧对我没有什么用处。” 兰小龙说他最痛苦的经历就是一天写7集25分钟的电视短剧,他说任何人要这么干下去,一年后就完蛋了。因为这样的电视剧就是写“水词儿”。“我跟电视剧做了多少年斗争,千万不能服从这种东西。如果我喜欢这行,我会尽量让干这行的生命延续下去,我知道不可能长生不老,但会尽量活长久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喜欢。”兰小龙甚至不承认《士兵突击》是一个故事,他说他创作之前不会去策划这个故事,“我要求我的每一句话都要吸引观众,所以我是写台词,不是写故事。为什么会这样?4个字:‘本该如此’。你既然写戏,又是写这种戏,你注定要用这样一种方式,这是我理解的戏剧。也许别人理解的戏剧和我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个现在时,你把你现在这句台词写好了再说往下一句。不要现在就来跟我扯,我多少集以后有一个翻,那是扯淡的事情。我写一个东西,第一重要的肯定不是情节,甚至都不是人物,是每句词。我写剧本需要的不是一个故事,有故事我不写。我不做改编,我从来不做小说改编或者剧本改编,我通常更乐于做的事情就是一句话,比如说你有一句话的创意,这句话打动我了,够了,你不用往下说了。《士兵突击》从策划到文案全部是我自己做的,没有人提议给我做这些事,做出来不是我拿剧本去找人,是一个影视公司找我帮他们做个戏,我说做什么呢?他说你随便。我那时候还不是混得很好,很少有人跟我说你随便。所以他一跟我说你随便,我觉得是一个机会。那我就随便做了这个东西。后来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一直到今天做戏还是,你不要给我故事。” 因为兰小龙当枪手写“水词儿”受过刺激,所以对别人事先预谋好的东西有种本能的反感,甚至他都不愿意参加几个人坐在一起的剧本策划会,要做就自己做,“我不愿意和几个编剧一起去谈一个戏,让别人从几个剧本、编剧中间选一个来拍戏,我觉得这个是有伤自尊的,这就是变态的自尊心啊。我觉得那像几条狗抢一块骨头一样,我不愿意做那样的事情,我不愿意做一个被别人选择的对象”。 兰小龙不喜欢去分析自己当初是如何策划写这个电视剧的,至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故事的结构,他都不想说,或者说,他太想说反而说不出来。他强调创作是一个心态问题,“我说不清,只能说别松劲。我写戏有点像跟自己过不去一样,其实每个人写东西都跟自己过不去,只不过突破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突破的时候,他可能就想我是不是应该再加点故事啊?该再加个人物啊?我可能不会往那方面想,我可能更想得多的是我自己有问题,也许就是一层窗户纸的问题,你要拼命去捅这个窗户纸。不是说,来这个房间你觉得不舒服你换一个。也许更多的是我调整一下我自己心态,我在这个房子里住得更加舒服呢。其实,我真的觉得影视不是一个复杂的东西,流程全世界人都是一样的。我说的这个流程甚至包括很多手段、技巧在里面,真正最重要的东西是心态。康洪雷导戏,他的流程和手段与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吗?没有,就是心态。” 很多人看了《士兵突击》后觉得他把男人的感情写得很突出,也是人们看了之后觉得最感人的。“也许在许三多刚进部队时候,他就想在军队要待下来,我就想着我要走。其实这在戏里是个一直存在的东西,可能是让这个戏有一点阴天的感觉,有一种随时要下雨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戏里的人比较善良,对他们最后的影响永远有一种离愁的东西。这倒是我有意的一种设计,这个会增加那种成长的东西,成长本身完全就是一种离别式的东西。” 一直都在谈论自由的兰小龙,其实他跟很多人不一样,他自己也承认:“也许我没有用一个当兵的法则来生存吧,也许我意识不到那种沉重。”但同时他也谈到了人的另一面,那就是尊严,一个人有了尊严才会有自由,许三多可能是他对自由的另一种表达,当许三多的尊严一步步树立起来的时候,他也就更加自由了。兰小龙说:“很多人都太容易投降了,自尊心不够。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些规则,甚至你知道你这些烦恼的根源都是来源于这个,最后你还要向它屈从。所以,变态的自尊心有时候是个好事情,我就不投降,我就按我的方式活。我到现在为止没服过,军队没有改变我,一点都没有改变,反而让我比以前更加夸张了。”不过兰小龙说,“许三多没有变态的自尊心,他比我可怜得多,他仅仅只是在自保,他只是有一种最基本的保护心态,他只能装作我听不见看不见。或者你们看不见我。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我微笑,我拼命对你们笑,哪怕你们觉得我是在傻笑。很多观众很厌恶这种傻笑,包括我自己。但是我知道那是一个人在保护他自己,此外他没有任何手段保护自己的。” 兰小龙反复强调,聪明和傻之间根本没有界限。 一件事让兰小龙知道了什么叫责任。几年前,团领导突然跟兰小龙说,一个月之内弄出个舞台剧,兰小龙说看资料的时间都不够。但是由于当时军队的文艺团体要解散,成败就在这个剧上,所以他只好从《士兵》里拿出一个片段,排成了舞台剧。没想到演出后军界反响很大,然后就进了国家精品工程。国务院和总政给了200多万元,让团里复排。“我们单位当时都傻了,从来没有见过,太夸张了。我真的很想把这个团救下来,只要进了精品,这个团就救下来了。可是他们没把钱用在戏上,戏剧是贫困的,但是当时我们一下摆脱贫困了,200多万元排一个戏,这个戏可以很华丽,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华丽了,因为我们穷惯了。买一套音响,几十万元,买一套灯光,几十万元,整个舞台要重新垫高一层,把舞台做成斜台。我说,做舞台剧不要做这个,结果就差0.1分就成了精品。第一年没进去,第二年又没进去。甚至外面的人来谈合作商演,都没法挽救这个团。最后就是看着这个团散掉了,到今天我觉得散掉是好事,我们没有存在的价值。” “我已经有了更大的自由,因为我找到一种更大的责任,这个东西永远是成正比的。”兰小龙说。 别人与自己
许三多这个形象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立志的标杆,但是兰小龙不想他塑造成的许三多被误读成一个坚忍、奴性的形象。“我不愿意给自己找一套生存哲学,然后按照这个哲学活着。”但事实上许三多确实把人们拉回到原来最基本的做人法则上了,人性最本质的一面是什么。“我不相信会拉回,但是我想他在受挫的时候会想起来一点,得意的时候想不起来。可能老板希望员工想起来,但是我想不太有可能有哪个员工看了这个戏以后觉得我要为老板做点什么,这个可能性很小,而是老板看了以后觉得我应该用这个东西教化一下我的员工。但是我想,在他很顺的时候,他能想到的是拿这个东西给别人看,而不是给自己看。” 《士兵突击》让王宝强成了明星。不过最初兰小龙并不看好王宝强,是康洪雷的坚持,兰小龙不明白怎么能让一个没有受过军人训练的人担任主角。不过到后来,兰小龙彻底认可了王宝强。谈到王宝强和许三多的关系,兰小龙说:“他们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跟宝强比的话,许三多是个非常幸福的人。生活中哪有那么多人来指点你啊,虽然宝强说他第一个戏就是他的史今,其实我倒是觉得那是他的老马,可能冯小刚是他的史今,可能康洪雷是他的袁朗。我特别不喜欢这么对应起来说事,因为没人那么去指点你的。没人那么说,真的是靠一个人的悟性。这个戏一播出,很多人说哪有袁朗那么完美的人,哪有史今这样善良的人,有没有?太有了。我想宝强现在的状态,那个‘钢七连’已经解散了,我非常希望他能够走到老A,然后一直走下去,一直走得非常自由。许三多的自由绝对不可能是提干什么的,他一定会回家。当回家时候,他有一颗非常自由的心就可以了,我希望宝强也能那样。他现在的情况是,如果傻根是他的333个大回环的话,《士兵突击》不过是他拿了满墙的奖状而已。很多专业演员就是阴沟里翻船的感觉,奖状拿了一满墙,接着来的是很多的名利,你就晕吧。宝强现在还是有点晕,但是晕完以后我希望他厌恶那种东西,晕完以后,他会是自由的。他如果迷在这种晕里面,他就被这种晕给毁掉了。所以我说他现在是‘钢七连’解散之后,你没有目的了,你没有目标了,我希望他很快就能找到这个目标。也许他比我想象得更高明,他有目标。我觉得宝强就像一个来北京旅游的小孩,他不知道北京什么样,就想来北京看看。刚来时候觉得北京多好啊,太好了,我再也不回去了。然后有一天,他看烦了,北京就这样,我就回去了。我现在多多少少有点担心,他最后能不能走到这条路上去。他如果能,我羡慕死他了。” 兰小龙的同学,另一个编剧史航说:“他在《士兵突击》里勾勒出了一个自己的状态和他想象中与朋友之间的那种状态。”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