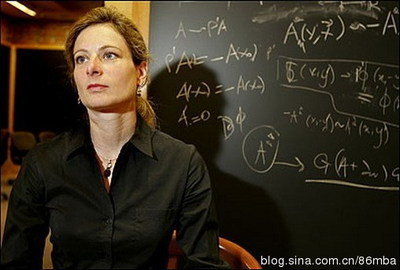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事,其实就是要将儒家带入世界。
撰稿·河西(特约记者)
在虹桥龙柏饭店见到杜维明先生已是黄昏时分。一开始我们谈起熊十力的曾孙女和上海书店出版社最近为纪念熊十力逝世四十周年而出版的《十力丛书》,这位68岁的新儒学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也不由得感叹时光匆匆。熊十力的曾孙女熊明心在复旦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杜维明见过她,这一晃就六七年了。 从熊十力到新儒学,一步之遥。我们的访谈马上切入正题。他一再强调儒家与政治的关系,并不如有些人所想象的是“国家机器的帮凶”,儒家的真正精神是孔子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孤往精神,这种精神在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等一代学者身上已经体现了它的风骨。 儒学到熊十力当然没有终结,杜维明觉得儒学可以介入到现代事务中去。“我们没有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但多元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他对记者说,“企业、媒体、政府、学术和各种不同的职业团体发展出一个平台,对国家出现的重大问题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进行讨论,进行公共论理,并使这些论理成为政策设定时重要的参照,这也是儒家可以发挥其功用的一种方式。这是民主化非常重要——也是在中国切实可行——的一条路。”他的语气和闲聊时大不一样,分明是凝重了许多,在他眼中,儒学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传统学科,它的观念从来不仅仅停留在《论语》或《孟子》等几部两千年前的小册子里,它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并希望在现代化的语境中发展自身。 当儒家遭遇政治 新民周刊: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和政权是结合得非常紧密的,特别是独尊儒术之后。对此您怎么看? 杜维明:如果我们把儒学史分得更细一些来看,儒家传统在先秦、两汉、魏晋、唐、宋、元、明、清都是有分别的。如果你笼统地说它和政权的关系,可能会淹没许多问题。孔子、孟子和七十二贤,基本上都是民间讲学,是社会力,和现实政权有些互动。他们当时的政治理念,这一套政治理念在现实中无法施行,所以他们看不起当时的君王。孟子不是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孔子和鲁国有了矛盾就走了。他们有一套政治理念,就核心来说,就是政治不是权力的分配,政治是为所有的人创造一个人格发展的环境。在政治上面,他们可以说很不得意。但这是理所当然的。他们本来就没有这个意愿。另外儒家又没有掌握很多的经济资源。 可是经过好几百年的努力后,儒学已经成了非常重要的显学,这完全通过教育。汉代开国七十年,推崇的是黄老之说。一直到汉武帝才独尊儒术,虽然是董仲舒提出来的,但真正付诸实施的其实是公孙弘。公孙弘是趋学阿势之辈,《史记》里对他的批评很厉害,因为他整个放弃了儒家基本原则,去投靠现实政权。一般学者认为这一时期既是儒家的政治化,也是政治的儒家化,瞿同祖称之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汉代晚期太学发展之后,学生有好几万人,汉代的儒家气派很大,对政治有很大的导引的作用。汉武帝本身不信儒家,信黄老之说,但儒家的学说到了西汉影响力已经不容忽视。这可以说是儒家和政治的一个互动的开始。 新民周刊:佛教传入中国后儒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儒家对于当时政治的影响是否也有所减弱? 杜维明:因为佛教的进入,因为魏晋玄学,儒家有一段时间不成为精神世界的主流,但是在政治上有它的影响力。唐代的经学非常重要,虽然唐代受佛教和道教的影响已经很大。唐玄宗亲笔写过《孝经》。宋明理学兴起后从中国影响到东亚。宋明时期皇帝的权力要比汉代增加很多,但宋代大臣和皇帝却可以“坐而论道”,可以平起平坐。你看王安石、司马光的影响力,乃至二程给皇帝讲学,皇帝听得不耐烦,他们还可以批评他。后来有些学者会认为他们有些过分的严厉了。那个时代的大儒,像张载、朱熹,抗议精神非常强,朝廷很少可以笼络他们。 元代,忽必烈是蒙古族中真正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人物。忽必烈建立朝廷之后,出现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刘英,一个是许恒。忽必烈一招,许恒就做官。人们说他过火了,太热衷于政治了。他说:“不入此道不行。”刘英招三次,他不去,人们就说他太傲慢了,他说:“不入此道不尊。”这其实反映的是一个儒家关于尊道和行道的问题。 新民周刊:明之后,文字狱盛行,虽然东林党也进行了一些知识分子式的反抗,但结果是悲剧;吕四娘进行了一些民间方式的反抗,但结果是传奇。在明清时期,儒家是否完全被政权所压制? 杜维明:明代废除宰相,以六部取而代之,所以早期大学士和后期宦官的权力很大,对知识分子的残害令人发指。但还是出了像王阳明这样的人物。王阳明之后的知识分子影响就更大了,出现了三个观念,一是公,二是私,三是官。日本儒学认为官就是公,私就是一般的老百姓。明代中期以后,对这些有非常明确的认识,如果朝廷变成一个私欲集团,我们就批评朝廷并非天下公器。明代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非常强,大儒几乎都不是官场的依附。黄宗羲就宣称自古以来所谓的儒学都是受政治利用的,所以后来发展出像东林党这样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所认同的是人民的福祉,是天命是天道,而不是政权,这也非常明显。 明朝受到也先所代表的蒙古游牧势力的侵袭。英宗皇帝御驾亲征,结果战败被捕,也就是著名的土木之变。也先要挟说把皇帝放回来也可以,但需要答应苛刻条件,整个朝廷一筹莫展惊慌失措。于谦就和朝廷内部达成协议,再立一个皇帝,即景帝朱启钰,说景帝已经即位,你送不送英宗回来,都没关系。也先最后把英宗放回。这个事件说明了什么问题?以于谦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所认同的,是皇帝的位置,不是这个人。孟子就认为,杀独夫不是杀皇帝。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君,臣要像臣。君要不像君,臣就可以不像臣,可以辞职也可以革命。在这个情况下,已经可以看出知识分子的抗议精神,如果知识分子只是依附于政权,那么会出现这样一种非常“现代性”的处理方式吗? 最大的改变是清代。因为清代的这几个君主太杰出了,特别是康熙、雍正和乾隆。满族就一百多万人,想要控制中国,他们是无所不用其极,想要利用儒家资源,作为他们控制中国的手段之一。文字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事实不只如此。我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有一个地方官向朝廷建议,他的父亲能不能入文庙。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他的父亲在社会上受到尊重,也以孝道闻名,许多人也认为朝廷应该对他做出肯定。结果乾隆得到奏议后大怒,觉得进文庙这么大的事,你一个地方官怎么可以定呢?在治罪之前定了他的罪是死刑,在治罪过程中只讨论他怎么死法:凌迟、剥皮最惨,腰斩比较方便点,最后大概是腰斩。这就可以看到清代的皇帝多么重视儒家资源,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新民周刊:儒家与政治的问题在于,如果儒家和政权结合,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的话,它就会出现问题。而如果完全依靠道德约束,面对权力和金钱的诱惑,它的抵制力是否也太薄弱了? 杜维明:完全不是简单地依靠道德约束,这是对儒家一种片面的看法。儒家这个独立自主的传统,靠的是“礼”。这是非常复杂的系统,不是靠个人的道德自觉、良性理性,不是这样。它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制度,而这一套制度绝对不是我们所谓的礼貌,也不是“吃人”的礼教,而是整个社会的规范。将中国传统的礼和法分别开来,特别是礼和行分别开来,那对于礼在社会上的作用的理解就太片面了。这个礼,用现在英美的术语来说就是习惯法,儒家大半的内容就包含在礼里面。在这个系统中,一般老百姓受到的约束比较少,主要是社会精英,他们受到的影响力太大了,根本不能违背。 其中,最不自由的就是皇帝。黑格尔曾经说过,中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不自由。这是荒谬的,甚至是无知。皇帝进入朝廷以后就是一个公众人物,皇帝从来没有隐私权,皇帝不论在何处,都有公共的眼光在盯着他,历史学家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包括他的性生活都在人们的关注之下。后宫不是妓院,不能乱来,仍然需要遵循一套规范。
也许可以对中国所有的皇帝做人格分析。很多人很小就做了皇帝,结果就出现压抑人格,很多人是平庸之辈,真正的英主不多。大半因为压抑就不愿意上朝,否则他每天四点钟就得起来。 中国有一套非常复杂的礼法体系在控制社会。到了晚清覆亡之后,许多习以为常的社会礼法规范逐渐消亡了。比如回避制度,广州地区考出的进士,绝对不会再把他派回广州。所以要形成一股地方势力非常困难。英国17、18世纪启蒙运动兴起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中国的文官制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位置,所以他们就学中国文官制度。我想这不是什么荒谬的事情。 纳入全球化的儒学 新民周刊:是否也可以这样说:晚清之后的礼崩乐坏是儒法社会逐渐消亡的重要内涵? 杜维明:说鸦片战争之后儒家的一些社会价值已经荡然无存了,我也接受。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每十年都会有很大的变化,社会的折腾更是不得了,整个儒家所标示的价值观和制度性的约束力都已完全丧失。 但虽然如此,我们对儒家中称之为“心灵的祭洗”的作用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反儒家最全面的基本上是知识分子,而且是最好的一批知识分子。反而在民间,基础的教育保证了他们和儒家的精神联系其实并没有断。 有一点值得注意,从传统中国来看,儒家的价值从一代传到另一代,最重要的角色是不识字的母亲。当代中国有影响的人物,包括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受母亲的教育多一些,有时候父子之间的关系反而非常紧张。孔子是无父之子,他三岁就丧父,孟母三迁的故事其实突出的就是母教精神。 新民周刊:学术界也有很多人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上世纪初,留日的知识分子对革命的兴趣,他们反对传统、反对儒家的热情要远远超过留英美的知识分子,您觉得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 杜维明:这也是我一直在问的一个问题。当时日本脱亚入欧的意识非常强,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你看鲁迅的形象,太像夏目漱石,完全是日本知识分子的形象。那个时候,他在日本肯定有很多深刻的感受,那是毫无疑问的。日本的知识界的传统没有断,儒学的研究在17世纪之后,每一代人的谱系都可以列出来,越现代化,日本的特色就越凸显出来。 当时日本与中国来往非常方便,一逃就逃到日本去了,孙中山的革命与日本也有很密切关系。日本的文化很厚,文脉又没有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很多都是通过日本的。可是问题在于,今天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人数并不少,在日本大学讲学的人也很多啊,而今天日本学术界对中国的影响与当时不可同日而语。什么原因我也搞不清楚。现在好像反而是欧美的一些极端的思想更能影响中国。 新民周刊:在新儒家诸家中,梁漱溟的精神确实是让人非常震撼。现在大家也谈得很多了,“文革”前后,梁漱溟、熊十力、陈寅恪、马一浮等传统知识分子,特别是新儒学的这几位代表人物所表现出的坚持信仰、不妥协的态度让人非常感动。可是像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却是自觉地将自己三四十年代的思想全部推翻了。而冯友兰的晚年的转变也让人困惑,新儒家内部的分别是否也很明显? 杜维明:梁漱溟被臭骂以后什么都不讲。到80年代,我去看过他好几次。后来我和汤一介等人一起发起中国文化书院,他是书院导师。那次他的讲话使我非常受感动。他80多岁的老人不愿意坐下,站着,声如洪钟,完全不用稿子,思路非常清晰,讲了一个多小时。 刚刚讲到新儒家的这批人,其实很复杂,每个人的情况都有些差别。其中张君劢可能研究的人最少。我看过他一次,他后来在美国去世。他所认同的就是所谓的“宪法主义”。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从德国的理想主义出发,就想中国怎么样可以走向宪政。后来人们批评他,觉得他的思想有点要走德国国家社会党的方式。他和梁启超从巴黎和会回来以后就提出人生观的问题。其实他的贡献非常大,非常值得研究。 贺麟也是非常奇特。他在解放前写的有关中国儒学能否复兴、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的文章,在现在读来仍然有非常大的感染力。但是我在1980年见到他时,他已经绝口不提儒学的事了,兴趣完全在西方的社会学。 熊十力在1968年去世的时候很惨。当时他的记忆已经很不好了,从他的《存斋随笔》中那些重复的地方可以看出来。他还在努力地奋斗,使他的那些理念还能够坚持下来。 冯友兰变化大,写出《论孔丘》,认同斗争哲学。我也到他家去看过他几次。《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他又从斗争哲学回到他的和谐观,就是《贞元六书》的理念。他从张载“必和而解”出发最终走向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际上晚年的时候他已经转回儒学。 在我看来,他们中间最突出的一个学者其实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冯契教授。他提出智慧说。我觉得他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中国古代哲学儒家修身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中间的复杂关系做了一些梳理。他的手稿在“文革”时候全部散失,从80年代起重新凭记忆来写,写了几百万字。 新民周刊:新儒学在进入港台之后,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试图沟通中西方的传统,但似乎收效甚微。 杜维明:这一代儒者,他们做了什么工作?就是试图将西方文化在当时中国有很大影响力的核心价值与儒家的基本精神结合起来。你也可以说儒家经过一个西化的过程,这是他们的努力。 当然1949年以后谈儒学的主要在香港和台湾。香港就是新亚书院,台湾就是东海大学。在那时,主要以唐君毅先生所提出的“人文精神之重建”——以儒家为代表的比较宽泛的人文精神——来对中国20世纪发生的问题提出一些框架性的回应。不论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还是钱穆和方东美,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能不能使儒家西化,另一方面则是儒家和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儒家能否成为现代化的资源,现代化又对儒家造成了怎么样的转变。而我们这一代人所做的事,其实就是要将儒家带入世界。比如用英文来研究。不用英文,那就局限在东亚世界,用英文的话就能进入西方世界。 我觉得新儒学这个概念其实是不能够成立的。为什么呢?我们不会说现在的基督教是新基督教,佛教是新佛教,为什么会有新儒学这个名词?西方在讨论宋明儒学的时候,用了一个术语是“NewConfucianism”,现在说新儒学,就变成“NewNewConfucianism”。 新民周刊:如果“新儒学”的“新”不能够成立,这将动摇我们所有对话的基石。 杜维明:假如有新儒学,就会有后新儒学,新新儒学,每一代的儒家和儒学都会有分别。而我一直希望能用“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这个概念。虽然这个概念也有争议,但我认为这是完全能够站得住的说法。第一期是儒家从山东曲阜的地方文化发展成中原文化的主流,一直到汉末;第二期从宋明儒学发展到东亚文明的基石,一直到19世纪;第三期是你刚刚讲到的晚清礼崩乐坏之后。我们要思考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前景,到底它还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进一步发展,那绝对不仅是从中国,也要从东亚和全世界来考量,因为全球化的关系,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都是全球性的,你不懂梵文也可以深入佛教的研究,你不懂希伯来文也可以深入基督教的研究,你不懂阿拉伯文也可以深入伊斯兰教的研究,是不是也可以有一批不懂汉语的学者来研究儒学?是否可能出现不懂古代汉语而成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贡献者?这些非常值得我们考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