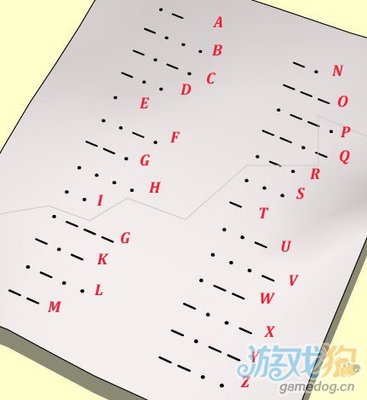并不只是在中国,世界上所有的古城都曾面临过“现代化”或“市场”带来的挑战。
撰稿·姚远
曾是活着的故城
上个世纪末,我前往北大报到,丝毫没有意识到一场全国性的城市改造运动已然兴起。尽管在我骑着自行车游历南京大街小巷的中学时代,我已看到城市空间的剧烈变迁,但我并未想到这同“城市化”、“旧城改造”等概念有着怎样的联系。 从宗白华《美学散步》到梁思成《中国建筑史》,我迷上了古建筑。大二的一年间,我试图沿着营造学社的足迹,踏访大江南北的名胜古迹。置身于正定隆兴寺的宋代建筑摩尼殿,或登临于洛阳汉魏故城金墉城的夯土残址之上时,这种与时间对话的感受真是奇妙极了。 一次次拿着这些古建筑的照片,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课间给老师看。这位在课堂上时常慨叹北京胡同被毁的政治学教授,最终被我的执著打动了。“没有了这些物质性的文化遗产,政治思想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翻着我的照片,“其实濒危的不是这些重要的古建筑,而是北京、南京等古城的胡同,记录它们才是当务之急。”学期结束前,他果真帮我找来了一笔资助,他建议我去买一个数码相机:“我们没有权力毁灭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并且剥夺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这些遗产的权利。你就用它去记录这一切吧。” 2002年8月,我在南京颜料坊开始了我的第一次拍摄。年复一年的寒暑假,我从北京回到南京,将秦淮老城即俗称的“老城南”,作为了我的“城市考古”的现场。而在北大的日子,我就去拍摄二环内的北京老城。 在南京,我“发现”了一个活着的千年古城。南唐金陵府、北宋江宁府、南宋建康府、元集庆路,它们依然活在城南的街巷里。走在那些貌似寻常的巷陌,抬头望见不寻常的地名,总令我浮想联翩。那平章巷,是否有过一位宋代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宅第;承恩寺,利玛窦是否在此与南都士大夫交游;南市楼,这昔日的洪武十六楼,又是否曾演过汤显祖的临川四梦?街头巷尾的历代碑刻、柱础、湖石,不知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历史之谜。或者说,这些历史的印痕不正是金陵史上“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明证吗? 黑簪巷6号、三条营92号、颜料坊78号、安品街88号、信府河119号、胭脂巷5号……,在一座座已经消逝了的宅院里,我亲身体验到了张岱《陶庵梦忆》里所谓“河房之外,家有露台,朱栏绮疏,竹帘纱幔”的景致。我一次次抚摸着镂花的窗棂,仰望着精美的砖雕门楼,耳畔似乎听到了钱谦益、王士禛们和着丝竹的“梦绕秦淮水上楼”的阵阵低吟。在这些优美而具体的建筑空间内,我对传统文化获得了更加立体的理解。 我还“发现”了一个活着的传统社区。老城里有最纯正的方言、最鲜活的民俗、最地道的小吃,它简直是一座巨大的民俗博物馆。你可以在同老者的交谈中,听到一个个家族或老宅的兴衰故事。这里的城与人,就是一本厚重的大书,它们用最生动的语言向你讲述不一样的“城南旧事”。 城市与政治 然而,一边是激动的“行走”与“发现”,一边是各地古城的正在成片的消失。我猛然意识到,频频发生的对历史核心区的大规模拆除,等于是巴黎拆毁城岛、威尼斯拆除圣马可广场啊! 我不能眼看美的毁灭而无所作为。推土机碾平的不只是古老的民居街巷和传统社区,它抹去的也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是人们的记忆和情感。记录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奔走呼告。作为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学生,与其在学术期刊上清谈公共领域或公民参与之类的话题,更不如从保护自己的城市的行动开始。在我起草的一份古城保护的紧急呼吁书上,一位东南大学古建筑学教授读到“难道却要毁在我们这代人的手上吗?”一句时愤怒难抑。他突然拿起笔来,在“毁”字前重重加上了“彻底”二字。他说:“这次是彻底毁掉了,以后再也没有了。”后来我知道,负责“彻底毁在我们这代人手上”的这一项目的设计师,正是这位老教授的女婿。老一辈学者表态反对拆除历史街区,却遭遇这样的尴尬:担纲改造设计的人却是他们的弟子甚至下一代。这是教育界的反讽,还是建筑界的悲哀? 目睹一座座古建筑的消失,行走在古城的废墟,想到梁思成说过的“拆掉北京的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北京的一段城墙,就像扒掉我的一层皮”,感同身受,我流泪了。 我要让自己平静下来思考这一切。我突然发现,在厌倦政治学而游历祖国山水古迹之后,却因在古城里的所见所闻,萌生了拯救生于斯长于斯的精神家园的决心,将我重新拉回到曾被自己斥为“权术之道”的政治学。目睹了老城的倒下之后,我这才在城市化、现代化的语境下,对法治、善治、公民参与等政治学概念有了发自肺腑的理解。 在一场评审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十杰”的答辩会上,一位评委老师问我:“我发现你的专业不是考古或历史学,你是如何从政治学看待城市保护问题的呢?”我回答说:“城市保护不仅是保护物质性的城市空间,也是保护活着的民风民俗和传统社会,保护生于斯长于斯的人的权利。四合院不只是私人的房产,也是属于全体公众所有的文化遗产,它的保护必然涉及公共政策。这些都是政治学的内容。” 护城薪火 有机会身临他国之后,我更坚信,纽约或东京的摩天大楼远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在京都的庙宇、庭园和市井,我看到了宋明中国《清明上河图》或《东京梦华录》般的繁华;而在费城,狭窄而密集的街巷网络与北京胡同惊人相似,只不过建筑风格与色彩相异。无论行走在奈良的“历史散策道”还是波士顿的“freedomtrail”,我们都能感受到历史给城市带来的魅力。 这种魅力来自对城市生命的尊重。城市是为人而建的,是让人能够在街巷里徜徉、散步而建造的。一座人性的城市,是人们能平静地坐在欧洲的咖啡馆或中国的茶馆里闲聊,能在东方的寺庙、西方的教堂或公园这样的公共空间里相遇,能随时得以触摸到时间的印记与具有城市特色的空间地标。正是这些人的因素,才赋予了北京什刹海、纽约曼哈顿、京都祇园迷人的神韵。 对比之中,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古城这样破败。无论是在北京、南京还是西安,当我走进老宅,访问那些往往住在最后一进院落的老主人时,老人们不同的口音,告诉我同一个事实:因为产权的混乱,造成了年久失修,人口密集,让当年精美绝伦的宅院失去了往昔的色彩。 于是,要让古城朝向住房“改善”、社区“整治”、老城“复兴”的“都市再生”的过程,治本之举应是医治计划经济时代造成的产权关系的混乱和社会功能的错位,设法复活老城以院落-产权单元为基础的街区/社区自我生长机制,让公共权力归位于社区基础设施改善和住房保障疏解人口压力的公共服务,让城市规划回归于规范和引导老宅修缮的define(规定)而非对老城空间“破旧立新”式的design(设计)。 制定这样一项保护文化兼顾民生的决策绝非那么艰难,可对城市管理者来说,这抑或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的选择。在现实中,我们通常更多看到的是以消除破败为名的旧城改造,它既隐藏着对土地财政的追逐,法治和物权上的制度缺失,它还制造了工业制成品般的“千城一面”,摧毁了老城蕴含的可逛可读的人文魅力。 其实,并不只是在中国,世界上所有的古城都曾面临过“现代化”或“市场”带来的挑战。而能否留下城市的记忆与魅力,往往是市民、学者、记者通过与公权力的合作,与房地产资本的博弈的结果,京都或威尼斯莫不如此。这些异域的经验告诉我,只有市民普遍参与的社会运动,才是文化遗产保护最为坚实的力量。而在“网络时代”的今天,中国的居民、志愿者、记者、学者也在通过与文物、规划等有关政府部门的合作,创造遗产保护的新途径,换言之,同方兴未艾的环保运动相似,中国民众保护城市遗产的城市保护运动正在形成。在他们身上,能感到一种薪火相传的精神力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