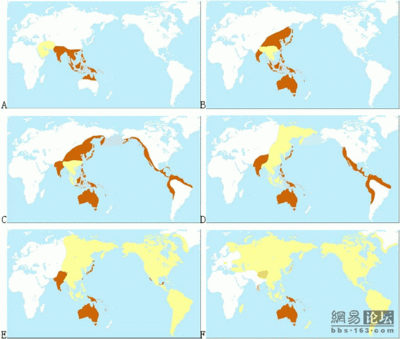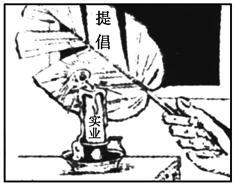绝大多数的贫穷、病苦与不公正,发生在远离我们视线的角落,而拥有能力和掌控资源的人,太忙于向上看与向前看,因此,必须有人充当转告者的角色,去战胜因为无知而导致的冷漠。
文/鲁伊
一个月前的一个早晨,我在迪拜机场,等一架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起飞的飞机。窗外大雾弥漫,候机厅里,横七竖八,或坐或卧,一地疲倦得没了表情的旅客。漫长而看不清终点的等待,最能消磨一个人的意志,必须做点什么来转移对那些超出我们控制范围的未来的不安——比如说,看看杂志。 我看的两本杂志是《经济学家》和《商业周刊》。它们的封面标题——《廉价食物的终结》以及《贪婪能否拯救非洲》——和我这次旅行的目的密切相关。2007年底,中国政府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向埃塞俄比亚捐献了价值25万美元的粮食,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因此邀请中国记者团参观当地的粮食发放和其他援助项目。 一路上,我一直试图阻止自己做这样一道数学题:一张机票等于多少非洲人一日的口粮?这是把问题太简单化了。经济学家早就告诉过我们,这个世界不是一人所得为另一人所失的零和博弈,而是一个科学和技术可以改善关注力所及的每一个个体生活水平的正和博弈。按传统解读方式,问题在于绝大多数的贫穷、病苦与不公正,发生在远离我们视线的角落,而拥有能力和掌控资源的人,太忙于向上看与向前看,因此,必须有人充当转告者的角色,去战胜因为无知而导致的冷漠。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支转告者的队伍实际上是在日益扩增的:媒体,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经济学家,商业企业,名人和明星……通过这些转告,我们看到一个破碎的非洲,一个经济凋敝、政府腐败、疾病蔓延、饥荒四起、战乱频仍的大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有些是童话故事式的。比如,多几个像安吉丽娜·朱莉和麦当娜那样乐于收养非洲儿童的大明星,就可以让非洲的战争和艾滋病孤儿不再流离失所。有些是结合了商业与时尚的,比如,买一个红色限量版的iPodnano或一件阿玛尼的红色T恤,就能帮助募得足够的款项解决非洲的艾滋病、结核和疟疾问题。有些是理想主义的,比如,抛弃高薪职位和优越生活去做一名志愿者,就会带给非洲新的血液和希望…… 当然也有更挑战旧有观念的解决方案。《经济学家》的封面故事说,因为富起来的中国人2007年平均比1985年多吃了30公斤肉,还因为美国人把1/3的玉米产量转化成了乙醇,全球正面临着1845年以来粮食供应最短缺、粮价最高的时刻。不过,这也许也是一个解决全球粮食问题的契机。通过减少西方国家的粮食补贴、转为资助发展中国家急需粮食的贫困人口、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并从价格上涨中获益,就能够让那些农业人口占就业人数2/3以上的最贫困的国家登上经济发展的阶梯——按照这一理论,埃塞俄比亚,绝对可以是粮价上涨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商业周刊》则给出了更为大胆的方案——赤裸裸的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文章中说,“大多数非洲领导人的共识是,只有私人投资才是通往(非洲)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唯一道路”。作者还引用了加纳总统库福尔(JohnAgyekumKufuor)的话,“投资者把钱放到可以盈利的地方,生意就是生意”。 过去几年中,全球对于非洲援助项目的反思可以当做帮助理解这些激进方案的注脚。不将各国的单边援助计算在内,自1963年成立之日起,世界粮食计划署共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价值400多亿美元的粮食援助,其中半数以上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然而,截至2004年统计数据,这里仍有2.035亿人常年处于因饥饿而导致的营养不良中。早在1978年,国际社会就曾经发出庄严的承诺,“到2000年实现所有人的健康”,但如今的情况却是,在非洲,艾滋病流行之外,肺结核和疟疾卷土重来并有失去控制之势,上亿穷人依然没有任何基本健康服务。在过去的50年中,非洲是所有大陆中经济和政治表现最差的,在各种国家排序上,非洲国家都位于最底层。东亚、南亚和撒哈拉以南地区是全球93%的绝对贫困人口集中之地,但从1981年以来,前两者的绝对贫困人口在下降,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绝对贫困人口却如同氢气球,一路飙升。
为什么?在注入这么多的援助之后? 如果投入更多的钱,更多的粮食,更多的人力,就可以解决问题,那么,事情或许会变得简单得多。但是,有一种情绪,比冷漠无知更为可怕,那便是怀疑:如果非洲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危机陷阱呢?《华盛顿邮报》一项调查显示,从80年代开始,非洲悲观主义在从事援助工作的国际组织和人员中的流行程度远远超出人们想象。非洲背上了“腐败的大陆”的坏名声,人们开始认为,面对一双双永远掌心向上的乞讨的手,任何努力都注定要失败。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Sachs),是因提出“休克疗法”而享誉全球的发展问题专家,是第一批向非洲悲观主义发起挑战的学者之一。在他的新作《贫穷的终结》中,萨克斯尖锐地将当前的援助形势比成苏联工人讲过的一个笑话:“我们假装工作,而你们假装付给我们工资。”他说,“很多穷国通过了改革的行动计划,但在实践中却做得很少,预期得到的收益就更少。而援助机构着力于一些标志性的项目而不是为整个国家提供援助,这些标志性项目正好可以使它们登上新闻头条”。 经历过“休克疗法”在玻利维亚的轰动性成功与在俄罗斯令人沮丧的失败,萨克斯得到的教训是,不要对一个答案轻易说“不”,也不要对一个答案轻易说“是”。非洲是如此复杂的一个大陆,没有一种解决方案,可以脱离对它独特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的解读。身为一名儿科医生的丈夫,萨克斯指出,一种像高烧这样的具体症状,可能反映了几十甚至上百种病因,医生需要一系列的诊断才能最终做出判断,开出药方,传统的援助和发展实践,也应当经历一个多维化、个体化、临床化的转变。 以我的水准,不足以判断《经济学家》、《商业周刊》和萨克斯哪一个更有道理。我只知道,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同时存在着善良与邪恶,成就与失败。爆炸的火光可以吸引方圆几十里范围的注意,而炊饭的炉火常常只在厨房的一角默默闪亮。接连发生的爆炸,未必意味着希望和未来的全部毁灭,扑灭了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的一场大火,也不代表宣告了未来的胜利。 在我读完两本杂志之前,飞机终于在延误了7个多小时后飞往亚的斯亚贝巴。雾会散,飞行员可以调换,油箱可以重新加满,破损的零件可以替代……旅程总要继续。飞机餐端上来的时候,餐盘上照例摆着红色小信封,一个仅以餐盘蔽体的黑人女孩从照片里直勾勾地盯着我,那是阿联酋航空基金会为非洲饥饿儿童募捐的广告。我知道,在未来的几天中,我会无数次遭遇同样的眼神,但我也清楚,对于这样的眼神,除了一颗慈悲的心和几张钞票,我们也许有更好的东西,可以给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