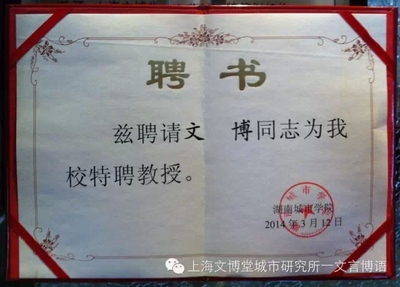从1月13日开始的冻雨,逐渐显现出惊人的破坏力。因为持续的零下低温,雨落下来不需要多久,就在遍及的一切落点上附着成冰,持续的绵丝细雨又让这“冰衣”滚雪球一般,裹得愈发厚重密实。人们没有等到太阳露面消融冰棱,反而等来了雪,那种鱼籽般颗粒状,落下来就压实凝结在一起的雪,铺天盖地落下来。
难以承受的冰雪之重,折断了绿化香樟树的枝干,压垮了某些建筑物的棚顶,也摧毁了整个郴州几十年建立起来的电网系统。穿越山岭间的铁塔、电杆和电缆,包裹着超过20毫米的冰层,以远超过人们抢修能力的频率倒塌断裂。1月25日开始,郴州一点点陷入黑暗,1月30日零点15分,最后一条输电线路故障跳闸,郴州电网的全部生命线彻底崩溃。停电、停水、银行停业……习惯了现代化生活的人们一下子失掉了方向。 城区的逐步恢复供电从2月6日,也就是大年三十的夜晚开始,而村镇还需要等待,不寻常的新年成为郴州人不寻常的集体记忆。新春里的第一个艳阳天在2月12日到来,久违的阳光让街头巷尾的人们格外欣喜。电力工人依旧在忙碌,山岭野外的电网系统还在紧张抢修中,而城市里的普通人,正在重回自己的生活节奏,重温一盏明灯、一杯热水,甚至一个晴天所能带来的最朴素的幸福感悟。
◎王鸿谅
征兆和危机 阳光很艳,南风很暖,生意人张萍一边享受着一件外套就能打发的暖冬,一边为店里积压着的厚棉袄发愁。按郴州老话里说的,“一日南风三日雪”,可从年底开始,天气一路暖上来,不见丝毫变冷的迹象,棉袄上的折扣标识已经换得让她心疼。 天不仅暖,而且干。在郴州气象部门的报告里,全市范围从10月4日以来的“少雨、晴朗”天气,已经呈现出“秋冬连旱”的征兆。旱不仅意味着火灾隐患,对郴州来说,还意味着城区电力的紧张。郴州有两张电网,一张是电业局管辖的隶属省电力公司的国电网,拥有燃煤火电和水电两种电能来源;另一张是市属郴电国际的地方电网,倚靠的只有小水电。国家电网自然还是垄断地位,占据了郴州70%的市场份额,而作为地方支柱企业的郴电国际则占据了中心城区2/3以上的市场。 两张电网的摩擦由来已久,不单纯是一个市场竞争问题,背后的财政归属才是重点。不过对于当地居民来说,重要的是竞争带来的服务改变,尤其是夏天,依靠丰沛的雨水,小水电的优势格外明显,可一旦面临枯水,劣势也同样明显。进入12月底以来,再度持续20多天的冬旱,明显让地方电网备感吃力,开始向省网求援。省网面临的还有全国范围内电煤紧缺的压力,限电早已开始,可是为了保障中心城区的用电,尽管利益各有归属,省网还是同意了城区电网与宜章分公司并网的方案,承担起分送输配电负荷给地方电网的责任。 这些复杂的局势和压力,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普通人其实并不能细致感受,尤其是这样一个暖冬,春节将至的喜庆和忙碌,才是各自身体力行的节奏。处于戒备状态的仍旧是专业部门,郴州市电业局的“防冻融冰工作会”1月初照常召开,那些历史上覆冰严重线路的观测和养护一直都是重点。 冻雨在1月13日不期而至。细细的雨落下来,一个晚上,屋顶路面就上了冻——这在南方也是常见的,只要太阳出来,一切又恢复正常。麻烦的是,雨没有停,太阳也没有出来。1月16日,冻雨的第三天,郴州电业局新闻办副主任黄安和她的同事们赶到220千伏东朝线的观音阁观冰哨,东朝线是大东江水电站到朝阳变电站的一条主网线路,也是历史上覆冰最为严重的线路之一。观音阁观冰哨观测的72号铁塔位于资兴市兴宁镇碑记乡松木村的一处山岭风口,那里的景象令她惊诧,“随手拿起一块植被上的覆冰,都超过30毫米”。那天的气温是零下2摄氏度,风速7级,工作人员拿着游标卡尺和杆秤现场测冰的结果,是“导线覆冰已达到10毫米”。这是一个危险讯号,郴州境内电网建设依照的高压导线覆冰值标准为15毫米。 必须迅速除冰。输电线路的除冰方式有两种,技术融冰和人工除冰。前者通过架设一条地线,形成短路,利用产生的热量来融冰;后者是以人工登塔敲击的方式,剥离覆冰。前者要先将线路上的用电客户转移到其他线路上,而后者需要完全断电。高压线路大规模的人工除冰,郴州电业史上未曾尝试过,而且按照规定,220千伏以上线路的断电融冰必须向省网申请。在当时省网因电煤紧缺已经开始限电的情况下,这些高压线路的断电安排需要经过更复杂的统筹安排。 电业局开始进入紧张的观测与应对准备,与此同时,湖南省的“两会”也在1月18日正式召开,郴州市各机关部门的一把手们不得不云集长沙。这对郴州电业局局长易泽茂的确是一种煎熬,尽管朋友们安慰他,郴州位于长沙与广州的中间点,地理上很靠南,不用过于担心,但下面不断反馈上来的电网情况,足够让他焦灼得“身在曹营心在汉”。 黄安再次去观音阁观冰哨是1月22日,这一次,进山的路已经全部冻住了,覆冰也在继续增加。密织的电网上,越来越多的线路呈现困境,比如作为主网骨干变电站的110千伏的大园变,从母线到主变,从导线到端子箱都冻结上了厚达20至30毫米的冰,绝缘瓷瓶垂挂着几十毫米的尖锐冰凌,瓷瓶间隙里也覆上了冰块。 郴州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人工除冰从1月23日凌晨开始,首先是大园变,接下来1月24日是东朝线72号塔。因为这是220千伏的线路,省调只批复了1天的停电时间,可人工除冰比想象中更艰难:30米高的铁塔,需要先一级级地敲击开辟出一条登塔路,然后电力职工才能腰系安全绳,一边攀爬,一边手持木棒敲击塔材上的覆冰。冰牢固得“像焊上去的”,敲击的力量,通常都会震得虎口生疼,敲击过程中还要注意平衡。作业人员每敲十来根塔材,就必须下塔休息烤火,否则手脚就会冻到僵硬得无法下塔。 72号塔的除冰当日早晨8点开始,19时结束,可还没等电业局松一口气,暴雪不期而至。仅仅两天之后,1月26日,观音阁观冰哨传来的信息是“覆冰再次超过40毫米”,“铁塔已经不行了”。那些被冰层包裹的铁塔和电杆,被照片和镜头记录下来,它们看起来“就像真实版的《后天》”。 暴雪和恐慌 城市里是一夜之间变白的。郴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今晚8点》栏目副制片人罗聪清楚记得1月25日的晚上,他在电视台的大楼忙着春节晚会的节目,加班到凌晨3点多钟,大楼里突然停电了。摸黑走到楼下,就听见很大声的“咔嚓”响动,那是马路中间的两排绿化树被冰雪压断的声音。保安建议他最好留宿在台里,外面看起来太危险,考虑再三,罗聪决定还是回到节目组为录制晚会特意租用的宾馆休息。“台里没电,太冷了”。 一出门罗聪就感受到了雪的力量,“不是飘飞的鹅毛雪,而是一粒粒的砸下来”,“一路都是树断裂的声音”,“只敢远远地沿着屋檐旁边早就结了冰的路走”。平常不到5分钟的路,这次足足走了40分钟,罗聪给几个记者打了电话,他们正在这个城市里忙碌。当晚为了抢救绿化树,郴州市的城管全部出动,但成效甚微,终于在接连几天的大雪后,城里“几乎找不到一棵完整的香樟树”。第二天上班,罗聪就把自己的网名改成了“盼望已久的大雪竟然成灾”。 南方和北方不同,下雪通常有个漫长的铺垫,先是雨,然后转成颗粒状的冰粒,在地上铺上一层,最后才是飘飞的鹅毛雪。这雪才铺上薄薄的一层,往往第二天就出了大太阳,灿灿地一晒,车辆行人踩踏下来,融得满地黑乎乎的雪水。可今年郴州的雪有些怪,像罗聪描述的那样,都是“砂子雪”,落下来就凝在一起,像冰一样,用力抓起一把来,那些颗粒状的冰粒边角能把手硌得生疼。 人们对于大雪的期盼,被这“砂子雪”砸得转瞬即逝。摔伤的人迅速增多,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下属的中心医院骨科接诊记录表明,大雪那几天,每天打石膏的人数最高值从平时的五六名,猛增到40余名。南方农贸市场的菜价雪后上涨原本是惯例,但今年没有章法的涨幅猛然间着实让人惊诧,白菜每斤5块钱,葱每斤20元。还没等人们从生活细节的震撼里回过神来,逐步的停电开始了,接下来是停水、餐馆停业、银行停业。柴油发电机的声音开始在城市的各处角落里轰鸣,在冰冷的夜里扰人梦境——其实人们也无心睡眠了,看到那星星点点不属于自己的光明和温暖,内心开始涌动着不安和焦灼。 张萍店里的棉袄在冻雨之后卖得出奇的好,但还没开心多久,因为停电只能关门。她带着儿子住回了父母家里,“有煤炉,可以烧热水取暖”。煤饼涨到了3块钱一个,还很难买,“真像烧金子”。有一天她出门还遇到了一个卖木炭的,“15元一斤,一会儿就被抢光了”。各种难辨真伪的消息也让她很迷惑,“其实并不怕停电,就是不知道停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作为最受郴州市民关注的民生新闻栏目《今晚8点》的新闻热线从1月25日开始陆续接到电话,反映自家断电停水了,想知道什么时候能来电。从疑惑到埋怨,打电话民众的情绪越来越焦躁。这些电话很清楚地表明,起初人们并不清楚电力的困境,以为只是惯常的小故障,而电力部门没有来及时维修,都希望借助电视台的“曝光”,督促问题解决。停电的范围在扩大,罗聪感觉到事态异常严重是从1月26日开始,连电视台的电都变得不稳定了。电视台由郴电国际双回路供电,还有一条可以搭接到电气铁路上的输电线,以往规模再严重的洪灾都没有过停电记录,俨然是这个城市里“最不可能失守的地方”。可怕的是,1月27日,这里也失守了,所有的搭接线路全部“黑”了。 根据后来电业局的文件,地方电网的线路1月25日开始崩溃,而电业局的主网一直支撑到1月30日,但普通人并不清楚,电网的四处断裂,迅速撕裂了这个城市的信息网络,这才是心理慌乱的开始。郴州只有两张报纸,《郴州日报》和《广播电视报》,但人们习惯性获取日常信息的方式还是通过电视,尤其是本地台的《今晚8点》。陆续停电后,郴州电视台集3个频道之力,只能保证一档新闻节目《新闻联播》的正常制作和播出,在停电遍及全市之后,这档节目甚至还用过与电台联动播出的方式,只是为了尽可能让更多人能获取正确信息。可是,能够通过电视和广播获取信息的人还是少数,从省内紧急调运收音机是后来的事情。最糟糕的是,因为冰灾和停电的关系,各通信部门的设施同样遭到严重损毁,城市里的通讯也陷入麻烦:一个电话,运气好时拨上十几次可能会接通,运气不好,几十次也是“用户忙”,或“网络线路忙”。 郴州电业局的总调度室,还在不断接到各处线路倒塔倒杆的报告。1月28日18点,郴州电网彻底与省网断开,根据接下来的“黑启动”方案,一边利用永州南和衡阳之间的小网继续运行,一边派出施工队伍试图修复从小东江电站过来的输电线路。至于最核心的大东江电站,暂时没有列入选择,“倒得太惨了”。与主网解列之后的电力“孤岛”郴州,一直坚持到了1月30日零点15分,因为220千伏的东城线故障跳闸,郴州电网的生命线全部崩溃。黄安记得那个晚上,电业局的办公楼里突然间一片漆黑。电业局大楼是郴州全城仅剩的最后一块“光明”阵地,市委市政府早就黑了,指挥部也早就搬到了电业局的办公楼。周围是人声喧嚣,她脑子里瞬间只有一个想法,“一世英名,毁于一旦”。 发电机开始在电业局轰鸣,紧急抢修线路和方案更改过好几次。1月31日和2月1日接连两天,电业局分别打通了两条输电线路,但分别都只支撑了一个多小时,就因各种线路故障功败垂成。“那才是最绝望的时候。”黄安回忆,“局里不停地定方案,组织抢修,结果不断回来倒塔倒杆的消息”,“打通一条,黑了;再打通一条,又黑了”,“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了”。 如果2月1日抢修出来的线路没有因为意外断裂,电业局在郴州市区70%的供电可以恢复,而问题是中心市区70%的供电网络属于郴电国际。结果一条并不确凿的新闻——“郴州城区70%恢复供电”的消息过早地传了出去,等到这条线路在1小时40分钟后重新中断时,消息已经无法阻止。罗聪回忆,以后几天这消息从外界再反馈回来,引发了最严重的一场情绪波动。 新闻像传言,传言像新闻,这种“信息无序”增加了人们的焦灼。“什么时候能够来电?”没人能够给出一个断然的确切回答。拥有自备电机的宾馆变得生意爆好,价位从100元/天跃升到500元/天,还是一房难求。ATM机取不出钱来,罗聪的许多同事手头都只剩了100元,像他这样家不在郴州的人,吃饭成了大问题。餐馆几乎都关了门,能够供应盒饭的宾馆奇货可居,罗聪和他的同事两个人,两个盒饭花了116元。省电力公司抢修队员张立和他的同事为了上山巡线需要购买两双雨鞋,当地农户拿出旧鞋,开出来的价码是“每双70元”。所幸2月1日,国家电网已经非常重视郴州电网异乎寻常的严重损毁,陆续派出增援抢修大军,2月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到访,更让这座城市的人们重新找到了一种信心和安定。 黑暗里的多重困境 大雪来的那个晚上,中心医院党总支副书记邓伟胜和他的同事们凌晨接到120出诊任务,去京珠高速,不到一刻钟的路走了一个多小时。到达时是凌晨4点50分左右,过了收费站,南下方向的3条车道有2条停满了车,四五公里外,则是3条车道全满,这样一路排下去足有10多公里。因道路结冰导致的京珠高速的阻滞和封闭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从1月25日开始的京广铁路因断电导致的郴州衡阳段的阻滞,让这座城市陷入交通、物资和能源的多重困境。 京广线阻滞带给春运的压力迅速膨胀,“通路”成为第一要务,对于郴州来说这就好比雪上加霜:有限的物资,一方面要保障阻滞在高速公路和铁路上的人,一方面还要顾及这个城市里的更多人。作为中心城区最大的连锁卖场,步步高超市很能感受到这种交通与物资的压力,步步高罗加井店非食品处处长庞艳的回忆已经被压得密密实实。压力从1月28日开始,“断续支撑的电彻底停了,接着又听到高速公路那边的消息,因为封路,从北往南的货运车辆无法通行,物资过不来了”。罗加井店没有自备发电机,1月28日等了一整天也不见来电,只好紧急将另一分店一台150千瓦的发电机调运过来。 接下来是打仗般的场景。庞艳回忆,超市的负责人一边要跟本市的各供货商联系,保证超市里的货源稳定,一边通过商务局、市政府“批条子”,费尽心思拿到每日发电所需的柴油。作为全城在停电期间唯一始终坚持开业的超市,步步高的日营业额跃增到了同期的五六倍,但是价格依旧,特惠商品依旧。对于这个城市而言,超市的举措也像一颗定心丸,即便住得远不可能每天来购物的居民,心里也有一个相对安慰的寄托。疯涨的物价因为陆续开业的各个超市的努力,逐渐回复到相对正常的范围。 更像打仗的是医院。邓伟胜说起来会笑,“中心医院在燕泉河边,每年涨水就有洪灾,早就锻炼出了一套应急机制”。这话并没有夸张。1月24日,郴州市发布冰雪灾害黄色警报,医院立即制定了抗击冰雪灾害应急预案。第一人民医院下属的北院是儿童医院,新生儿科里住院病人都是未满28天的婴儿,必须在恒温箱里,一旦断电,后果不堪设想。早在冻雨的时候,院长吴志坚和副院长刘劲松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他们到下面县里的医院去做例行访问,沿途都看见冰封景象,从气象部门那里,得到的都是不确定的消息。刘劲松和电业局的党委书记私交不错,费尽心思希望电业局能保证医院用电,儿童医院的电力网络还可以搭接到铁路上,也算是二手准备。电业局答应得很爽快,会尽一切可能保证医院用电,可到了1月26日大雪的晚上,刘劲松接到市卫生局长的电话,说其他医院都停电了,让他们做好接收转院危重病人的准备。到了1月29日凌晨,儿童医院的电也断了,刘劲松赶紧打电话问,得到的答复是电业局的“系统出了问题”。他起先以为只是电脑系统问题,再打电话给总调度的朋友,得到的答复当头泼了他一盆凉水,“连我的总调度都没电了”。按照既定方案,这一天的凌晨3点,新生儿科22名病人向中心医院开始转移。温箱、呼吸机等各种设备要从6楼靠人力抬下来,打着电筒,每个楼梯拐角点上蜡烛,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此后的30日、31日陆续都帮助病人转移,可到最后陆续会亮一下的灯31日彻底不亮了,但医院里还有40余名新生儿。1月31日晚上吴志坚终于从市政府要到了第一台发电机,90千瓦,1995年生产的老机子。机器连夜运过来却故障不断,配件受潮,变压器和二极管刚运转就烧掉了。折腾到2月1日16点多钟,换了新二极管,将老变压器断裂的铜线用煤火烧融连接起来后,这台煤炭局的老爷机终于运转了。那轰鸣声震得玻璃都会响,不过有电就好。为了保证新生儿病房的温度,医护人员已经各显神通,将自己家的煤炉煤球都搬了过来。
新生儿不比其他病人,必须热水冲调奶粉,为了保证热水供应,医院成立了“烧水专业队”、“送水专业队”,用大铁锅烧的水,一次只能灌7个热水瓶,但医院里有200多个热水瓶要保证。刘劲松笑道,那几天,专门负责烧水的医护人员“脸都是熏黑的”。即便这样,医生们自己几天甚至都喝不上一口热水,院党总支书记李细莲还记得多日后喝到第一口开水的情景,“那就是幸福”。 90千瓦的老爷机运转起来依旧让人揪心。集团办公室主任曹印专说,停电的日子里,最让他揪心的就是各分院的发电机,“就像心脏一样,生怕出半点纰漏”。等到郴州大面积断水断电,城内大多数医院无法自行供电,病人开始大量涌向中心医院,城内其他医院的危重病人也不断转入。“全院病床仅1400张,而在院病人持续1500人以上,特别是产科、新生儿科、ICU(重症监护)等科室,加床现象十分严重。”产科的情况最特殊,产科主任雷冬竹回忆,“白天产妇来得并不多,都是晚上突然增加的”。产科共有病床49张,平日住院产妇保持在60人左右,可冰灾之后,“最高在院产妇达145人,最多时一天出生婴儿22个”。雷冬竹记得,大年三十那天就有43名产妇出院,“一上午就只能忙着办出院手续”。 吴志坚和刘劲松守着的这台老爷机还有好多麻烦,发电每天要用1吨多的柴油,从市政府拿到指标,全城已经找不到专门的柴油桶。派人到郊区找了一大圈,才以高价买回来18个装猪油的大油桶。猪油很容易凝固,但发电机如果被阻塞就会崩溃,于是各科室的医护人员又被召集起来,“像做手术一样清洗油桶”。从只能伸入一个拳头的开口里倒入热水和碱,盖上盖,在地上不停地滚,通过充分摩擦来去除猪油。吴志坚回忆,“一共用了72袋碱,洗了4个多小时才完工”。 这台老爷机撑到2月3日发电车到来。消息2月2日晚上刘劲松就知道了,电业局告诉他,国电江苏南京分公司援助郴州的第一批5台发电车要到了,其中一台给儿童医院。他和同事们兴奋地留守了一整晚,后来才知道,当晚设备已经到了,只是从火车上卸下来花了很长时间。次日下午,发电车来了,跟车的南京公司技术人员邵伟很让刘劲松感动:“他的鞋袜全都湿了,到我们这里,把鞋袜一脱,光脚套进胶鞋就开始忙了。” 刘劲松在医院里驻守了整整8天,期间不幸遗失了家里的钥匙,电话又与家人联系不上,以至于好几天都不知道老婆孩子“在哪儿吃的饭,怎么过的”。再回忆起来这段被冰灾凝固的时间,产科主任雷冬竹感叹的是“人的潜能无限”。她科室里的人,“那几天做事不是走,是跑”,几台手术同时上场,再一台台轮换。而刘劲松感叹的,也是每日的安排太过密实,以致“都没有时间来恐慌”。 似乎过不下去的日子,也就这样撑了下来。2月6日,城区供电逐步恢复,年三十夜晚的烟花和爆竹照样在城市上空绽放,一切都不再可怕。此刻在那些市民们看不到的地方,遥远的山岭电网抢修点,来自国电网各分公司的抢修大军还在加紧赶工期。每一条线路恢复供电的死命令已经下达,他们要把笨重的塔材拖到数十、数百米的山上,然后重新建塔、布线。2月14日,记者所到的110千伏城宜线74号塔已经到了竣工阶段,计划的完工时间是当天18点。山上还是一片冰封,上午还飘过几片雪花,塔在风口上,站上10分钟已经手脚冰冷。施工人员生起火堆,在20多米的高杆上作业的年轻电工,4个多小时里只有两次下塔烤火的机会。那些帮忙拉线架绳的工人们,棉线手套一下子脏得不成样子,用手拧拧,全是黄色的泥水,他们的手上,是被泥土糊住的冻伤。他们的努力,是这个城市夜间已经到来和那些即将到来的光亮背后,最令人感动的朴实付出。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