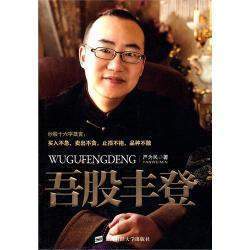书店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和判断构造出一个思想的、意义的世界。这是书店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
撰稿·何映宇(记者)
在上海,季风书园的名气也许比不上“新天地”响亮,却也是颇受瞩目的文化地标。许多人说起它时,还会提到台北的诚品、北京的万圣书园…… 走进每一家季风书园,摆在最显眼位置上的多是新近出版的政治、哲学、历史等严肃读物,非常醒目,而那些在市场上知名度很高的畅销书却没有受到多少追捧。 这正是季风书园董事长严搏非的眼光与立场,与他的个人经历有着微妙的关系——经商之前,他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做过十年的哲学研究。1997年,严搏非创办季风书园,从书刊亭到只有40平方米的小店,如今上海开出了8间季风书园,多在人流摩肩接踵的地铁沿线,其中还有静安寺地铁站的艺术类主题店。这里定期举办读书沙龙,一杯咖啡或清茶,就能让作者、读者消磨一个下午的时光,严搏非也常常参与沙龙一起交流。 “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这是季风书园、也是严搏非本人一直追求的经营理念。他的学术理想并没有因为经商而中止,也正因此,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卖书,2003年初,上海季风图书有限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组建了“上海三辉咨询有限公司”,和新星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等出版机构合作从事图书策划工作。严搏非策划了大量在国内外学术界赢得很好口碑的学术文化著作。曲高难免和寡,严搏非多少有些无奈地说:“这些书基本上不能盈利,这体现了思想的衰退。”但他从未放弃,这种对畅销书的淡漠与对学术的热情,在上海文化界乃至整个中国图书界都显得卓尔不群。 书店构造的世界 《新民周刊》:书店用“季风”命名,是不是希望书店能为城市带来清新空气?季风书园挑选的图书你是否都过目,还是有人专门负责这项工作? 严搏非:“季风”的名字出于偶然。注册企业要到工商局查名,若有重复就不能用了。当时很多名字都通不过,最后一次报上去,大概也有三四个名字,其中就有“季风”。这两个字还是我太太建议的。结果,最后通过的是它。当时选的每一个名字都想过,这个名字也一样,季风是大洋气流,随气候变化,生生不息,就像近代中国的命运。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出,开始现代化进程,对外部世界的吸收和抵抗、融化和变构从此就成为它的命运。 季风的立场不是从第一天就有的,而是逐步形成的,当然是因为先有人的立场才有了书店的立场,所以几年后,在总结的时候,我说了“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这句话,并把它写到书店的介绍上。 这个立场同时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书店是一项与其他行业很不同的生意,就像媒体的利益来自于它的公信力,书店的商业价值在很大程度上也等价于它所构造的文化价值。从这点出发,图书的选择(包括采购和陈列这两个环节)就成为书店的核心业务。在书店刚起步的很多年里,我花在选书上的精力是很多的,此外主要是大量阅读,寻找面对当下的文化和社会问题最有价值或比较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然后反复推荐。同时也慢慢有了一支小队伍,现在,主要是由我们这支采购队伍做第一轮的采购,我自己还是会不断去看,但不像早几年用那么多时间了。书店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很像媒体,它可以根据自己的立场和判断构造出一个思想的、意义的世界。把思想和意义、问题和争辩,通过图书呈现出来,就是书店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 《新民周刊》:你曾说:“我们有个好班子,这么多年没有分裂。这在民营企业中是少见的。”这个班子是怎样的? 严搏非:我们有个董事会,大部分董事你不知道,读者了解的应该是何平(小宝),我们的常务董事。80年代的时候,我们曾是同一个学术圈子的。何平的文字很有功夫,有了书店以后,他写了不少书评,当然完全是个人风格。我也写些书评,也是个人立场。 我们的天真与悲观 《新民周刊》:地铁开通后,你是否马上就想到了在地铁沿线开设分店? 严搏非:先是做了些书报亭,一年半后才开出第一家书店,就在现在我们陕西路店(总店)的外文部,40平方米,是家小书店。 《新民周刊》:季风书园已经开了十年,现在场地租金不断提高,是否面临经营困难? 严搏非:我们的总店(陕西路店)今年年底租约会到期,一般来讲,续租应该不是问题,我们原来的合约就规定了优先权。但租金多少就很难说了,希望地铁公司能够体谅我们这个行业,这个行业的利润不但微薄,而且随着经济增长反而在下滑。一座城市总要有些让人挂念的去处,尤其是文化和思想的去处,我们多少做了一些事情,虽然财政上一直不宽裕。 《新民周刊》:你曾说季风的成功在于它规避了同行所犯的错误,具体而言,这些错误是什么呢? 严搏非:我曾在北京盘桓,对王炜的风入松书店了解得多一些。当时我看出他在经营的基本结构上有些严重问题。比如他当时竟有1400多万的库存,这是一定会造成现金流全面阻塞的。然而王炜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也没有认真地去寻找有效解决的办法。他对学术的热情误导了他对书店和采购的看法。当时他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将出版社的一些重要学术书一次拿光,像上海三联的《海德格尔选集》,他告诉我“风入松”一次就进了2000本。我问他能卖掉吗?他有点自信却又不是很有把握地说:一年卖200本,10年就卖完了。这个天真的王炜!再好的销售,也经不起这样的囤积啊!但当时的风入松,像这样单品库存量上好几百的有很多。 那几年是书生们办的民营书店经受商业历练的几年,失败的例子有好几个。除了风入松当时的库存危机,广域的成立和解体也在那两年。我的这些勇敢可敬的朋友们,在一个政策、资金、规则和经验都极其短缺的阵地上,用自己的失败为后来者探明了道路。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就是在这些经验的帮助下造就的。当时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我一夜没睡,决定了好几件事情,其中第一件就是:不建或只建最小的仓库。这是王炜用他的困难告诉我们的。 《新民周刊》:就我看到的三辉图书的书目,还是以学术为主,你开书店、做出版是为了实践自己的学术理想? 严搏非:三辉图书已经出版了200多种书了,我很感谢几家合作机构,它们一直容忍我的固执,陪着我一起做这些目前还看不到盈利前景的思想学术类的图书。做这些书与我个人的学术兴趣自然是相关的,但同时也有其他的考虑,主要是与我对未来的悲观想象相关。今天人类终于进入了一个物质主义的消费世界,当所有的神圣事物都不再与我们的世俗生活相关的时候,所有的个人都将成为孤独的失去理想的个人,再无某种终极关怀将他们连接起来,这是自轴心文明以来没有过的,是世界性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时的人类将不再能应对大危机,社会一旦发生崩溃将无法重建。而我们现在正走向这样的时代。我所想的,只是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尽管很微不足道。 《新民周刊》:这些书是否能够盈利呢?或者说,如果季风书园能够盈利,你是不是就不必太在意三辉公司的盈利状况? 严搏非:这些书基本上不能赢利。这也说明了思想的消退,尤其是人们对公共领域的思想话题的兴趣在减弱。不过如果我能将库存书即使以比较低的价格销售出去,公司还是能够持平的。所以我应该特别谢谢当当网和李国庆,国庆最近帮助我消化了一部分库存,是为了支持三辉这样的学术出版。三辉是一间独立公司,在理论上它是不能占用季风的资金的。 《新民周刊》:做大的民营企业几乎都走过这样的道路:老板制——少数股东制——内部股份制——内外部参股公司——上市公司。季风和三辉现在属于哪一种? 严搏非:季风和三辉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有若干股东,有董事会。在经营上,都是总经理负责制。 我不研究畅销书 《新民周刊》:我想开公司总是想盈利,希望能扩大再生产的,你对近十年中国的畅销书是否有过研究?在中国,畅销书是否有规律可循? 严搏非:我没有研究。 《新民周刊》:陈寅恪的书一度销得不错,高端的学术书或文化类书籍达到一个不错销量,与媒体有多大关系? 严搏非:思想类的图书其实是有需求的,如果言论环境能够更自由些,更多的公共问题可以公开直接地讨论,许多思想类图书的销售是可以成倍增长的。但现在,很多学院里的知识分子都回到专业中去了,对公共问题的关注,比几年前弱了很多。当然,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包括物质主义盛行。 《新民周刊》:教材教辅一定是销量的大头,可是在季风书园只能很少看到这方面的书,是否也是刻意拒绝这样的书来破坏书店的格调? 严搏非:我们是拒绝的,主要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做所有的东西。 《新民周刊》:思考乐书局和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两家非常大的书店相继停办,在人文类小书店里,卡夫卡书店、博尔赫斯书店和左岸书店等较有品位的书店都难以为继,你觉得危机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严搏非:这几间店的停办原因都是不一样的,思考乐当年停办是因为大股东抽资金,使书店负债过高从而倒闭。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应该是租金问题,当年南京路改造后一度也传出要停办的消息,但当时汪老(汪道涵)在,汪老说了话,保了下来。现在那里的房子产权已发生变化,就很难保了。一家书店,生意再好,也无法接受南京东路的房租水平的。你知道,中国的大城市近年来地价是成倍上涨的,但图书的销售,连续六年按销售册数计算是下降的,平均书价的上升,近五年来也不过25%左右。城市中心的书店,除了“新华”还有些自有房产可以坚持外,要是全都按市场规律,都只好搬到郊外去了。即使新华书店,若从利润考虑,也应该将房子出租,那样会有更多盈利,但如果这样做,市区就将没有书店了。这是一件需要政府考虑和干预的事情。那些小书店的关门,我不了解具体原因,至少,还有很多小书店仍在坚持。 《新民周刊》:有人提出,民营书业应该更开放地接受其他行业的合作,您怎么看? 严搏非:我很同意,但很难。资本一般都嫌贫爱富,所以很难。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