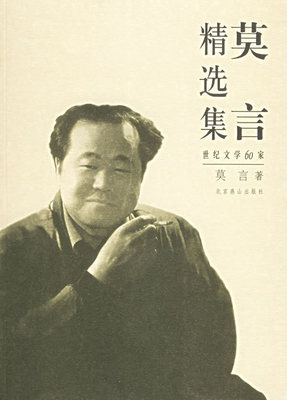从福克纳那里得到的启发,莫言也试图创造一个属于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去写一个“邮票大小的地方”,于是,在中国的文学中,就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高密东北乡。红高粱不仅变成了香气馥郁的高粱酒,也是乡村之血一直在他的心中汩汩流淌,成为他创作的永不干涸的源泉。
撰稿·何映宇(记者)
6岁进学校读书,他曾因骂老师是“奴隶主”受警告处分。从小,莫言就像是《四十一炮》中他自己笔下的炮孩子,有着一种以三寸不烂之舌舌战群儒的冲动。 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这个以“莫言”为戒的山东汉子现在把说话的欲望全都倾泻在小说之中,这是一个狂放不羁泥沙俱下的莫言,小说中充满进攻型的语言,可是在生活中他却总是谨言慎行,从来不见他像陈丹青一样放大炮,甚至《丰乳肥臀》受批判后,他也选择沉默,以搁笔两年的决绝方式表达着他的愤怒和对批评界的失望。 现在,莫言的读者中,添了一位法国建筑大师——保罗·安德鲁。“保罗·安德鲁看了我的《檀香刑》、《天堂蒜薹之歌》、《生死疲劳》,他看我的很多小说,他说在我的小说中读到的农村和他熟悉的法国农村很不一样,他说他可以理解。他的小说《记忆的群岛》我读了半天也不知道他在写什么,这样一个受法国新小说影响很重的先锋派,对我的小说感兴趣也很有意思。”谈起这位新结交的法国朋友,莫言的眉眼微微上扬,既矜持又略有些得意地笑了起来。 “人毕竟老了,现在写小说肯定写不出《红高粱》时的那种感觉喽。”在上海书展上见到前来签售和讲演的莫言,刚刚获得香港红楼梦文学奖的他低声谦虚地对记者说。这是事实也不是事实。虽然和之前的写作略有差异,在《红高粱》之后,他写出的《食草家族》、《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都和他的童年生活和乡村经验息息相关。从福克纳那里得到的启发,莫言也试图创造一个属于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去写一个“邮票大小的地方”,于是,在中国的文学中,就出现了一个神秘的高密东北乡。那里有红高粱和红蝗,炮孩子和残酷的刑罚,瞎眼的驴子和长着鱼眼睛的公狗。红高粱不仅变成了香气馥郁的高粱酒,也是乡村之血一直在他的心中汩汩流淌,成为他创作的永不干涸的源泉。对于故乡,莫言有一种感恩之情,他是赤诚的,正如他在《红高粱》卷首上写下的文字,每读一遍都让人无语凝噎为之动容:“我愿扒出我的被酱油腌透了的心,切碎,放在三个碗里,摆在高粱地里。伏惟尚飨!尚飨!” 我的父亲母亲 《新民周刊》:《丰乳肥臀》题献给您的母亲,我不知道您母亲是个怎么样的人,和小说里像吗?比如开场的难产那一段,写得非常长,同时给人非常真实非常震撼的感觉。 莫言:我母亲是个很普通的农村妇女。我外婆很早就去世了,母亲跟着姑姑长大成人,小的时候裹过小脚,16岁就出嫁。当时的封建社会里,婆媳之间媳妇总是要受点气,她生了八个孩子,死了四个,上有公婆,下有孩子,又是那么艰苦的岁月,自身也有很多的疾病,真是非常的不容易。 当然跟我小说里描写的母亲差距非常大。像一开始难产那一段,都是虚构的,并非我母亲的真实经历。小说中的母亲并不仅仅是我的母亲,它有一定的象征性,我想中国大部分的母亲都和我的母亲在性格上有相似之处:仁慈、忍耐、勤劳、善良、勇敢……当然她身上也有一些特殊性,因为在特殊的环境中成长长大,在封建压迫下也做出一些社会道德不能容忍的事。 《新民周刊》:您父亲为什么对您那么严厉?是因为您小时候调皮,像《四十一炮》中写的那个炮孩子? 莫言:我父亲对我要求严厉是因为他对孩子的期望比较高。我父亲受过私塾教育,在乡村里也算知识分子,在他身上传统的道德观念比较重,他严格以这样的道德观念来要求自己、要求子女,对劳动、农业和读书都非常重视。他在政治上一直要求进步,一直很积极。我爷爷是个老式农民,把土地看得比生命更宝贵。土地革命的时候,我爷爷觉得自己好不容易省吃俭用、积攒半辈子留下的几亩土地,现在要交给集体,心里总是有想法。土地革命到人民公社还有一段时间,当时的形势很明确,肯定要走公有化路线,那时候极少数人才会买地,结果我爷爷就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人。最后在我父亲的坚持下,我们家还是加入了人民公社。和我爷爷不同,我父亲忠心耿耿跟随共产党,他这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加入共产党。而且当时上面的干部来了之后,都在动员我父亲入党,但是村里的人不同意,我想这是他一生中很大的遗憾。村里反对的主要原因,一是我们家是中农出身,另一个我大爷爷(也就是我爷爷的哥哥)是地主——他其实是个老中医,在当地很出名,靠行医积攒了些钱,买了地。 解放后我父亲一直担任大队会计,在农村算是法定可以脱产的干部,一般可以不下地劳动,坐办公室。但是我父亲做了30年的大队会计,每天都是夜里算账,白天一样下地干活,从来也没有享受过干部的特权。他在村里口碑很好,在乡亲们中间的威信极高,对子女的要求也比较严格。我大哥能在60年代考上大学,在整个高密县都是绝无仅有的,在当时可以说是县里的奇迹,跟我父亲的教育也有关系。我父亲为了维持这个大队会计的职务,在阶级斗争的呼声一天比一天高的情况下,使我们家不被划到阶级敌人的队伍中去,也是为了子女的前途考虑,所以对孩子会比较严格。 离开乡村生活 《新民周刊》:在白卷英雄张铁生出现的年代里,您竟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写信阐述自己也想上学的强烈愿望,居然还接到了回信。 莫言:当时我也是一种年轻人的狂想。我大哥上了大学之后,我也感受到了一个大学生对乡村巨大的影响。我记得我们村是去集市的必经之路,很多赶集的人都到我们家门口指指点点,说这家人出了个大学生,他们家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要上大学,这就成了我从小的梦想。我上了五年小学,“文革”后退学,大学也不再招生,那我的愿望基本上就破灭了。后来听说了张铁生的事,等于给了我一线希望,确实还是想努力表达自己想上大学的想法,真的没想到教育部居然会回了我一封信。 我对那一天印象深刻,我回家后,我母亲正在烧火、做饭,往锅里贴玉米面的饼,我父亲神色惶恐不安,很紧张地手里拿着一封信,拆开一看,一句话也没说。信上写着:“某某某同志,你的来信已经收到,首先我们肯定你想上大学、学知识,为人民服务的想法,希望你在农村好好劳动,等待贫下中农的推荐。”怎么能推荐到我呢?每一个公社五十多个村庄,就两个名额,公社里的干部都不够分的,党委书记、副书记等等一大批领导的孩子都轮不上,怎么可能轮得到我? 《新民周刊》:没上成学,但18岁时,您去了县棉油厂干临时工,听说是走后门才进去的,临时工在当时也很吃香? 莫言:对当时的农村青年来说,最好的出路是去当工农兵大学生,其次就是当兵,到部队表现好的话也可以离开农村,你复员转业,也会安排工作。第三是招工,城市里的工厂需要工人,和大学生一样,也都轮不到一般的人,但是有些乡办工厂会招一些临时工。我们高密是非常重要的产棉区,所以办有棉花加工厂。棉花加工厂是季节性工厂,每年收购棉花的时候,会到每一个村庄招两个人,再从县里招一批待业青年,几百个年轻人集合在一起加工棉花。一般三个月左右,到春节前后棉花加工完毕,这些临时工也就解散回家。这些人正规叫法是合同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户口还在农村,生产队还在给你记工分,然后你要把每月的工资拿出一半来交给队里面,剩下的一半由自己所有。我记得我当时刚进厂的时候,每天的工资是一元三毛五,每个月上全了的话可以拿到四十元左右,交给生产队二十元钱后,自己还有二十元钱,在当时来说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一笔钱了。合同工的机会也很难得,一般都给支部书记、民兵连长的孩子给占了。我是因为叔叔在棉花加工厂里当会计,我们村招两个,一个是书记的女儿,一个是我,属于搭配着把我给弄进去了。在加工厂里一干就是三年,直到1976年我入伍才离开了那里。 《新民周刊》:部队生活怎样?什么时候开始对文学作品感兴趣的? 莫言:棉花加工厂这段经历还是让我开阔了眼界,结识了村庄之外很多的年轻人,来自县里、来自青岛的知识青年带来了很多外面的讯息,我的文化程度也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到了部队之后,新兵先要给新兵连的党支部写个决心书,实际上是显露自己文化程度的一个机会,可能我的字写得还有点样子,就让我出黑板报。后来我又在全团的新兵代表会上发言,逐渐受到一些重视。 我刚刚入伍不久就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又过了几个月就粉碎“四人帮”了。1977年的时候,掀起了学习科学文化的热潮,我们刚去也就学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同时我也读了一些文艺作品,我们部队有个餐馆,餐馆负责人的妻子是黄县(现在叫龙口)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图书馆里有很多的书,“文革”前出版的高尔基的《母亲》、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还是有一些,当时如饥似渴的我去借来看了不少。
从传统中汲取营养 《新民周刊》:《天堂蒜薹之歌》每段前面都有天堂县瞎子张扣演唱的歌谣,《檀香刑》中您使用了大量的口语和韵文,在《生死疲劳》中您索性用了章回小说的文体,什么时候开始有意识地关注中国的民间文学,重新发现中国章回小说的价值? 莫言:也不是有意识的。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多年,耳濡目染。 农村那时候电影基本上看不到,一年两次,县放映队开了拖拉机过来,巡回放映。一部电影今天王家庄明天李家庄,我们都要跟着看十几遍。再一个就是猫腔剧团会来演出,但机会很少,每当轮到电影队或剧团来了,就变成我们的盛大节日。在这个“节日”里,瞎子的演出还比较多,当时县里把瞎子都组织起来,让他们有谋生的手段。一般他们会分成若干小组,三四个人一组,一个小组里有一个人不是瞎子,他的眼睛还是有一点视力的。他们有的弹三弦,有的拉二胡,说的当然还是革命书:《林海雪原》、《红岩》之类。 “猫”这个字原来是“茂”。我之所以要这么改,还是要避嫌一下,直接叫茂腔会影响到我的虚构。实际上,茂腔没有任何特异之处,和黄梅戏、吕剧在服饰、脸谱上都差不多,都是从京剧过来的,无非就是腔调不一样。我改成“猫”腔之后,那我就非常随意了。 《檀香刑》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嫁接的文本,把小说和民间戏曲嫁接到一起,很多句子是押韵的。民间戏曲的土语、俚语用得比较多,严格说来很多语言都不规范,戏曲里的唱词为了押韵就凑字数,会生造很多词语,将成语割裂得支离破碎。 《新民周刊》:从《红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一直到《生死疲劳》,您是个特别注意形式与结构的作家,找到一种合适的结构对您来说是否意味着完成了一半小说? 莫言:我觉得现在我们写长篇小说,如果不在结构上出一些新意,我们就失去了目标。故事说来说去很雷同,而且现实主义的写法前面的许多大师的高山已经不可逾越,对我们来说,在小说的形式方面做一些创新还是有一定的余地。人还是追求新奇,对作家来说,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对他构成一种挑战,那才有意思。 比如,写《檀香刑》之前,我去听北京师范大学讲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叶朗老师的讲座,听到他讲中国古代批评家对中国短篇小说结构的一种概括,就是“凤头、猪肚、豹尾”,我灵机一动,就把它移到长篇里来了。中间的“猪肚”部分写得比较庞大,“凤头”和“豹尾”部分用每一个人物的自述,中间的部分对于前后两部分可以起到平衡的作用。现在来看,正是结构把我整个庞大的小说给压缩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