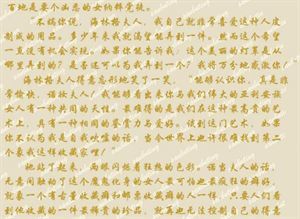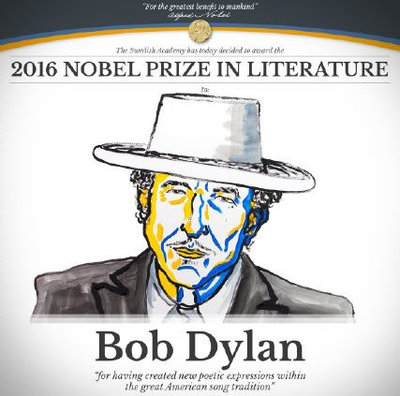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霍雷斯·恩达尔今年的一个表态应让中国幻想家们猛醒。
撰稿·边芹(发自巴黎)
自从发现各类“国际大奖”后面那只看不见的手,我对光鲜的颁奖仪式早已无动于衷。如果说凡有几分独立寄望的文人,对任何带着“官方”印戳的东西,都会抱十二分的疑心,并且假设这样的“独立”文人的确存在于世间某处的话,那么他寻遍世界想找到的“非官方”荣誉,可悲地不存在于任何地方。 只要有正式的奖状和奖金,有一个机构庄严宣布你中了奖,不管这个机构有着私营的一切表象,或是干脆不掩饰地自报官办,荣誉就必然是“官方”的。 当年让-保罗·萨特以“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不要诺贝尔文学奖,说老实话,听起来很爽,但心里多少有个小鼓:他是不是有点故作清高?那会儿可不明白这“官方”与诺贝尔奖有什么关联。 西边的世事表面一片潇洒,一切都在下面控制,一分一厘都是不放手的。后来随着对法国各文学大奖的公正性之幻灭,对国际电影奖包藏的意识形态子弹之厌倦,我渐渐明白萨特拒绝的理由,他点出的“官方”二字的深义,他的不同寻常的勇气。勇气时常是在面对荣誉时才真正显现出来的。 萨特拒奖让财大气粗的瑞典学院一气之下20年不再给法国文学奖,足见萨特此举之超凡脱俗,以及诺奖评委并不如人们象的得那么严肃。没有一处地方天上会掉几块馅饼。给你100万美元,凭什么?就凭你的文学才华?这么多钱会不烫手?所以每有“独立”影人或“独立”文人在“家里”拳打脚踢一番,一甩门到别“家”去领来“独立”和“非官方”大奖,我便忍俊不禁,想到孙悟空一飞十万八千里,在一石边留下便迹,以示逃离的快乐,却连如来的一根手指头的地盘都没飞出去。这真有点像现在这个被看不见的手控制的世界。 西方利益永远是诺奖的中心 法国《解放报》没有在头版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喜讯”,而是放在报纸第30页的文化版,头版是金融危机,可见并不想炒成国家大事。 诺贝尔奖做了一系列自砸牌子的举动,尽管都可以隔岸观火地视为恶搞第三世界,但在别处放火,不见得不会燎到自己。
所以当诺奖选了勒·克莱齐奥这样一位“政治绝对正确”的作者,我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新蒙昧主义乌云般笼罩西方上空,当世界主子的宝座摇摇欲坠的时候,挑一个用闲余感情为东方“野蛮人”唱一唱挽歌的西方作家,既为了西方自己不要重回野蛮(极右势力正以巨人的步伐走回来),也向剩下的世界放一只诱人的小白鸽。 西方总是在它略显劣势时(金融海啸),对界外的众生打出友善的白旗,由进攻转为单纯洗脑,而标榜“世界主义”、乐做原始文化守护人、批判“全球化”的勒·克莱齐奥,代表的小资思维——自由、道义而不负责任,就成为正处在板块大动荡的世界可以高扬的旗帜。 你看,没有一笔不出自精心算计,也没有一事不是意识形态先行。 2006年把奖颁给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时的进攻态势,这一次显然收敛了,那颗炸弹在土耳其民间引起的憎恶,固然炒爆了诺奖的“国际性”,但也搅起了外交风云。 明眼人谁都清楚一个西方文化圈外的土耳其人为什么突然倍受青睐,那几年在西方得了势的亚美尼亚移民,正利用攥在手中的法律、舆论与政治大权,为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的历史夙怨最终定性,遭到土国强烈反对。帕慕克在此关头选择了西方立场,一表态立马得奖。一个文学奖总是让分裂与仇恨加剧,对西方之外的世界的“施舍”总是以煽风点火的方式,大门只向“背叛者”敞开,将文学世界的马车硬驾到西方全球战略的版图上,而且即便在西方内部意识形态表态也高于文学本身,的确是发人深省的。 瑞典学院常务秘书霍雷斯·恩达尔今年的一个表态应让中国幻想家们猛醒,他说:“有一个事实是无法逃避的,那就是欧洲永远是文学世界的中心。”西方利益永远是诺贝尔奖的中心,就是这么直白。 19世纪以来就划好的国际版图,一根线都是不能挪动的,有它的核心地带(上等国),有它的外围(附庸国),有外围的外围(旧殖民地),还有永远的界外。别忘了就是非洲、拉美的“幸运儿”,也未脱出西方殖民文化圈。 因此一个文学“世界奖”本身就是荒唐的,是将纷繁世界挤压进一个思想囚笼的门票,堪称文化暴政。我总在想剩下的世界那几个“幸运儿”,尤其是那些先领到“背叛者”证书然后才被排进候选者队列的人,几十年甚至百多年后,占到的便宜会变成什么?如果千年帝国没有建立起来,百世流芳的梦想就会随之破灭,那么今天的这满把荣誉,简直就是轮盘大赌,谁输谁赢还不知道呢。 西方人剪不断欧洲中心主义的脐带 循勒·克莱齐奥的创作轨迹,发现没有一步是越了雷池的。1963年的那部成名作《审叛笔录》,正好踩在西方社会内部反叛传统、反抗资本主义的鼓点上。到了70年代,那股起自内部的反叛风,被成功“嫁接”到环保、人权的枝杈上,至此资产阶级精英专政的大树化险为夷。 这是一个绝妙的移花接木过程,只需要几桩第三世界被无限放大的“人道灾难”,对内批判的眼睛就被转移出去了,让“愤青”们去改造世界比让他们质疑体制聪明多了。也就是从这时候,勒·克莱齐奥转到了“浪迹天下”的写作。 他之为更多读者接受,也是从“外部写作”开始的,师从的就是法国旅行作家亨利·米肖,当然还有诗人兰波,但学兰波不容易,兰波恨“野蛮人”,也不处在需要装善的年代,不光心里装满恨,还要有刀一样的眼睛,先割自己。 勒·克莱齐奥显然没有这么“心狠手辣”,我在他的文笔里总是看到女人的影子。实际上“外部写作”自19世纪西方殖民征服时代就是时髦的营生,那是西方人寻遍世界只为了证明自己优越的年代。 20世纪后半叶殖民战争结束后,“外部写作”换掉了赤裸裸的征服者面目,捡回了18世纪以卢梭为代表的左翼人文主义的老唱词:野人是可爱的。但也并非不划界,只有完全屏弃现代文明的才是可爱的。 西方人很难处在一个中庸位置,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别一个极端,我称之“无事生非”,从一百年大摧大毁的文明改造,一跃而到“越原始越美好”,跨度之大,令人晕眩。 后来全世界出了一群小资,蜜蜂般涌到穷乡僻壤,为原始部落、宗教迷信唱赞歌,一脸神圣。勒·克莱齐奥一步不差地也做了环保主义信徒,并成了印第安及太平洋土著文化的捍卫者。诺奖选他的理由之一就是他是一个“直接参与行动的环保主义作家”。 我丝毫不怀疑作家偏爱原始文明的真诚,只是质疑“原始的必是美好的”这类倒行逆施的逻辑。在北美、欧洲和北非等大陆都有落脚点的他,有没有想到这份飞来飞去的自由,得自污染环境的飞机!人类每一平方公里的视野,都来自现代交通的进步。 我从他们对奋起追赶的文明之憎恨,体味到西方左翼“人道”之虚伪,对哺育世上无数生灵的宏大文明,他们唯恐改造得不彻底,生怕那样的文明真的复兴会遮盖他们的光彩。我后来听到“原始文明守护人”之类的头衔就不自在,你何不多建几个动物园去溜达!自己爬到金字塔尖,却让别人止步不前,如果不是自认上帝,有什么资格裁定哪里可以进步,哪里必须保持原始,哪里最好一草一木都别动。 勒·克莱齐奥1978年在《陌生人》中写道:“我愿为世界的美,为语言的纯洁,为站在动物与儿童一边而写作……”在他向往的世界里,云云众生是多余的,因为不够纯净。我对只接受动物与儿童世界的人宣示的“善”是打一百个问号的。 战后试图洗白西方自己的那套“人道主义”词语,将勒克莱齐奥从里到外洗得一点异味都没有。一点异味都没有的作家,或披挂一层轶事故弄出一身腥味的文人,让我最不知说什么好,他们身上其实只有两个字是让人忘不掉的:幸运。 我昨夜失眠,一口气把勒·克莱齐奥2004年出版的《非洲人》读完,开页第二段头句话便是:“我长久以来一直梦想我母亲是个黑人。”对于身材颀长、金发碧眼、有着标准雅利安人脸庞的他,一生只凭着这身皮囊,走到哪里都是主子,却浪漫地幻想做奴隶的后代,若不深究的确让人掉泪。 你当然可以解释为这是“艺术的胸襟”或“思想的良心”,而且我也没有权力怀疑他的真挚,但我知道有些痛苦是只有透过自己的皮肤才能感觉到的。比如某日你随便进了巴黎一家小店,至那一天以前你一直以为买卖方之间只有一道墙:金钱,你挑了两只土豆,忽然就有一双手伸过来夺下土豆,说:“不卖!”不卖是不卖给你,并没有别种解释。而你与他素不相识,之间只隔了这么一张皮。 所以梦想做有色人和只能做有色人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荒谬。有些仁慈剑一般直刺卑贱者的灵魂。所以我一直以为行吟诗人的慷慨必以在人生战场的彻底失败做筹码,非此权当是无病呻吟。 这里面包含着可能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在“野蛮人”身上寻善的贪婪,也不排除抓住奴隶的一无所有清洗灵魂的打算,更有把异文明永远挂在墙上的审美意图。诺奖评委们说他是“超越统治者文明的人道探索者”,我却认为西方人不管怀揣多么美好的愿望,都剪不断欧洲中心主义的脐带,那是一切精神的养料。 勒·克莱齐奥更像是在寻找失去的天堂,在他的《淘金者》第一章里有这样一句话:“此时此刻所有我感觉到的,所有我看见的,都好像是永恒不变的,我不知道这一切很快就要消失。”向“外”寻找,时常是向“过去”寻找时的一条岔路,那么“过去”对勒·克莱齐奥来说,究竟是人类一路前行一路丢失的东西,还是刻在他童年旧梦里的帝国殖民地幻影,还真不好判断。就像诺奖忽然不再选斗士,而是挑了一位温和人物,一个时不时愿意将灵魂放出西方精神牢笼的作者,究竟是傲慢与偏见的退潮,还是两场战斗间的喘息,也无从下断语。 勒·克莱齐奥1940年4月13日生于法国尼斯,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法国人。他时常也自称是印度洋岛国莫里斯人,让人错以为他沾过一点土人的血液,至少是为其并无半点探险色彩的教书的一生布下传奇。其实他父母是表兄妹,祖先从法国西海岸布列塔尼移居英国殖民地莫里斯岛,是岛上的上等白人,父亲家族后来破产去了英国,而母亲这一支来到法国。这样纷乱的背景却有着相近的血脉,有点像他海阔天空的写作却循着最正确的路线。 我很难对文学幸运儿做出公正的评价,还是留给时间吧。他的文字优雅从容,一如他的美男风度,他喜欢铺陈广阔的空间,记录人在空气中的感觉,有时精确,有时琐碎,多数时间他是在稀释,丰产之必然,而缺少刀一样刻骨铭心的东西,似没有让人过目不忘的力量。 读勒·克莱齐奥让我再次感到文字的苍白无力,它们自作多情地将世界分装到很多精致的盒子里,再像猎手一样为盒子囚笼去世间捕捉灵魂,这时才发现已经永远捕不进来,人类文明早已越过了文字的绳索。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