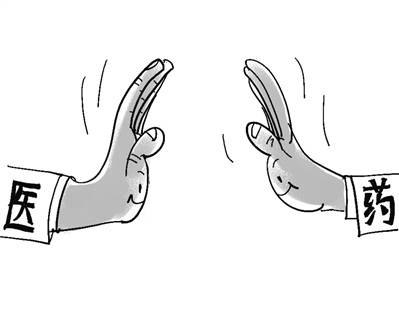在中国有两个故宫,一个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个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整整60年以来,由于两岸之间的隔阂,几乎没有多少大陆人知道台北“故宫”的情况,包括北京故宫的专家对台北“故宫”也都缺乏真正了解,甚至“两宫”之间的民间交流也很少。
很多年前,胡骁还在《光明日报》做记者,他喜欢研究历史,1988年左右,他逐渐对台北“故宫”产生了兴趣,于是他决定写一篇报告文学,介绍台北“故宫”。但是他着手这项工作,却发现几乎找不到任何关于台北“故宫”的资料。他认为,这批文物自从1948年运到台湾后,大陆老百姓就再没见过,反倒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很不正常。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中国文物概念,它代表着中国顶级的文化、艺术和哲学。做记者出身的胡骁,对这种揭秘性的东西有一种天然的敏感,所以他一定要把台北“故宫”的情况公之于众。于是,作为总撰稿,由于他和所在的九洲文化传播中心的努力,12集大型纪录片《台北故宫》即将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人们可以通过这部纪录片了解到台北“故宫”全貌。为此,记者专访了胡骁先生。
◎ 王晓峰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会对台北“故宫”产生兴趣? 胡骁:这是一个宝库,号称65万件文物,而且都是代表中华文明顶级东西,在世界博物馆界占有第四或第五大的地位,又是从大陆搬过去的。可是大陆13亿人对它的历史一无所知,对它里面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人品以及他们的学养更加一无所知。到今年正好60年,一个甲子,没有人见过。我看了很多资料,我觉得这个东西必须得用影像的方式表现出来。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当时想写报告文学,后来又觉得要用影像来表现呢? 胡骁:因为你越看越觉得文字很难去描述,比如说一幅画你怎么去描述呢?而且你描述了半天,读者也不知道这幅画到底是啥样,所以就必须要用影像。比如汝窑的瓷器,形容它就是“云破天青”的一种感觉。“云破天青”是什么感觉,谁能揣摸得到?影像是比较好的方式,2003年我调到九洲文化传播公司,它是专业从事对台宣传的一个部门,有很深的跟台湾的人脉关系,可以让我获取这些资料。但是这个过程也比较复杂,很难。不过在2005年底到2006年初这段时间,我们获得了台北“故宫”很多文物的影像资料。 三联生活周刊:这两年你在做哪些准备工作? 胡骁:做了很多基础的研究。比如它的历史,它迁台的历史从来也没有人考证过,到底运去多少箱文物,具体是什么,只知道是顶级的东西,其他什么都不知道。还有那些学者,比如那志良、庄尚严,他们是怎么去的,他们的命运是什么样的。比如跟知情人联系,寻找这些人的下落、归宿,还有他们的子女、部下。后来居然还找到了三位健在的、当年押运文物去的人,最大的一位都90岁了,最小的也已经85岁了。跟这些人建立了一些联系,还有跟台北“故宫”的一些老专家、退休的“院长”、“副院长”,我们都做了很密切的沟通。因为那时候两岸关系不允许我们去做一些更具体的事情,当时是陈水扁当政,台北“故宫”在台湾是直属所谓“总统府”管辖的,它的级别非常高,“院长”的级别相当于咱们这边的副总理。在我们看来它是一个博物馆,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很高阶层的政府部门,不便于联系。 三联生活周刊:既然沟通不便,为什么后来很快决定拍摄《台北故宫》这部纪录片? 胡骁:2006年,台湾有一股很特殊的势力,我们叫“文化台独”。这些人从文化上要割裂台湾,他们制造出一个所谓本土文化,割裂和大陆的关系。有很多论文都是些很专业的人士搞的,甚至台北“故宫”当时的“院长”也都是民进党人,他们对台北“故宫”也是想方设法去割裂。没法割裂,他就淡化。比如说台北“故宫”每次展览,不管在哪里展览,都有很大一个展板,展板上用电灯绘制出文物迁徙到台湾的地形图。1933年从北平出发,怎么样到了南京、上海,然后从南京、上海怎么样到了四川、贵州、陕西,后来又迁回南京,又从南京运到台湾,又建了这个台北“故宫”。秦孝仪任职时,都要有这么一个很大的展板,就是告诉老百姓这些是来自于祖国的。后来这个展板就没有了,每件文物底下都有简介,他们就改动简介。比如说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的老家是哪儿,什么朝代、什么地点创作的,这些都说得很清楚,一看就是中国的。他们把这些都删了,比如就写王羲之,也不说东晋。他们老搞这些小动作。这个事情就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了,当时有很多论文都出来了,有人说这是外国的文物,还有人说这是亚洲艺术品,极力篡改历史。九洲公司的一个职责就是进行两岸文化沟通文化交流,于是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做出这个片子来,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 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大陆的老百姓从来没见过,我们要把这些东西给大陆的老百姓看;第二就是要告诉台湾的青年人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它的迁台过程,还有它代表中华文化一个什么样的理念。这时候正好周兵他们拍纪录片《故宫》,他们有一个动意就是要接着拍台北“故宫”,可是被台北那边拒绝。所以我们这边筹备差不多了,就想到还是跟央视这个团队合作,我们一拍即合。由九洲这边来投资,他们的团队有很丰富的经验,对历史也很熟悉,虽然他们对台北“故宫”还比较陌生,但是这个是很容易接上。 三联生活周刊:大陆的史学家、文物专家对台北“故宫”也没有研究? 胡骁:没有。我去拜访了很多人,他们对这段历史,只知道有这么件事,但是没有专门的人去研究,包括我走访过一些搞近代史和国民党党史的专家,还有北京故宫的一些专家,他们都只知道有这么个事,但是史料在哪儿也不知道。也不是说他们不去研究,是没有史料支持,而且两岸是一种隔绝的状态,没法获得这些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当时怎么收集资料? 胡骁:我没到九洲之前,资料就是一些回忆录,散落在很多片段、书籍、杂志上的一些回忆文章,很简短,但是它足以说明问题。有多少我就搜集多少,慢慢就积累起来了。等我到了九洲之后,因为有一些途径可以跟台湾方面进行联系了,就得到台湾那边很多文化人士很大力的支持,给我提供了很多资料。他们给我寄了很多书和光盘,还有那边很多人的一些回忆录,包括手写的文稿。我就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梳理。真正有实质性的进展,还是2006年我们开拍以后,开始跟以前联系的那些人进行比较实质性的沟通,说我们希望做一个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他们很热心。这些人实际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非常强,一听说我们要做这个事情,都非常积极,无偿提供了我们好多东西。还有就是介绍了很多当事人的子女,包括他们日记、手稿。我们拍摄的过程也是一个历史研究和资料整理的过程,这些东西最后我们汇总之后,与台北“故宫”的一些专家来谈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吃惊,他们说你们说的这些事我们都不知道,你们获得的这些史料我们都没有进行过整理,都对我们很佩服。有一种很真诚的东西去打动他们,让他们就觉得我们真真正正是在干实事,这样我们双方之间的隔阂就越来越少了,认同感越来越强。他们也不想让这段历史就这样淹没掉。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和这些人和物接触是有什么感触? 胡骁:我第一次去台湾是2003年,我把别的工作都安排好就直奔台北“故宫”。到了“故宫”之后就站在那里,台北“故宫”的建筑不是很宏伟,跟北京故宫没法比,它坐落在台北郊外的一个叫外双溪的风景区,那种设计很讲究风水。我第一次看到它心情特别复杂,我觉得这些长期以来都是在书本上资料上看到的东西,觉得那是不可能被我靠近的,这次终于走到它跟前了,而且离得这么近,那种感觉是说不出来的。然后我就买张票进去看,所有我在书本上读到的那些文物都在那儿,什么毛公鼎、散氏盘、鸡缸杯、溪山行旅图,还有汝窑瓷器、珐琅彩瓷器……我特别激动,好像以前受了很多累,吃了很多苦,终于见到它们了。 那些专家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是,台北“故宫”里搞清史研究的专家叫庄吉发,他退休了,有一次我们想采访他,他就说不方便。因为当时是民进党当政时期,他又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那些人只要一跟大陆接触就会被扣帽子,说你“卖台亲中”。他说非常愿意跟你聊天,但不接受采访。我说行,那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见面的。过了两天我就去台北“故宫”的图书馆看书,它的图书馆复印材料要买一张磁卡,然后自己印。我不会印,怎么也印不出来。后边有一个老头,抱着一摞书在等,等半天他说我帮你弄吧,印好了他说,我听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我说是从北京来的。他说,前两天北京来的一个小伙子打电话要来采访我,我觉得不方便。我说您是不是姓庄啊?他说是。我说我就是给您打电话那个人。我们就这样在台北“故宫”图书馆里聊了好久,他特别希望能促成两岸共修清史这件事。他也跟咱们这边联系过,清朝的档案很大一批在台北“故宫”,也就是说台湾的清史专家看不到大陆那部分,大陆的清史专家看不到台湾那部分。修清史你看不到原始档案怎么修?他觉得两岸应该联合起来共修清史,因为清史这个项目在台湾已经被陈水扁当局给停掉了,弄台湾史。台湾的清史专家是中国的清史专家中最优秀的一批,他们这些人的这种传统观念依然特别强,甚至他身上这些中国文化的东西比我们要重得多,非常深刻,都渗透到骨子里去了。他希望有朝一日两岸专家能够共修清史,因为清朝都灭亡那么多年了,清史还没有修出来是件很不应该的事。 还有他们有个“副院长”叫张临生,他以前是秦孝仪的秘书,现在是台湾震旦艺术馆的馆长,他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历史照片,还有对秦孝仪、蒋傅聪这些人的感受,讲得非常透彻。他们对于中华文化的研究非常深刻,长期以来都关注这边,比如说这边出土了一个什么东西,他们很快就获得了,然后他们就归纳,和他们那边的进行对比。两岸的局势松动后他们也经常能来这边,参观咱们的博物馆看咱们的史料,他们人在台湾其实心在大陆,割舍不掉这些东西。比如说:台北“故宫”现在的文物编号依然是用的1924年清史善后委员会的文物编号,那时候是用《千字文》来标明编号的,《千字文》有999个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故宫有999间房,每间房用《千字文》中的一个字来代替。这个宫殿所有的文物都编在这下面。秦孝仪有一个想法,就是1933年南迁的箱子到了台北,他说这些箱子我都不动,有朝一日,我把这些文物全都装回箱子里运回北京去。他们还是抱着这个理念。还有我这次采访的索予明,90岁了,他是第三船押运文物去台湾的,是搞漆器研究的一个专家。我问他将来对台北“故宫”有什么打算?他说台北“故宫”是由两个单位合并起来的,一个是“故宫”,另一个就是叫“中央博物院”(现在的“南京博物院”)。他就说将来最大的愿望就是“故宫”的文物还都回到北京,我们“中博”的文物还回到南京,我也还回到那里去。实际上“中博”已经消失60年了。而且现在台北“故宫”的文物和“中博”的文物在编号上还是分开的,这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纪录片当初怎么构架的? 胡骁:除了向大陆人介绍台北“故宫”的历史,还有就是那些当年跟随文物去台湾那一部分专家,他们的人文精神,应该被现在大陆的老百姓所认识。他们当年跟着文物去,并没有政治上的选择,战争一来,这些学者不考虑政治问题,政府让他们迁到哪里他们就迁到哪里。这些文物在战火之中是很危险的,他们的考虑很简单,打起仗来子弹不长眼,万一文物被毁了怎么办?打完仗,我再运回来不就完了么,就是这么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所有去的人,都觉得几个月之后就回来了。所有的随船走的人,甚至有的连家属都没有带,就把门一锁,装上船就走了。那志良才逗呢,他说我们在那里都别买木头家具,就买点竹子的,但真没想到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感动的事。另外,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特别根深蒂固。庄尚严当时走的时候是一家六口全去了,后来升任了台北“故宫”的“副院长”,他是一个特别著名的书法家。文物到了台湾之后在雾峰乡一个叫北沟村的地方待了15年,这15年是条件非常艰苦的,就挖了个山洞,把文物全搁在里面,然后盖了几间平房作为展览室。他们在那儿就体现出中国传统文人乐天知命的精神。首先学术研究从来没有间断过,就在那种环境中,他们依然搞出版、搞研究、做展览,还有人带学生,教育大学生、跟国外的收藏界进行交流。还有他们每年搞一个活动,就是王羲之在《兰亭序》里说的那个曲水流觞,这些人在一条小河边,河里漂着酒杯,漂到谁那停了谁就喝,喝完酒之后要吟诗,是对王羲之他们当年生活的怀念。曲水流觞在中国文人中是一种很盛行的游戏,在咱们这边没有了,在台湾依然还有,很多名人都参加了他们这个活动。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他们的学术,他们的文化并没有脱离他们的生活。不管那条件多艰苦,他们都乐呵呵的,一点都不抱怨,也没有钱。那些专家还要养鸡。庄尚严的太太也是“故宫”的专家,家里穷,养鸡卖鸡蛋来维持生活,但是从来没有抱怨过怎么到这儿来。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思乡。很多专家的一生没有安安静静在图书馆或书房里从事研究,精力都耗在搬运文物的过程中了,一刻都没有停过。庄尚严、那志良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们大学一毕业20多岁就进故宫了,到1933年没几年就开始搬,也就是从1933年到1965年,30多年,但是学术研究从来没有中断过,对于学生的教育,对于后代的教育从来没有停过,对于他们自己所坚持的文化理念从来没有怀疑过。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咱们这边,我们会把它拔得很高很高,但他们就觉得,生活不就是应该这样的么,我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奢望,我就是搞我这个书画研究的,只要有块地方,能让我把这个画摊开来看就行了,有钱没钱没关系。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看来今天从事文化研究的人,和那个年代的人最本质的差别是什么? 胡骁:我觉得,那个年代的人抱着一种传统:“藏诸名山,传诸其人。”他们的文化研究和他们的人格之间是统一的。现在要进行一个文化方面的推广,用现代化的手段进行推广,比如说从事文化研究或者从事学术研究他也需要资金的实力进行支撑,这也是时代发展的一个需求,因为这样,所以不如当时的人心态那么沉静。他们会把这些东西做得特别到位。你看他们的书稿,他们不像咱们这边一下就写出一本书来,他们可能十几年二十几年就写了几页纸,然后等他们把这些全部都弄好了之后,出一部书,也印不了多少,这是他们毕生积淀下来的东西。比如那志良的《玉器通释》,现在成为玉器研究的典范作品。索予明的《中国漆器考》,所有东西都有了,你没必要再去查别的资料,他毕生心血都在里面了。我觉得这点,值得现在的学者或者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人借鉴。他们的心态很静,与世无争。尽管条件比较艰苦,但是他们都是被养起来的,淡泊名利是一方面,他们的日子过得还都可以,不能跟那种很富有的人相比,可是有一点好就是他们不去追求那些物质上的东西。而且像他们从事的这些事情,并没有拿到外面对人过多地宣传。他们很多人也是毕生第一次对我们讲起这些事情,真正的没有障碍的跟一个媒体去袒露这些事,大概这是他们毕生唯一的一次。我想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因为他们都已经是这个年龄的人了。他们那时候受到的表彰、获得奖章一枚一枚的,从来也没有拿出来给别人看,让人觉得挺感动的。 三联生活周刊:《台北故宫》在拍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胡骁:有两点。一是我们想进台北“故宫”拍摄,但是被拒绝。后来我们已经有它的资料了,没必要进去拍了。因为上世纪90年代,秦孝仪很重视用影像表现文物,他想推广,但是财力又不够,因为拍这些东西要花很多钱。后来台湾有一家公司来承担这些事情,他们用胶片拍了很多高清影像资料,我们通过和这家公司的联络取得了这些资料。另外,去拍摄一件文物是非常麻烦的事。他们有的文物几十年也不拿出来展一次,一些名画,大概三四十年露一面,就存在那个山后面。那个山实际上是挖空的,里面全都存着文物,恒温恒湿,能够防止重磅炸弹轰击多少次都不会坏。台北“故宫”展厅非常小,只有3层楼,没多大面积,展出一次非常不容易。你要把它那些东西拿出来拍,那大概我想我们这片子10年也拍不完。我们只是拍了展场的一些环境和建筑风格。甚至如果得不到这些资料我们可能就会放弃,好在突然之间就有了这些资料。还有一个困难就是,很多人多年以来都散在各处了,资料也都很零散。比如说我们想找很多人的子女,找到很多,但是还有很多人出国了,或者都已经故去了,也留下很多遗憾。主要的人都找到了,还有一些人失去联络了,有时候知道住哪条街哪门哪号,去了以后门也锁着,也找不到人。这种情况也都有,我觉得非常可惜。 三联生活周刊:哪些人非常重要,但是没有找到的? 胡骁:特别重要的我们还都找到了,有一个人没找到,就是梁廷炜先生,这个人很特殊。梁廷炜一家三代都在故宫工作,他本人去了台湾,他的儿子叫梁旷忠,现在北京故宫工作。他的孙子叫梁金生,也在北京故宫工作。实际上祖孙三代都在故宫工作。梁廷炜也是我们重点研究的一个人物,可惜我们就采访了梁旷忠、梁金生。梁金生现在工作的地方离当年存放《四库全书》的地方很近,他爷爷当年在北京故宫就是负责保管《四库全书》的,现在文渊阁是书去楼空。梁金生每天上班要从文渊阁路过,他很怀念那栋楼。他爷爷在台北保存着《四库全书》,孙子在北京看着这个空楼。我们唯一觉得遗憾的就是,我们想拍摄梁廷炜先生在台北的墓地,他葬在什么地方,始终没找到。他好像还有个后代在台北,但是始终联系不上。 三联生活周刊:这是一个有点令人伤感的戏剧性的事实。 胡骁:还有很多很多戏剧性的故事,比如说李济和他的儿子李光漠。李光漠现在是近80岁的老人了。李济是中国考古学界的开创者,他是安阳殷墟考古发现的第一人,当年是带着李光漠一起到台湾的,可是李光漠不愿在台湾待着,又回来了,他觉得不可能两岸隔绝。当时李光漠是在同济大学念书,他觉得去了台湾学业就中断了,还得回来念书。李济不让他回去,说大陆那么乱,你回去干嘛。他就死活要回来。这件事李济也很伤感,李光漠回来后两岸就隔绝了,父子就这么分开了。直到李济去世,李光漠也没有去台北。后来李光漠到台湾看到他爸爸当年住的地方,在台北的温州街,把李济留下来的遗物全都拿回来了。我问李光漠,后悔不后悔?现在他这话没法说起了,也不知道历史怎么就演变到这个程度,当时谁会想到父子再也见不到呢。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在我们采访中遇到很多,我一直被这种情绪纠缠。我采访李济的学生,“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老头都70多岁了,李济当年在台北把甲骨文都摊开在地上给他们讲,给他们讲当年安阳考古是怎么回事,考古队怎样的,旁边还有两棵杨树,多年以后李济过世了,他的学生回到安阳考古现场,看到李济当年考古的那个坑,还找到了那两棵杨树,那些事情都是他们在故事中、教学中听到的,他回到这个地方亲自看到这些。老头接受我采访的时候,眼泪一直忍不住流。 三联生活周刊:感觉在拍摄过程中两岸之间的联络很困难,这些问题是怎么克服的? 胡骁:联络是非常烦人的事。因为我们机构的性质就是跟他们那边进行联系,所以有一些天然的条件,但是一涉及这么长时间以来被淹没的历史,重新发掘出来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即便是在北京,我们去找的话也会费一番周折,台湾隔着那么远,又不能随便去。但这过程中也得到了许许多多人的帮助。有时候如有神助一样。比如我们想找到李济先生的学生,怎么也找不到,这事让我挺苦恼。我在最后一次去台湾之前头一天晚上,总导演周兵说有几个台湾来的朋友聚会让我去。我当时说特累,而且第二天就走了,该休息了,他还是让我去。那天都晚上21点多了,我跑到后海去跟他们见面,其中就有台湾很著名的文化人叫林谷方,我就跟他说想找李济先生的两个学生,一个叫李易元,一个叫许留云,没法联系。他说,你早跟我说,我跟他们都是老朋友了!后来很快就联系上了。还有我们想采访一个书画专家蒋勋,也是台湾很著名的书画理论家,我在那边采访别人的时候他正好在旁边,就好像都赶到一起来了,第二天就采访了。还有我们要拍蒋傅聪先生的墓,怎么找都找不着,有人说在这,有人说在那,我们都去了,都没有。后来就有人告诉我说好像是在一个叫三峡的地方。三峡具体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包括“故宫”的人都不知道,“蒋院长”葬在哪儿了,他们都想不起来了。我们开着车就去了,非常顺利的就找到了。蒋傅聪先生是个天主教徒,就找天主教的公墓,找到一个天主教的公墓,那也没有管理人员,墙上有个电话,打电话,一问就找到了。 三联生活周刊:《台北故宫》跟《故宫》在表现手法上有什么不一样? 胡骁:周兵他们创作团队的一些创作理念,确实是很符合我们这个片子的主旨。周兵拍《故宫》3年,之前他也和我一样,也进行了很艰苦的准备,他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我当时提出的一些创作理念他们进行了发挥,还有的地方进行了修改,能够被青年观众所接受。比如说,他拍的北京《故宫》比较居高临下、皇家气派的那种风格,这种风格用在《台北故宫》上也行,可是《台北故宫》有个更加人性化的东西,它很贴近于民众。如果去台北“故宫”看的话,你会觉得那些东西离你特别近,就隔着一层玻璃,有很亲切的导览和解说的方式,它把那些中国文化的元素想方设法融入人的生活中。比如制作很多纪念品,把台北“故宫”的名画印在桌布、窗帘或者衣服上,进行民众教育。周兵可能从这些地方得到了启发,《台北故宫》没有居高临下那种风格,更加贴近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跟现在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现在和历史不是分割开来的。比如说新闻性,就是当下发生的事情。最近台北“故宫”搞的晋唐书法和珐琅彩瓷的展览,我们这个片子是12月底播出,这个展览是10月份开始的,那么我们会把新闻性的东西加到这里面来,让人感到台北“故宫”和大陆的观众也没有什么距离,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会在片子中讲述台北“故宫”对台湾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他们从小对“故宫”的感受都很深,从里面获得了很多熏陶,这些东西还在台湾老百姓中活生生地存在着,就不像咱们这边,日常生活跟故宫有什么关系?台北“故宫”进行的这种民众教育,是我们这边所欠缺的,比如学龄前儿童、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要接受这种教育。还有很感人的是他们会把这些东西拿到监狱里去展览,会给犯人来看,教育那些犯罪的人,给他从灵魂上进行一些净化,还有对于残疾人的教育。对于非专业的人,你让他们去谈故宫,他们都能说出很多东西,我们不板起面孔来讲历史、讲道理,就是很亲切地说。在那么一个地方,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是按着那个时代的理念来生活的,并且到现在依然延续着,很深厚的积淀,在他们生活当中,如果我们看到,会觉得很吃惊,但是他们不吃惊,他们觉得不就是应该这样么,还能应该是怎么样呢。2004年我去台北,台北“故宫”正在搞一个展览,规模空前。我在那儿观察,好多青年人,还有义务来给大家做解说的大学生,他们讲得非常好,解说的水平我觉得相当于咱们这边的教授、副教授。还有一个父亲让他孩子骑到他肩膀上,跟孩子讲黄庭坚的《花气熏人帖》怎么写的。还有我看到一个打扮特别入时的女孩,她看一幅画的时候那个专注的神态,反正我在北京是没有看到。那幅画特别长,她看这幅画从头走,走得特别慢,走两步站在那儿看,再走两步再站那儿看,一直把那幅画看完。要我都看不下来。后来我问她,你是搞专业的吗?她说不是,就是爱好。 三联生活周刊:台北“故宫”在台湾民众心中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 胡骁:他们博物馆的理念跟我们不一样,咱们这边偏重于收藏和高端学术研究,他们那边收藏和高端学术研究非常发达,但是他们的理念就是一定要进行民众教育。民众教育是他们到了台湾就有的,台北“故宫”历史上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它迁到台湾的时候,台湾受日本统治已经50年了,1945年刚光复的时候,台湾人都没有姓,都是姓日本姓。“故宫”的这些文物和专家去了之后,用这些东西慢慢让台湾人知道,我们是中国人。这些东西像物证一样,因为那些人传播中国文化,扫荡了日本的皇民化教育。所以从一开始到台湾,哪怕是在北沟那么艰苦的时期,他们花了很多钱建了一个陈列馆,让学生去,他们给那些学生讲,这好像是他们的一个传统,一直到现在。现在有了声光电的现代化设备,他们就做得更好了,他们做了很多光盘、影像资料,甚至做成电子游戏。咱们的电子游戏就是打杀,他们有个电子游戏叫《国宝总动员》,讲台北“故宫”晚上闭馆了,那些文物都活起来了。“翠玉白菜”上面有个蚂蚱,叫冬,从上面跳下来跑了,这些文物就开始找冬,宋孩儿瓷枕也活起来了,在那里跳来跳去地去找。谁找到了就奖励谁,比如找到这个东西奖励一个汝窑的作品,就像咱们这边得分一样。然后让小学生去玩这个游戏,在游戏中受到一些历史教育。 三联生活周刊:《台北故宫》在拍摄过程中有什么新发现? 胡骁:有一件事,当年从南京搬去台湾不是有三艘船吗,第三艘船有一个人还健在,就是刚才我说的索予明。那个船上当时发生了一件事,他从来没跟别人讲过,就是船长想起义。船走到长江口的时候突然往北开,北边是解放区,南边是往台湾去,他们就很奇怪,怎么往北边走了。然后这个船上的大副和枪炮官联手把这个船长给架空了,这艘船后来还是到台湾了。这件事儿他一直没给外人讲过,因为当时这个船长好像也没受到太重的处理,他不便于说。在蒋介石时代说你要投共,肯定拉出去毙了,一点不带犹豫的。我约了他四五次之多,他都以身体太坏给拒绝了,这次去我说无论如何要找到这个人,去拜访他,请他能够接受我们采访,他挺感动的,接受了采访,后来把这个事情给说出来了。这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没有被证实,这是他第一次证实,我们在片子里会提到这件事。这件事他在回忆录里也没提过。副船长写过一篇回忆录,没有提到这件事,这些人也都过世了。现在只有他还活着,我问他船上是不是发生过一些很激烈的对抗,他说也没有,就静悄悄把这个船长架空了,走了一个多月,最后才到了台湾。 三联生活周刊:还有什么是第一次披露出来的? 胡骁:迁台的过程是第一次披露,整个台北“故宫”的历史基本上都是第一次披露,比如怎样到了基隆,基隆到了杨梅,在杨梅一个仓库里放着,放了几天又到了台中糖厂,台中糖厂就放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转到台中,在北沟那个十几年的生活从来没有人提起过。台中我们也去了,当时的现场我们也都拍摄了,“9·21”大地震把那个地方都夷为平地了。我们提起这些台湾当地很多人说,还有这回事儿?我们都不知道。他们自己好像都很陌生。另外我们还拍到了台北“故宫博物院”当时的设计图纸。台北“故宫”的一个设计师叫黄宝瑜,在台湾非常著名,他已经过世了,他的子女我们也没找到,后来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找到了他当年的一个同事,叫苏泽,他当时跟黄宝瑜一起参与设计的,我们就采访他,我就问他有没有当年的设计图纸。本来在台湾大学还保存着一份台北“故宫”的设计稿,可是不让我们拍,愁得我没办法。后来我给他打电话,想采访这件事情,我想问问图纸还保存着吗?他说有,都在他那儿,他的是最原始的图纸,而台大那个是复印的。他把最原始的晒图拿出来全让我们拍了。台北“故宫”本来不是现在这样,不是传统宫殿式的建筑,是现代化的建筑,本来那个作品已经入选了,也是台湾很著名的一个设计大师王大泓设计的,一点中国元素都没有。可能现在说是造价太高,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不被蒋介石认可,蒋介石不太喜欢西方的东西,他特别喜欢中国式的东西。但他那个作品又是设计得最好的,又是被评审委员会通过的,可能后来上面不太同意。黄宝瑜当时不是设计师,是评审委员,说设计稿都不行,好不容易挑出一个又被毙掉了,干脆我设计一个吧,他就设计了一个。最让我觉得幸运的是,我们就想拍当初那个设计稿是什么样的,跟现在的对比,但找不到王大泓。就在我们采访的同时,王大泓在台湾的“国父纪念馆”搞了一个他的作品展,正好把他当年设计的“故宫”做成模型在那展出,我们赶紧派人去把它拍下来了。有些事情就是这么巧。 (实习生李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