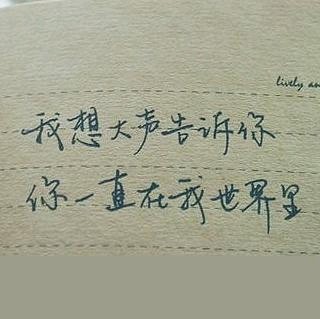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且艺术作品的欣赏和解读本身就有多义性。
BY 吉力

任何一种艺术批评,如果没有建立在一种历史观和理论建构中,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批评要有热情,但感情不能代替分析,分析不能失之随意。要评论一种事物,必须对它做出全面的了解和客观的分析,如此才能“入木三分骂亦精”。否则,心怀恶意恶言中伤,或仅凭一时冲动乱批一气,与泼妇骂街何异?如今有些艺术批评,总让人想起那则经典的故事: 一日,苏东坡去拜访佛印,遇到佛印在打坐,便学佛印打坐。两人结束打坐后,苏东坡问佛印:“你看我坐禅的样子像什么?”佛印答:“我看阁下像一尊佛。”苏东坡听后,心中窃喜。佛印反问:“那阁下看我像什么呢?”苏东坡故意气佛印:“我看你像一坨大便。”佛书云,心中有佛,则观看万物皆是佛,反之亦然。有时,刻意贬低他人他物并不能抬高自己,显出自身的高明,反而自取其辱,自暴其短。 对于上海双年展备受广大观众热爱的排队等现象,有人将其简单化对待,比如把公众的热情参与等同于娱乐化,把观众的积极性理解为盲目性,似乎中国人民就不应该关注和热爱当代艺术,就不可能具备较好的艺术欣赏能力。上海双年展不走极端的道路以博得前卫之名,因为前卫不是一个综合性主题展的全部。作为一个公益性、学术性、综合性的展览,上海双年展的参展艺术家个人可以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而上海双年展本身从来坚持为人生而艺术,坚持关注社会现实,坚持强烈的人文关怀,坚持为城市文化的繁荣添砖加瓦。上海双年展的努力及意义不容置疑,它带动了如此众多的观众欣赏艺术、关注艺术,尤以青年观众为多。可以想见,这些青年观众会影响其下一代,会形成良性循环,从而让中国观众形成参观美术馆的习惯,并在未来的中国卷起更波澜壮阔的艺术欣赏之潮。奇怪的是,为何有些人就不能看到公众热情参与背后的意义?而且对中国观众的艺术欣赏能力如此怀疑? 作为一个群展,上海双年展汇聚了众多艺术家的不同人生体悟、观察视角和创作手法,不应要求普通观众去读懂全部作品。 其实,实在不应怀疑和低估普通观众的欣赏能力,比如有位观众,其父亲是知青,对于井士剑的《移城》,他说:“走进车厢,黑色车厢四壁用米黄色写了个无数个‘正’字,我想这大概是艺术家想用此象征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吧,不管梦是如何,他们都踏踏实实、一笔一画地画出一个又一个‘正’字。”看来“里面的实物很少”并没有妨碍他的欣赏和理解。 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而且艺术作品的欣赏和解读本身就有多义性。如果有可能,陈志光那批蚂蚁当然在别处也可以爬到墙上去,至于在本次展览中,这批蚂蚁的意义不仅紧扣主题,而且寓意深刻。在此,谨借艺术家本人的文字作答:“在同一空间中流动着不同的人群演绎着不同的故事,站在一定的距离看,很多空间中人群的故事和情绪以及个人形象都是模糊的,剩下的只有关于人最基本的形象概念了。在这组作品的创作中出现的蚂蚁每一只也都是各不相同的,但在我们习惯的距离内它们是没什么区别的,都是大小形态相似的蚂蚁。从某种角度看,无论是人还是蚂蚁都在不停地迁徙流动,以类似的姿态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将陈志光的蚂蚁和井士剑的《移城》放在一起展出,更是相得益彰:鲜活的生命即便被抽象为数字,渺小如蚂蚁,但是永远坚韧乐观、各自创造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和传奇,这其实正是“快城快客”的精神。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