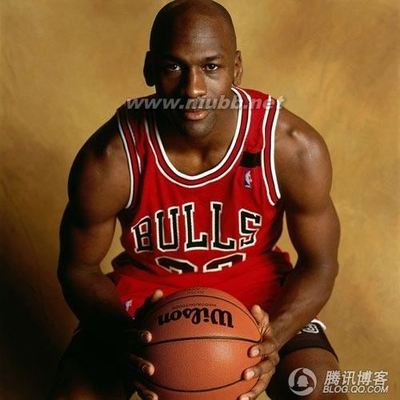我希望好小说能有更多的人读,希望让膨胀中的个体看一看被削弱的个体是如何存在与挣扎的……
撰稿·苗炜 专栏作家
2009年一开始,我似乎闻到了文学的味道,好多人都在读卡佛。这可能是一种错觉,只是周围几个朋友都在看他的小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大教堂》,大张旗鼓地宣传,似乎让很多人注意到这个20年前去世的作家。 10年前,我的领导和我聊起小说家,他说昆德拉等人不过是二流,一流小说家是卡佛。我的这位领导原来就是《人民文学》的小说编辑,他的眼光当然高。他从文学杂志出来之后一直致力于大众媒体,他说“文学承载的信息量太少”。我当时就找到卡佛的小说看,挺喜欢,但也说不上多喜欢。那时候我是个青年,涉世不深,满脑子都是积极进取,改变世界的梦想,根本没理会卡佛小说中的苍凉与失败。此外,我还迷信承载更多信息的大众媒体,以为文学是太个人的喜好,是小趣味。 再看到卡佛是2006年,这次是在互联网上读到的,博客大巴上有一个“寻找卡佛”,博客主人是兰州的一个公务员,他偶然看到卡佛的小说,很喜欢,就设了这样一个博客,把自己能找到的关于卡佛的一切都发布上去,这个博客上也发翻译小说,翻译者叫小二。通过这个博客我找到小二。我本以为小二是个文学青年,没想到他是一家公司高管,上世纪80年代就去美国留学,小二衣食无忧,致力于翻译。我重新阅读卡佛,基本上是通过他的翻译。 这一次读,忽然发现卡佛的好。卡佛说,谁要是写小说,就等于把自己处于世界的阴影之中。其实,谁要是持续地看小说,又何尝不在阴影之中?那些与现实交流不畅的人才会沉迷于虚拟的世界。谁能在阅读卡佛的过程中,不断用自己的阴影去覆盖那些人物与对话,谁就能获得更大的满足。
这一次的发现之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发现,说得夸张一点,那就是我结束了自己有关“大众传媒”的梦想,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已经形成,“大众媒体”那种“信息守门人”的角色已被瓦解,传统的编辑,决定哪些东西对读者是重要的,哪些东西对读者是有趣的,他按照自己的理解来反映世界,可由于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方式有了很大的不同,任何人都可以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去组织信息,他可以找到他认为重要的东西。随便什么人,有个什么特别的爱好,他都能找到同好,都会觉得自己不那么孤独。他不再需要任何阅读权限和发布权限,这就是网络之所以变得强大的原因。我不敢预言所谓“大众媒体”都会消亡,但我真的厌倦那种面对大众说话的姿态。而小说完全是自言自语(博客也是一种自言自语的状态),受众放弃那些高亢的声音,选择自己喜欢的自言自语。我们在互联网上能获得的信息是那么多,再也没有哪一家大众媒体敢于说它承载了足够的信息,再也没有哪一家媒体可以说自己清晰而准确地描述了这个世界。 而从另一个层面说,卡佛那种底层、暗淡、悲凉的故事给这个事事都求成功的时代带来另一种味道,卡佛专写一些不成功的人的故事,也遭到美国右翼评论家的批评,说他没有给美国涂脂抹粉,说他不够乐观,卡佛自己说:“这些人的经历和那些成功者的一样有价值。我把失业、经济和婚姻上的问题当成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人们总在担心他们的房租、孩子,以及家庭生活上的问题,这才是最本质的东西,是百分之八十、九十,或上帝才知道具体比例的生活。” 让我再把自己的困惑说一下,卡佛的小说大多写的是失败者,他们被生活的琐事折磨得筋疲力尽。中国这些年来的主题就是快速发展,是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如果谁应付不了生活,谁就会被当作失败者抛弃,在这样的背景下,卡佛能提供的参照会有什么样的意义?我希望好小说能有更多的人读,希望让膨胀中的个体看一看被削弱的个体是如何存在与挣扎的,尽管我也疑心这样的努力会不会有些不合时宜。但我相信,在某种程度上,浪漫主义者和失败者是同义词,让我们在热闹的、折腾的、大众狂欢的时候,在年景不好、经济萧条、悲观的时候,都保留心里的一点浪漫和柔软。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