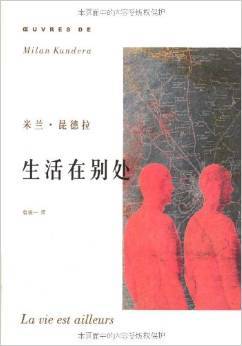大地震那天像一个停摆的时钟,人们再也无法回到之前的时刻了。要让人们大胆地迈向新生活,目前暂时也还只是一个遥远的鼓励。
5月27日,我第二次前往汶川大地震的重灾区。和第一次一样,我先到都江堰,即使被专家验证为没有受损的新楼盘如今依然没人敢入住。在这个“帐篷城市”中,再结实的高楼也看起来“摇摇欲坠”,安全感和信心的重建需要时日。 惊心动魄的大救援持续两周后,灾区的时间仿佛静止下来。人们在观望中等待进一步的政策,等待来自政府的分配——对粮食、物资和住房的分配。如此巨大的灾难夺去生命的同时,也毁坏了这里的成就和经济秩序。灾民们倔强的自救令人尊敬,却不足以恢复这一切。他们期待着一场彻底的国家力量的重建。◎朱文轶
20年的贫富差距没了 在都江堰、青城后山这些邻近成都的著名景区,20多年来因旅游形成的家庭收入差距一夜间被抹平。一些人似乎重新回到了平均主义时代,等待命运也许又一次公平的裁量。 周太军一家5口挤在泰安村一条河边走廊的入口处。他们在5月12日以来东躲西藏,逃避余震,终于在5月26日找到了这个还算“理想”的安身之所。 5月29日的一场小雨,让震后的青城山再现出它的迷人姿态。如果不是大地震,这条去年由村里投资修建的木长廊,会是一个理想的观景之所。因为它正对的那条“飞泉沟”,让1986年前来考察旅游资源的私企老板和都江堰市旅游局官员们一眼看中了青城后山的商业价值,也把泰安村从一个贫困、无力的农业村庄“拯救”了出来。现在,这个500米长廊成了古镇一些村民的临时避难所,收容了七八个像周太军这样的家庭。 象征性隔开这些家庭的,是长廊每个过梁挂下来的一条条花色床单,它们在这个局促的户外空间里制造了“家”的概念。白天,床单被撩起来;晚上,它多少保护了一些家庭隐私:泰安村的邻居们从来没有住得这么近过。“总比帐篷好。”周太军说,“不用两户人家挤在一起。” 5月28日,又有50顶帐篷从青城山镇送到了泰安村。这些天,新到的物资不断往山里运,不过,还是不够。整个泰安村有1400多人,随着旅游生意的深入,这里不断接纳外来的开发者,近10年内超过400名外来者在泰安定居,新的外来人口还在陆续涌入。泰安是青城山镇里的“大都市”,帐篷没有把这些新移民统计在内,甚至也没有计算到那些没有户口的人。 按照以往的防灾经验,帐篷的数量是按照受灾人口派出的,泰安村大概分到了200顶,7到8人要共用一顶。旧经验没有考虑到1个月甚至3个月以上的帐篷生活——而这次地震和以往灾难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彻底毁坏了居住——帐篷不仅用来应急,还要应对相当长时间的生活过渡。让两家人几个月挤在一个帐篷里显然不太合适,要是以“户”为单位,泰安村一下子就出现了至少200顶的帐篷缺口。泰安只是一个缩影,局部压力汇聚到全局,帐篷严重短缺成了这次抗震救灾从5月19日开始就要对付的大麻烦。 人们回到了一种公共生活的状态。生产队、大锅饭,这些消失了的组织单元和分配形式又一次出现了。村民们200多人一组共用一个灶,到吃饭时间,泰安古镇空旷的街道上就会出现长长的打饭队伍,大家端着锅碗瓢盆,聚到一起,或者把饭打回“家”。 村民大多家里是开餐馆的,他们把储存的蜂窝煤搬出来凑在一起,一天的烧饭煮水得耗掉将近100个蜂窝煤。不过,救灾物资里没有蜂窝煤,一周后,所剩无几的蜂窝煤撑不了多久了,这很是困扰泰安村人。 周太军说,他们没办法预料这样的生活还会持续多久。旅游旺盛的好时光,像花一样,刚盛开就枯萎了。对于城市人来说,旅游是一种可以替换的娱乐,对他们,却是命根子。与离他们不远的都江堰不同,城市人用不了太久会回到既往生活的轨道上,新的城市生活在召唤他们。他们很快会克服房屋摇晃带来的心理障碍,许多人会回到工厂;一些人可能还会因为城市出现的新面貌而产生新的希望,获得新的机会。对这些青城后山的农民而言,生活方式有可能再次被根本性地颠覆了,就像20多年前突然发生在他们中间的变化那样。
青城后山的商业开发在1986年启动,农民们被引导到旅游这条道路上来,为此,农民们一点一点放弃了土地。先是乡里以每亩1000块钱的价格把村集体土地卖给了前来开发的企业和私人老板,这笔交易现在看来简直是赔了老本,但当时每个村民都被一下子分到的几百块钱弄得欢欣鼓舞。泰安村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农村更早尝到土地流转的甜头。 为了加快这个新旅游景区的成熟,两条政策再次加速了农民远离他们土地的进程。一是保护后山生态,政府对这里实行大规模的封山育林,农民告别耕作,退耕还林,玉米地和土豆田几乎绝迹了。二是实行宽松的信贷方针,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政府鼓励农民大胆贷款,所有信用社对农民敞开大门。曾祥贵是村里的老书记,他现在有些陷入自我否定的情绪里:他不知道当年自己对这些事情投的赞成票,是帮了这个村子,还是害了这个村子,尽管这一切实际上并不由他说了算。 建设这么大的景区,光靠政府财力当然不济,第一次投入由都江堰市28个乡镇筹资分担。这笔钱远远不够,最好的办法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向他们许诺前景和信心。人们很快被调动起来了,周太军,甚至包括曾祥贵本人,都加入了这场致富风潮。 周太军一次就借了15万元,第一批“农家乐”的参与者至少都借了这个数。借来的钱全部投在了房子的建设上,大大小小的私人旅社一夜间就在山沟里林立起来。与很多当地人一样,周太军毫无经营经验,刚开始只是把房子租给那些前来淘金的外地人,后来他们都按捺不住了,把房子收回来,自己当了业主。还有一些没有胆量伸手借钱的村民,则拿土地做筹码,出让给外面的投资客建设旅社,投资方承诺,20年经营期满,房产归村民所有。周太军们完成了由农业生产者到小业主和消费者的身份置换。 农民们被带入了一种看上去欣欣向荣的秩序里,青城后山的势头比商业化年头更久的青城前山还要好。人们把挣来的钱全部投入到旅社的建设和维护上,干净体面的住宿环境为他们换来更多的钱,他们把钱还了债务,然后继续贷款。青城山的未来支付这一切——而这秩序被地震瞬间摧毁了。 用借的钱盖房子,农民们虽然节省,用的是最简陋的砖混结构,不过全都是真材实料,不会有人拿自己的产业开玩笑。这些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老房子,大部分都挨过了5月12日,这使得整个青城山镇基本上躲过了惨重的伤亡。“但里面全坏了。”曾祥贵说。对景区来说,房屋疏松跟完全坍塌没什么两样;更重要的是,整个大环境和大气候不复存在。周太军去年刚刚还清了20年前的15万元贷款,为了把旅社里所有的普通房升级成标准房,增加卫生间,他又接着贷了12万元,4月12日完成了翻修,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现在,他破产了。 “苦了20年,两分钟就没有了。”现任村长李桂伤感地对我说。20年来,旅游将财富不断带到这里,一系列巨大外力作用下,青城山镇正按照某种既定的规律分化。14个自然村的地理位置为它们在5月12日以前的命运已经做了注解:泰安村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这场变革的最大受益者,它和那些靠近旅游路线的“过道”村子分享了机遇;另一些村落分布在山头,远离干道,则和财富无缘。但5月12日,来自经济和体制的外力,遭到了来自地壳深处的自然力量的狙击——持续20年的滑动中止了,农民们和14个村子重新被拉回到了同一条“起跑线”。 李桂说,相比之下,那些长期被边缘化的村子现在因为拥有土地,倒可以自力更生,而将赌注全部押在房产上的小资产者却失去了一切生产资料。人们似乎重新回到了平均主义时代,等待命运也许又一次公平的裁量。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