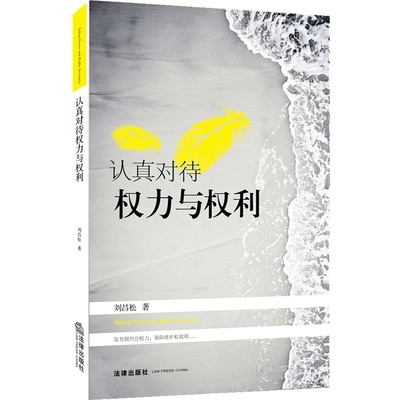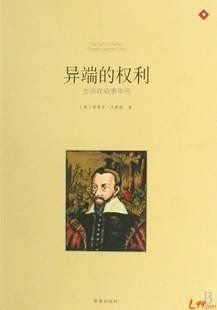王军 媒体有关凉山童工事件的报道再次将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人道主义问题推至舆论焦点。毫无疑问,以欺诈、暴力手段拐骗或强迫儿童从事劳动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应予严禁和惩处。但是,对于那些迫于生计而自愿或父母同意其务工的未成年人,法律一律禁止他们务工是否有足够的正当性?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4月10日,记者在凉山采访童工马海布的母亲时表示,“你儿子在那边很可怜,两三天才能吃到一顿米饭”。但他母亲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两三天就能吃到一顿米饭?”这位前几秒钟还在为儿子失踪而痛哭的母亲,突然变得一脸惊喜。 童工现象源于贫困。记者发现,有些被解救的童工不愿离开工厂,因为回家意味着再次陷入令人绝望的贫困。如何减少和消除童工现象,多数意见认为,法律应该禁止工厂雇用童工,同时国家和社会应加大扶贫投入。人们无法容忍儿童在工厂从事生产:“榨取童工血汗”的工厂是不道德的,容忍童工现象的社会同样不道德。可是,禁止童工的法律无法消除贫困,被解救的孩子离开工厂后并未得到生活保障和上学机会,他们的生活可能变得更加困难(例如,可能转移到那些易于逃避检查而条件更差的工厂务工,甚至丧失基本生存条件)。 对于赤贫者而言,唯一能够支配的“财产”可能只有自己的劳动了。通过自己的劳动维持生存进而摆脱贫困,是贫困人群的天赋人权和希望所在。如果家庭、社会和国家无法保障贫困儿童的生存、发展和受教育机会,那么,禁止童工的法律无疑就剥夺了贫困儿童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的天赋权利。因此,道德的法律可能存在“不道德”的一面:童工禁令的有效实施伸张了国家和立法者的道德观,查禁行动也“大快人心”,但被保护或被解救的贫困儿童的境遇却没有改善,甚至变得更糟了。 禁止或限制童工的法律由来已久。罗伯特·赫森在《工业革命对妇女和儿童的影响》一文中阐述:在英国,1819年到1846年间陆续通过的工厂立法对雇工条件施加越来越严格的限制。大型企业最容易也最经常受到检查,这些企业越来越多地选择开除童工。法律干预的结果是,遭到开除但仍需要工作才能糊口的儿童,不得不到老旧的小工厂、小作坊找工作,这些小工厂容易躲避检查,而卫生条件和安全状况却恶劣得多。那些无法找到新工作的儿童则只能从事临时性的、更为繁重的农业劳动或者沦为流氓、乞丐等。英国童工现象在日后的逐渐减少并不是童工禁止法的功劳。当父母们的收入足以养活孩子,在经济上不必靠孩子的工资就能养活家人的时候,童工就自行消失了。 童工报道激起民愤,但“事实上的童工”现象在我国司空见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大多数农村家庭的孩子们在很小的年龄就开始跟着父母从事农牧或者家务劳动。我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够衣食无忧、快乐成长并接受良好的教育。但现实没有如此美好,贫困客观存在,而相对贫困可能是长期难以解决的问题。当国家和社会没有足够的力量援助每一个贫困家庭的时候,法律没有理由禁止贫困的人们通过劳动实施自救。当一个贫困家庭不得不用儿童的劳动增加收入的时候,法律应该提供清晰可行的规则限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滥用监护权,督促他们履行监护义务,要求并监管用工单位提供适当强度的工作、保障未成年人权利,而不是简单地一禁了之。 实际上,即便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用工单位雇用“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也不是绝对违法的。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制定,2006年修订)第三十八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招用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应当执行国家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的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等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可见,从法律上细化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明确政府监管职责,为贫困家庭的孩子(包括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可靠的劳动保护是可能的。 对于童工事件,有人建议检讨财政政策,尽快建立农村地区最低收入保障。这些建议当然不错,但远水不解近渴。而且,过度依赖外部救助的减贫措施已被证明是低效甚至无效的。贫困虽然表现为物资短缺,但其根源却是权利的匮乏,包括法律不合理地压制贫困者的自救和发展机会(可参阅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和尤努斯《穷人的银行家》)。因此,国家在增加扶贫投入的同时,通过扩大贫困家庭的选择自由(包括放宽十六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的务工限制),确保贫困者劳动自救、自力更生的权利(包括保障各项劳动者权利和获得小额贷款的机会),恐怕是扶贫并最终消除童工现象的更为根本和有效的方针。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