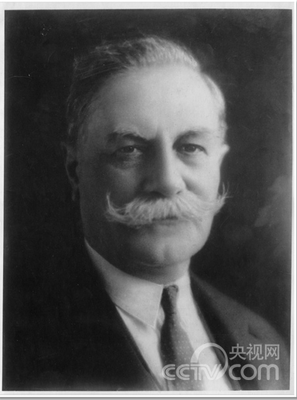一个城市能建造起来,但城市生活不是建造起来的。
撰稿·苗炜 专栏作家
要说三里屯的历史,恐怕诗人大仙最有发言权。他是一个脸庞宽阔、头发稀少、走路蹒跚的老哥,他身边层出不穷的姑娘充分证明了一个男人的魅力主要靠内在,跟外在关系不大。他快50岁了依旧在外边鬼混,所以我跟他在一起就不担心自己老。而且,北京的确有一帮“大叔控”,这是个日本单词,意思是喜欢和老男人混的小姑娘。 有一天大仙又用对诗这一招儿把一姑娘灌高了,他带着那姑娘来到“海上”,姑娘在沙发上睡觉,大仙和我们接着喝酒,没多一会儿,那姑娘的父母找来,当爹的头上缠着白羊肚毛巾,断定此地为魔窟,扬言要把酒吧给砸了。几大好汉一字站开,十分雄武,好像捍卫的不是一间酒吧,而是世俗乐趣,对抗的也不是一个父亲,而是清规戒律,当时我也忝列其中,主人翁精神把我脑袋刺激得嗡嗡响(更主要的还是因为酒精),仿佛参与了一场三里屯保卫战。后来这对父母偃旗息鼓领着闺女回家了,大仙这才从洗手间里出来,如梦方醒:“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儿?”
在这里溜达绝对不孤独。除了蹿出来拉你去他们家喝酒的酒保,还有突然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神秘人士。“到我们那儿吧,有美女!”后来拆拆修修,好多人就“倏”地不见了。我在一个胡同四合院里见过一次冰冰,她是南街音乐圣地芥末坊的老板,酒吧被拆,凭吊的冰冰却格外平静:“7年前开店时就说这条街将要拆掉,如同你的女朋友天天说分手,最后真正分手的时候却容易接受。芥末坊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初恋,是梦开始的地方,是成长的地方。这条街就是一个舞台,很多人来到这里表演,我也身在其中。”我在她那儿吃了一顿精致得不像样的私房菜,喝着盖碗茶,一个曾经叱咤的老乐队成员在院子里悠悠练琴。我手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一离开三里屯,大家都变得不那么好玩了。 最近,三里屯开了一大片新商店,有中国第一家苹果店,开张头一天夜里有2000多人排队,店里每天都满满的。还开了阿迪达斯的旗舰店,里面有Y3、斯黛拉·麦卡特尼的设计,还有宝马生活馆。这片商店的模样,看着怪怪的,怎么也不像三里屯原本的小店。现在我还去三里屯,不过只喜欢一家,我叫它“西红柿餐厅”,大名叫POMODORO。老板季哥也是摇滚老炮,大家都清醒时,我正经八百地问他:“您为什么开餐厅呀?”他白我一眼,别过脸去,好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操!好吃呗。”我更仰慕的还是虽从未谋面却见过许多次的大老板——也就是餐厅洛杉矶总店的创始人。他的照片密密麻麻挂满了整间餐厅,每一张他都搂着一个好莱坞明星,年头跨度很大,既能见到正水灵的凯特·耐特莉,还可以一窥小伙子版汤姆·汉克斯的风采,每到那里,我都会点一份生肉披萨,菜单上写着“这是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最爱”。所以这家餐厅还有一外号叫“好莱坞的金鼎轩”。金鼎轩是北京一家连锁餐厅,24小时营业,喜欢贴上葛优、田震等明星和服务员的合影。可惜,从这里出来,就会撞见突然拔地而起的大购物中心,那里灯光炽亮、一尘不染,汇集着以蔑视俗世乐趣为美德,仅把物欲当作有益健康的上天恩赐的家伙。 你要说三里屯的变化是好还是不好,我说不清楚。不过,我最不喜欢的是后海和南锣鼓巷,这两个地方原本是老北京的地盘,如今都按照西方景似的弄了堆酒吧,我总觉得这是西方对东方的侵略,后海和锣鼓巷就应该是北京小酒馆,至于三里屯,离使馆区近,就留着给西方人便利一下得了。有时候,想想也怪了,三里屯多年来有许多变化,但比起北京城里其他一些地方,变化还算小的,那条街整体上还能认出老样子,十来年前在那里混的人,现在还时不时在那里出没。北京奥运期间,恐怕还是工体附近更有人气,在工体看完比赛,周围的夜店肯定会热闹一把,而鸟巢附近,全是地铁站、公共汽车站,全是冰冷的道路和建筑,一个城市能建造起来,但城市生活不是建造起来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