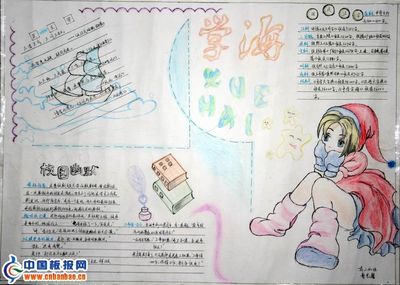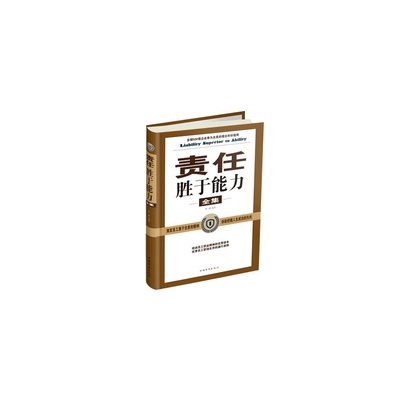汪丁丁 经济学家的基本信条是“天下没有免费午餐”。那么,制度化的代价是什么呢?我认为,制度与自由是一对矛盾,是“表”与“里”的关系,同时需要增加一些论据,是关于“情境理性”的。 张五常教授将“cost”译作“代价”而不译作“成本”,因为在经济学家看来,成本与价格是同一件事情的两种表达方式,虽然从会计学角度看,价格里面包含了成本之外的东西,叫作“利润”。十几年前,我告诉过一位朋友,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只有两个,在本科生水平就是“成本”,在研究生水平就是“利润”或“租”。汉译“成本”,我估计又是受了日译的影响。但“成本”的“成”字扭曲了经济学“机会成本”的确切涵义,反而有了“会计成本”的涵义。而“代价”的“代”字,更能传达“机会成本”之“机会”与“替代”的涵义。任何事物或观念,只要我们试图加以制度化,就意味着我们将要放弃一些机会,从而意味着放弃那些机会可能产生的收益,而被放弃了的“机会收益”当中最高的,就叫作“制度化的代价”。 剩下的问题,只是要来寻找,当我们制度化一件事物或一项观念时,我们必须放弃的是哪些“机会收益”。随着我对中国社会理解的逐渐深入,我逐渐意识到,制度化与不制度化,二者之间最严重的区分在于,前者无视任何具体情境而后者是“情境依赖的”。这看起来有些“同义反复”,因为“制度化”的本义难道不是“抽象到可以涵盖一切情境”吗?是的,不过,我提醒你,世界上一切重要的领悟,说穿了都是同义反复,也因此,怀特海认为在有理解之前先有表达——不同的表达方式导致不同的理解,同义反复就是换一种表达方式从而导致一种不同的理解。

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口号意味着基于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异性的“实质平等”可能要求的不平等性,被遮蔽了。比较而言,中国传统的基于“情理”的正义,更关注特定场合与情境内的实质平等。如果我们拘泥于法律的抽象平等,当真不考虑具体情境,我们的法官将面对许多荒唐的案例,其中一例,最近由一位法学界朋友告诉我的——关于新近出台的交通法,似乎是在广东某地,导致一辆摩托车非要撞到一辆停在路边的奔驰车,然后援引交通法关于“机动车辆”的条款索赔。据说,法官拒绝这项索赔,因为被告可以援引“物权法”的相关条款——奔驰车既然是停在路边的,就应是“物”而不再是“机动”的车辆。于是,肇事的摩托车侵犯了他人的物权。 再例如“代议制”,其核心的观念其实早已存在于几乎一切人类社会,就是奈特在1942年的一篇文章里描述的:每一社会都有一些被认为“重要的”社会成员并由他们关于“什么是重要的”达成共识,从而社会能够提出和求解“重要的”社会问题。奈特在那篇文章里,其实提出了“演化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 为什么不能实行“直接民主”呢?因为——至少我认为奈特是这样考虑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或不平等性,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基本事实。一个伟大的社会,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保护和鼓励(而不是无视和扼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所谓“劳动分工”的制度也正是对这些差异性的保护和鼓励。既然如此,在所谓“公共事务”(也就是被认为具有重要性的那些社会问题的求解)方面,就会有一些人比其他人更经常地做出正确判断,于是其他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就会更经常地听从这些人的意见。西蒙教授曾仔细研究过这类“社会认知”现象,他认为这是符合“有限理性”假设的——因为“有限理性”,所以听从更明智的人的意见。 当然,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在不同的公共事务上,社会可以有不同的被认为重要的社会成员。很少有人能够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被其他社会成员认为是“重要的”社会成员,这就导致所谓“专家”的涵义。换句话说,只要我们在一些事务上愿意听从专家的意见,我们就在最原初的意义上实行了“代议”。注意此处“愿意”的涵义,它意味着专家的权威是韦伯所说的内在权威,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听从,它不需要任何外在力量的强迫。否则,我们就永远只能以“强权”而不能以“社会契约”来解释“政府”和“国家”的起源了。 从“代议”到“代议制”,如这篇文章的标题所示,是制度化的过程,它在西方社会里发生了,然后被西方文明带到了全世界。如前述,许多事物和观念一旦被制度化,就将无视具体的情境。由此导致的代价,或许在西方社会里低至可以接受的程度,所以在最近两百年里被普遍地实行了,但或许在中国社会里高至不可接受的程度呢?这是我最近思考的问题之一,与我一直鼓吹的“情境理性”或梁漱溟先生鼓吹的“理性”(而不是西方人的“理智”)有密切的关系。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