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向喜欢具有社会文化视野的心理学家,因为他们能看到人的行为、人的所谓“心理问题”的复杂性。他们不会简单地将问题归结于人的童年经历就了事,而愿意去了解人的内心冲突是怎么建构出来的,在其中社会文化起了怎样的作用,他们又是如何与之抗衡的。 套用波伏娃的“女人不是天生,女人是变成的”,我们也可以说,很多“心理问题”不仅是被社会文化催生的,也是被社会文化建构、界定出来的。具有这样的视角,或许更能跳出技术化的陷阱,同时也更容易转换视角,将“问题”看做是一种对文化,特别是病态文化的对抗与斗争。 霍尼在书中提出三种神经症的文化来源:竞争所带来的敌对性紧张,即以竞争和成功为一方,以友爱和谦卑为另一方之间的矛盾;各种需要所受到的刺激和满足这些需要时受到的挫折,即被刺激起来的需要(如高消费)和实现之间的差距;个人自由和所受到的局限之间的矛盾。 无疑,霍尼所提到的“时代”的、“集体的”神经症,无论是症状还是原因,在当下中国都有丰富的体现。 比如,日渐庞大的“国考”队伍,年轻人从“逃离北上广”到“逃回北上广”,这些行为背后掩藏着怎样的焦虑?是不是年轻人越来越感到只有进入体制才能获得安全感?是不是小地方“拼爹”的文化,让他们宁愿承受大城市的生活压力,也不愿意在缺乏公平公正的环境中生活?这样的选择会不会带给他们巨大的内心冲突? 还有另一种更加隐蔽的情况,如霍尼说的“有许多人,虽然表面上看完全适应现存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却可能有严重的神经症”——为了欲望,为了安全的需要,有时人们会认同、顺从、屈服于某些自己也并不相信的东西,但最后总要付出极高的心理代价,因为他无法避免激烈的内心冲突。 以我看,中国人的种种集体神经症,不排除传统文化对我们人格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感受到作为人的自主性,无法感受到我们对自己的生活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预期和把握的。对自己的生活、未来无所适从,那我们又该如何摆脱内心深处的不安与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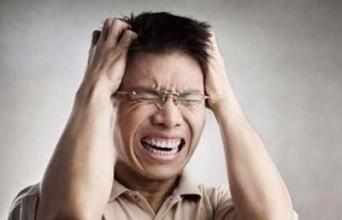
 爱华网
爱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