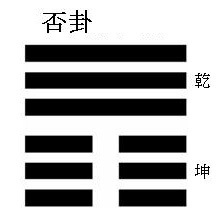“他骂我‘书呆子’,我说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碰上了一个‘疯子’。小堡村从1994年到今天,没有我不行,没有他也不行。”老栗这样形容他和小堡村支书崔大柏13年的合作。
◎ 曾焱
为什么是宋庄? 在老栗的叙述里,宋庄给他的感觉,更接近19世纪中期法国画家米勒他们住过的巴黎近郊小村庄巴比松。艺术家的画室被农民的房子分散在村子的各个角落,画室大,环境安静。如同米勒他们在巴比松一样,宋庄的艺术家同样过着一种以画画为职业的生活。 几年后,宋庄艺术家里面那些成了名的,几乎每个人都遇到过同一种提问:为什么会是宋庄?老栗在他写的一篇文章《只是想住农家小院》里,其实说了他的答案:纯属偶然。“有人把艺术家的聚集和这个地区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说事儿,就像当时把艺术家的聚集和圆明园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说事儿一样。但是,在我的印象里,无论是圆明园还是宋庄,艺术家聚集在这些地方纯属偶然,尤其与这些地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无关。扯上这些文化和历史的背景并不能抬高这些艺术家,如同说艺术家和聚集地的文化历史背景无关也不能贬低这些艺术家一样。” 第一批买房的人里,张惠平是近年在媒体上出现不那么多的一个,但最初这些人能到小堡村来,和他有最直接的关系。圆明园时期,张惠平画画,也开了公司,属于这帮人里经济状况比较好的,要好的几个人常去他公司食堂吃饭。老栗做完《后89》的展览后,和方力钧、刘炜等人接触很多,而方力钧和王音、杨茂源、张惠平、田彬以及杨少斌、岳敏君经常在一起吃饭聊天,离开圆明园的计划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商议的。 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计划过找别的地方,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开始讨论这个议题的,但我知道他们一定需要大的工作室,所以只能选择郊区。离城市最近的郊区是通县,决定到宋庄,是因为张惠平的一个学生是宋庄小堡人,他提供的消息说,宋庄小堡有不少农民进城居住,村里有很多空院子,于是决定到宋庄小堡看看。”进圆明园之前,张惠平在通县师范学校教美术,那个小堡村的学生叫靳国旺。 老栗说,每一个人到宋庄都有不同的想法。最初打动老栗的,是从北京城里去宋庄沿途的开阔河床和一望无际的黄土地,这些久违的景色唤起他对北方农村的童年记忆。他记得第一次去宋庄是1994年初春,天气还很冷,他和刘炜坐着刘炜妹夫开的一辆北京吉普,杨茂源开另一辆吉普带着杜培华、王音等人。到小堡村,他们看了不少院子,第一个印象是这里的院子可真大。老栗喜欢上了那些已经破败的院子,青砖灰瓦、白墙黑柁,深褐色的老式花格子窗户,窗前一棵弯弯曲曲的老石榴树,房顶上有荒草在风中沙沙作响,“童年生活过的环境和眼前的情景混在一起,使我的宋庄之行有了一个幻想、浪漫而怀旧的开端”。 岳敏君对自己第一次去小堡村的描述没有任何浪漫,只有现实:过完春节不久,他和几个朋友说去小堡村看看。那天得有五六级大风,村里真的是飞沙走石,尘土飞扬,给他的感觉是自然条件恶劣,到处堆有垃圾,房子大都破败不堪。但当时实在没地可去了。他和朋友之前去香山附近看过房,那片地区和他们想离开的圆明园同属一个派出所管辖,想来以后日子不会好过。也去密云看过,比宋庄离城更远,从东直门坐长途车过去得要两三个小时。比较之下,宋庄是唯一可以接受他们、也是他们可以接受的选择。 到小堡村看过房的这些人,最后决定买房的第一批是6个:方力钧、刘炜、张惠平、王强、高惠君和岳敏君。 老栗是退缩的那一个。首先他不需要大画室,倒是需要经常出现在北京城里的各种展览上。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当时失去公职,未来生计尚无着落,没有闲钱买房置地。但方力钧还是力劝他买。当时刘炜有两个院子,方力钧说,你也不给老栗一个?刘炜就把其中一个院子送给了老栗,当时的价格是5000元,老栗称之为“刘炜的厚谊”。他开始修房是1995年春天,当时他在城里的工作还很多,朱冥、马六明等艺术家都帮他监过工,朱冥还在他的院子边监工边表演作品。接近完工的时候,老栗要到美国和加拿大去讲学,方力钧就负担了工程的收尾工作,他说老栗你不用管,我来帮你收拾了。老栗在美国待了两个月,回来的时候院子长满了荒草,连大门都推不开了。 岳敏君的院子花钱多一些,1亩地大小,2万元。看房的时候,他喜欢上院子里面那几棵大树,没还价,隔天交完钱再进院子里一看,傻了——树刚被房东给放倒,正装车往外运。他的红本土地使用证也找不着了,只好让村支书崔大柏手写了一纸证明。 那年夏天,杨少斌和马子恒这些还在圆明园的人听到消息,紧跟着到小堡买了院子。杨少斌说他当时手里有卖画挣的5万元,花2.2万元买了一亩二分地——给农民1.7万元,村里在土地使用证上盖个章,收5000元。房东家三代人,他从儿子手里买的,那张宅基地图纸还是解放后土改时期划的范围。杨少斌和方力钧是同学,加上高惠君,3个人在宋庄早期来往比较多。他记得高惠君的院子是5000元买的,张惠平的房子当时修得最好。“老栗和刘炜的院子面对面。我和老栗也近,他家在前排西角,我在东角,也就五六十米距离。刚开始过得艰苦,小土坯房,床也没有,1995年春天我父母过来住,用砖头和木板搭了张床。1995年5月正式住过来,就这么在小堡村待下来了。”杨少斌说。 村支书的想象力 小堡村支书崔大柏现在谈起对宋庄、“798”艺术区、上海莫干山路和深圳大芬村的艺术市场优劣比较,可以深入浅出一口气分析半个小时。当年他可没有想过,自己的小堡村有一天会因为艺术和艺术家在全世界出了名。1999年前,村里还是以农业为主,300亩西瓜地、白菜地,200亩蔬菜大棚,600亩果树,现在一点踪迹都看不到了。 1994年开春后,村里那个叫靳国旺的学生到村委会找到他,报告家里想卖房子给画画的,他妈娘家有几个亲戚也想卖,请他在手续上签字。“靳国旺告诉我买房的人能出到5000块,我说那就赶快卖。”崔大柏说,那时候的小堡村委会对农民出租土地和卖房不干涉,只是开会定过一个底价,一水房作价1000到2000块钱,比这个数高当然更好,低了他不签字。至于卖给什么人,一概不管,“那天我只知道来买房的人是画画的,什么当代艺术,没听说过”。 “那天老崔没多问什么,也没感觉到他有为难我们一下的想法。之前为找房子也去过不少村,感觉老崔比其他村的书记有水平。”岳敏君说村委会那时还放置在老村子中间,没暖气,开个大空调,崔大柏裹个大棉袄坐在屋里。 崔大柏经常强调一个概念,那就是他和老栗、方力钧他们这些人的私人感情和信任程度是建立于上世纪90年代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不可再造的,所以中国也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小堡村。崔大柏原来也不知道这些画画的人有多大本事,直到1999年,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又来找他批地盖新的工作室,他知道这些人画卖的还真不错,“有钱盖大房子了”。再过三四年,他开始在很多报纸上都看到这些人的名字一遍遍出现,小堡村也被外国媒体不断写到文章里面,他知道,一切都不同从前了。 岳敏君说老崔这个人比他见过的其他基层干部有想象力,“他能直觉到什么对他有利。镇里警察开始都是直接来找我们,老崔就不高兴,说我们村委会也是一级政府,凭什么跳过我们。后来就是村干部带着警察来找艺术家”。岳敏君说他们那几年其实很老实,也比较紧张,基本不在宋庄搞什么艺术展览活动,也不给老崔出主意,怕给他惹麻烦,“能安稳住着就不错了”。他们去小堡村买房的时候,崔大柏并不知道有圆明园艺术村这回事。虽然圆明园被警察彻底清理是1995年的事情,但实际上在1993年、1994年,聚集在那里的流浪艺术家已经遇到了麻烦。崔大柏现在说的是,当年就算知道圆明园的事情,他也不会在意,“我不过想让村民多点收入。有人租村里房子,还不用给人中介费,这是最省事的,为什么不干?” 崔大柏自然也没有听说过栗宪庭这个在艺术界已经被有些人呼为“教父”的人。1995年他才第一次见到老栗,那时候方力钧、岳敏君他们已经进村一年多了。据他记忆是老栗去家找的他,聊了几句,时间不长,“一个挺好的老头,头发没有现在这么白”。老栗那年其实不到50岁。崔大柏说,直到2004年修建宋庄美术馆前,他和老栗见面还很少谈村里的文化项目之类,只是闲聊天,说说种树的事情,“我那时也还没看出他是那些人里面能做主的”。 1995年,小堡村这边第一批来的艺术家已经盖完房子,生活和创作都开始进入状态了,圆明园艺术村那边,警察开始彻底清理。小堡村于是陆续迎来了从圆明园出来的艺术家,警察的注意力也转移过来。老栗记得小堡村委会有段时间不准艺术家买房了,后来的人只好转向宋庄镇的其他几个村子,比如任庄、大兴庄、辛店、喇嘛庄等。1996年,镇里和区里领导开始对小堡村招画家来租地的事情关注起来。那两年,通州区定了两个治安乱点,一个是小堡,另一个是耿庄。1997年是小堡村受到压力最大的时候,崔大柏天天被叫到区里开治安会、“打招呼”,区政法委书记亲自主持。 有关部门对小堡村这么严防死守,崔大柏说他还真没觉得有多大心理压力,用老栗的话来形容他,一个胆大包天的“疯子”。“我让村民多挣点钱怎么啦?又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不怕上面撤他的职,“那时候让人当村支书,还要先做几天思想工作。我当不当这个官真的无所谓”。崔大柏1978年高中毕业回乡,当了几年大队民兵连长,1984年离开大队自己出去干泥瓦匠,1986年又回来,当上村支书。1994年画家高惠君买的那个院子,崔大柏说就是他当泥瓦匠时候盖的。他重操旧业是20年后了,现在村东头有片利用旧人防工事兴建的新艺术园区,崔大柏不请设计师,自己管了这个园区里面的全部房屋设计。 村里这些艺术家有时在家里办很热闹的聚会,有人邀请过他,他从来不去。崔大柏说自己有个“弱势”,就是不喝酒,不喜欢凑热闹,对艺术家喝多了酒之后的样子也不适应。遇到村民和艺术家有纠纷,大部分在他的民兵连长李学来那里解决掉,如果闹到他这里,他也愿意调停,但一定要听他的处理。有一次,画家王强扩建自家院子,误砍了邻居的树,村民告到村委会,崔大柏让王强赔点钱,王强觉得不公平,不认他这处理,崔大柏就命令管治安的李学来给他那个院子断电断水。僵持两天,画家气得搬到任庄去住了一段,“现在他又搬回来了,在村里东区那边起了工作室”。崔大柏说他们俩现在见面气氛也很好。李学来和王强一起吃饭,喝完酒想起那事,王强还指着他鼻子,说你当年带人掐我的电。 李学来说他平均每周处理两起纠纷,80%的村民和艺术家都认识他。村里人都知道他从前和艺术家关系不好,老打,以观念摄影成名的王庆松、罗氏兄弟,都打过,“遇上事儿,老跟你讲法律,讲民主,讲得人心烦意乱”。他的办公室在村委会办公楼一层最顶头,挂的牌子是“民兵连连部”,窗台上摆了个小泥人,是去年一个搞雕塑的艺术家送的。沙发靠背上搁了3张小油画,是他自己在今年宋庄艺术节第一届“艺术集市”上买的,花了75块钱。李学来说觉得自己和艺术家还是有共同语言,因为从前在村里做过油漆彩画,画房梁,“到哪里提崔书记和我的名字都好使,跟提老栗一样”。“范围在小堡村内。”他又补充了一句。 万物生长
爱伦堡写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其中一篇说到俄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1924年在巴黎的经历:诗人慕名去蒙帕纳斯艺术家的据点洛东达咖啡馆,但已经找不到那个乱糟糟、臭烘烘的咖啡馆了,而是一座“业经修缮、扩建并重新粉刷过了”的名胜,导游不断在旁边指点给游客看,谁谁曾在哪个角落,用一幅画换一杯酒。 这场景,也许会有一天在小堡村再现。如果问起宋庄最好的时期,接受采访的艺术家想一想后,多数人会或迟疑或坚决地回答:2000年以前吧。他们指向的是精神和内心状态。“艺术聚居区在宋庄早期,有自由主义的形态,但到2000年不再如此,有人找机会来了,这是一个分界线。这是任何一个艺术聚居区都面临的结果。”老栗说。 方力钧在圆明园时期就成名了,岳敏君、杨少斌等人也不是全无名气,香港和国外的一些画廊都和他们有联系了,开始卖画了。杨少斌记得他有幅1平方米大小的油画卖了500美元,很是激动了几天。正是由于早期聚集于小堡村的这批艺术家在当代艺术中的名声,使宋庄具有当代艺术的招牌性质。可老栗说,回头来看圆明园和小堡村早期的这些艺术家的状态,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触:艺术不重要,自由的生活才是重要的事。“艺术家把职业化的生活方式作为聚集目的,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现象,它意味着作为一个艺术家决定走自由和独立的生活道路,尽管这种自由和独立不能保证其艺术品格的自由和独立,但生存方式会给艺术创造带来影响,而且整体的看艺术家的职业化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文化管理体制起到不可估量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看,圆明园是宣言,宋庄是试验。” 每天中午起床,骑10分钟车去燕郊吃饭,下午画画。杨少斌说,刚去头两年,村里只有一条路,一个小卖部,一家餐馆,经常停电,一到晚上无聊得很,大家就一起喝酒、打麻将,或者谁说一句“进城吧”,搭公车到三里屯泡酒吧到天亮。 老栗在2000年前不常过来,他的院子主要给几个年轻艺术家安身,先后有罗氏兄弟、郝秀丽、孙国娟、伊德尔等人住着。但每年大年三十他都回小堡来,城里还会来些朋友,三五十个人一起包饺子,每年都要包上千个,和面、和馅是老栗的活,也不让别人插手。后来老栗盖了新房子,厨房也奇大,据说最多一次有上百人用餐。 另一个日常据点是方力钧的家。有时是他父母做饭,他们到饭点就去蹭吃,老栗有时也在。2005年后没有这种日子了。艺术市场最好的时候,打电话找人,不是在英国,就是在美国,总之见面很少。早期那些小堡艺术家,现在都有不止一处工作室,大理、丽江、海南,都有。老栗说,这些工作室我没去过,他们的画展也很少参加了。 做当代摄影的艺术家海波没有经历过圆明园的生活,代表了小堡村另一类艺术村民的成分。1996年正式加入北京自由艺术家行列之后,他仿佛乍富的穷人,几乎每天都有幸福感,说觉得这么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简直是一种罪过。1994年第一批艺术家进村的时候,海波还是吉林艺术学院版画系老师,当时在他眼里,体制外艺术家都是“野战部队”,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却让他十分羡慕,睡懒觉、不上班,想画什么都可以。1995年他冲着自由的生活晃到北京来了,偶尔回长春上课,直到1996年被学院除名,他彻底脱离了体制。海波买下岳敏君的老院子是在2002年,但实际上1997年他就在通州艺术区定居了,只是没有住进宋庄,和几个圆明园出来的画家一起,在通州城里的滨河小区生活了几年。他和老栗的关系,也不像早期那批小堡艺术家那么接近,但老栗在他艺术生活中体现的重要性却有同样的分量。1998年,海波带自己的“合影”作品系列参加了乌里希克设立的“中国当代艺术奖”评选,老栗是评委之一,他不认识海波,但欣赏他的作品,专门写了一篇评论文章。“他太有名了,我以前从未想过要通过什么人去认识他,但老栗的这篇文章,对我在北京能够立足很重要。”一年后,海波去看一个展览,看见老栗,过去表示了谢意。那是他和老栗的第一次正式见面。“我们现在住处相隔不远,也两三个月才见一次面。见面说的话都和艺术无关,聊聊闲书,还有我们俩都喜欢树,聊怎么种树,这是谈论最多的话题。有时我也跟老栗抱怨,村里不如从前安静了,哪里又怎么怎么不好了,他总是安慰我,水至清则无鱼,把门关起来过自己的生活。他真的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理想经常和他背道而驰。” 岳敏君也说,到小堡后,他们和老栗在一起基本不谈艺术话题,“每一个人都自由了,都可以跟着自己的感觉去走,而在谈论它的时候,难免让自己的观点影响到别人”。 海波他们的活动范围都有限,他自己就只和五六个人有联系,“前面来的人大都有名了,很少和后进村的人、低层一点的人交往”。小堡村是个孤寂的地方,他说有时在家待上几天,就一定要找朋友过来聊聊天,成了一种生理需要。有一次他向岳敏君推荐一本书,老岳看了一眼书名,说:这本书再好也和我没关系,我不看。“在小堡村就是这样,每个艺术家只把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做到极致。我个人认为,这里是中国最接近精神自由状态的一个地方,不仅是艺术村落,它还是自由村落,一个能按照自己意愿生活的地方。不管怎么说,感谢小堡村委会为中国自由主义精神的滥觞提供了滋生地。”岳敏君的代表性作品都是在那个老院子里面完成的,1999年他用挣的钱盖了一座新工作室,6亩地,老院子卖给了海波。海波现在也搬出来了,盖了自己新的工作室,老院子免费提供给老栗赞助的那些独立电影人使用,“现在住的是王宏伟,演《小武》那个”。 左邻右舍 农民—村集体—艺术家,这是老栗眼中正常的小堡村社会生态结构。现在村委会给老村子那片地方安了一个时尚的新名词:原生态村庄。其实,就是艺术家和村民曾经混居,不像2000年后被逐渐分隔开了。 住老院子的时候,老栗有4个村民邻居。平时没多少往来,但到了重要的节日,他都会送礼过去,一般是两瓶好酒,五粮液、浏阳河,然后割上10斤肉。村民也会给他家回礼,送点红薯、玉米什么的。老栗觉得住在村里,这是比较好的相处状态。岳敏君也和邻居处得不错。他家左边住了一个老头,一个人。右边是一老太太,需要帮忙的时候,还会主动叫他。住他后面那家是外地人,岳敏君有时会出钱请他们做些零活。只有一家邻居,处事有些霸道,有次在大家都要经过的路上挖一大坑,好些天也不填上。岳敏君选了两条烟送过去,第二天也就填上了。村民有时也会问艺术家,你画能卖多少钱啊?这是他们之间唯一和艺术有关的话题。 农民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比如秋天晒玉米,直接就铺到艺术家的院门口来了,出门一走就摔跤,还不好意思说。艺术家也有让农民烦的“恶习”。负责治安的李学来说村民经常举报他们扰民,夜里弹琴打鼓、跳舞喝酒。岳敏君的老院子2002年8万元卖给了海波,海波重修了房子和围墙,艾未未帮他设计的。“可能是围墙修得太高了,隔壁的村民就不高兴了,老和他别扭。”岳敏君说。村中心那条路,被艺术家们叫做“王府井”,其实也就5米来宽。1995年村委会开始修现在这条大马路,叫“村东规划路”,投入120万元,当时进了村的十几个艺术家,每人都捐了1000元。有个画家开始只捐了300元,李学来给人送回去了,话说得很直接:我们不领你这个情。这个画家后来凑成1000元捐了。17个路灯也是艺术家们捐的,一共2万元,李学来说这件事情之后,“村民觉得艺术家很可爱”。 村里的院子都没有门牌号,信只能送到村委会,然后大喇叭通知去领,“方力钧,挂号信,就这么喊。威尼斯双年展的通知就是这么送到我们手里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