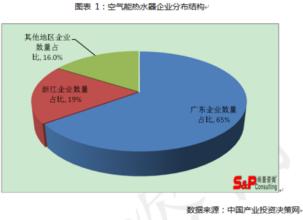◎ 苌苌

黄宇兴最新的一幅画,画一座俯瞰的海岛。淡蓝的海,葱郁的岛,上面的藏文小字写的是周杰伦的歌词:“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了解他生活的人都知道,这是组成他生活的自然而真切的元素:海岛是他对一种根本自由的解释,他喜欢周杰伦的歌,而西藏,早已以很个性的方式融入了他的生命中。在中央美院的第一学期,他和在北大东方学系上学的朋友策划了来年暑假的西藏之行。他们先去了西藏驻京办事处,让传达室的人介绍藏族朋友。好心人把他们打发到西藏中学,在那里,他们被带到学生会,还真交到了同龄的藏族朋友。“我介入西藏的方式比较奇特,从一开始就不是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介入,我从来没在西藏住过旅馆,到了以后就住在不同的同学家里。他们有的是住在拉萨核心城区的贵族后裔,有的住在边远的牧区,我都一一去过。”黄宇兴说。 那次旅行回来,黄宇兴的周末都用在了去黄寺的佛教系高级佛学院学习藏语。毕业那年他去西藏,在活佛朋友介绍下,又在拉萨郊区的寺庙住了两个半月。“ 我第一次去,就被那地方迷住了。烟雾缭绕中,一个女神高高在上,面前有一个大酒缸,好多苍蝇醉死在里面,弥漫着很浓的酒味和燃香的味道。来朝拜的人在外面排成长队,每个人都要把一壶酒倒在那酒缸里,我朋友在一旁给他们敲钟,这种感觉很吸引我。”那是一个供奉扎细拉姆女神的小寺庙,在当地很有影响力,香火极其旺盛,但旅游者知道得很少。 9月的拉萨总下雨。黄宇兴剃着光头,穿着酱紫色袈裟,在拉萨的夜雨中听王菲的歌。他和当时在寺院的24个僧人混得很好,朋友们念经的时候,他在一旁敲法器,或者和寺院周围的乞丐小孩玩儿,他成了孩子王。他很享受隐藏起真实身份的感觉。 2000年,黄宇兴大学毕业了,父母希望他去法国深造。“在他们的想象中,法国就是艺术之都,他们觉得这样的人生很完美。”黄宇兴上小学时就立志当一个画家,仅仅出于无因的反叛,一边学法语的黄宇兴,一边为去印度留学做准备。他写信向印度的使馆、学校要资料,但是发现教学方式不尽理想,后来放弃了,法国也没去。父母婉转表达了他们希望他在体制里安定下来的愿望,给他在美术事业单位找好两份工作,他都没有去。 “我父母没怎么给我就业压力。虽然有时候和他们有冲突,但是他们没真的强加给我什么,只是无形中流露出来他们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乱七八糟折腾了一年,黄宇兴觉得有必要证明可以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生存。2001年,他以个人身份参加董梦阳办的第一届艺术博览会,卖掉了4幅作品,唐人当代艺术中心和香港的一个画廊和他签了展览合同。之前的一年,黄宇兴的毕业创作《视觉与成长》大型绘画获得好几项奖学金,没经历什么坎坷,就走上了职业艺术家之路。现在他是他大学同学房方的星空间画廊的签约画家。 尽管去了藏区多次,西藏题材从来没出现在他的创作中。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黄宇兴和他已经上了民族大学藏文系的朋友们,办了一本杂志叫《白玛草》。 “那种红颜色的、质感茸茸的就是白玛草。白玛草一般被扎得很严实,切成横断面后扎在墙的最上面。”黄宇兴说。他做主编,藏族同学写稿子,讲述他们对藏区的理解。黄宇兴说:“我一直坚持不画任何关于西藏题材的画,我觉得那种风情性的西藏绘画太表面,但我画里的精神,可能来自于我在西藏的观察和思考。它和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改造存在关联。” 西藏经验带给他的是,从此选择相信自己感知到的一切。“春天里,哪一天树开始长芽,开始吐毛毛,然后下雨,这些东西总是特别吸引我,但是身边事情总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我小时候,总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是有灵魂的,是个活着的真实存在,其他人都是没有思想的,陪我玩的。”对33岁的黄宇兴来说,人生仍然是一场充满变量的旅程。成为艺术家后,他没有为卖画发愁过,他的画很快受到一些成年收藏家的追捧,即便所谓金融危机的到来,他仍然像个局外人。 《生物学家的肖像》是一组肖像画,“现在我们很多人意识不到,一个医学家发明的一种药悄无声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史。他们曾经在医学界被认为是疯子,现在也不太被文化领域关注。作为个体的生命历史是那么脆弱和容易被改写,以前,一场感冒可能就要了人的命,人的生命和历史轨迹被各种各样的外力扭来扭去。我就想什么是不变的,可能是血液循环、脑组织的构成,但人的肢体仍在不断衰老下去。它的历史就像一场病,即便你吃了药得救了,但你可能丧失了一部分听力。就是这样一个熵增的过程”。 黄宇兴养冷血动物为宠物。“变色龙只喝活的水,只吃活的昆虫。我给它喂蝈蝈、喂蟋蟀,还得补充维生素。把蟋蟀放在维生素B3粉末里,沾得它身上都是粉,变色龙吃它就能补充维生素了,但是这样变色龙不爱吃。后来就先让蟋蟀吃沾有B3粉末的菜,再把这种富含维生素的蟋蟀喂变色龙。要给变色龙营造70%的湿度,25到28摄氏度的温度,有流动水,有掩体,如果它长期找不到一个地方躲着,精神会相当紧张,这会影响到它的寿命,它必须躲在一个叶子后面才觉得安全。而你能模拟一个亚马孙丛林那样的环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我喜欢原始森林和热带雨林,但它们距离我太远了。你看到一个蜥蜴,脑袋上长着绿色的鬣,它特别强烈地提示你,它来自于南美洲,把你的居住地和它的原生地之间建立一种线索,这种关联让我感觉非常舒适和美好。你只能观察它,不能驾驭它。它们反复告诉你婆罗洲那样一些地方,你会想到它曾经是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树上盘旋着的一条蛇。而你为他制造那样的环境,它并不领你的情。其实冷血动物并不冷血,这也是一个误解,因为都是人们一厢情愿。它的脑容积只有那么一点点,它感受不了更多东西。它给你提出一个个难题,让你去解决它。很多小孩养它们是为了酷,不去学习相应的知识和经验,你卖给他等于这个东西到了死神手里,我们叫他们‘杀手’……”黄宇兴津津有味地讲述着他的宠物。然后又看到那些和想象很不符的晦暗的画面,奇怪出现的冰冷的数字和异域文字,又听说他对冷血动物有特殊感情,但这个鸿沟随着采访渐渐弥合上了。在一切表面的错综陆离的冷色背后,是他这代艺术家对这个世界的情怀。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