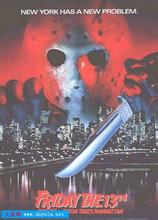系列专题:《零距离认知华尔街: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
美国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一般都属于后勤部门,从事事务性的人员协调和统筹安排,诸如安排去学校招生、安排新人现场面谈、离职人员面谈、背景查询和落实医疗保险、养老金、假期等福利项目,但对人事没有取舍的决策权。人力资源部的一个重要职责是询问新人、旧人一些主管部门难以启齿或有利害冲突的问题,诸如为什么要离开原单位,同主管有什么纠葛等。对新人来说,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前一个工作职位的工资是多少。有了这个数目,公司就有了价格底线,可以做到心中有数,大概花多少价钱可以买断你的劳动力。一般来说,换一个工作,工资有个20%~30%的增长就算相当不错了,算是升级跳槽,会让新雇员工高兴一阵子。除了工资外,人力资源部门还让你填一大堆表格,包括学历、工作经历、有无犯罪记录、有无非法活动,诸如吸毒、赌博。美联储不允许雇员参与任何性质的赌博活动;不能在工作时间喝酒,包括午餐;更不用说其他非法活动。他们做的背景核实(background check)一般都旷日持久,要持续一两个月。经过这样一番清查,想必美联储的工作人员都历史清白,即便无功,但也无过。 我在加拿大做教授的四年期间,前三年的年薪都是52 000加元。因为政府财政赤字要精简支出,所以我们学校实行了三年工资冻结。第四年解冻后,加了1400加元。这些加元折合成美元才40 000多一点。而且,当经济学教授的发展前景也不容乐观,加拿大政府财政亏空,经济学院招生不足,员工能不被精兵简政就已经不错的了。 想必Kevin看了我的工资数目定是觉得惨不忍睹-- 这还不如纽约一个硕士毕业生的起始薪金!难怪我为什么要跳槽了!但其实,我向来对钱不很看重。因为消费水准低,也没有时间吃喝玩乐,所以物质上欲望比较少,经济上盈余也就比较多。再说,我也向来没有觉得缺钱花。求学期间,一直有全额奖学金,除了做点轻描淡写的助教,夏天教点本科生的课,从来不需要外出打工挣钱。出国第一年,便有5000加元结余,是让我感觉最为富有的"万元户"的一段日子,毕竟与当时物质生活一贫如洗的中国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因为工作比较刻苦认真,花很多时间在系里计算机房写文章,算程序(当时个人电脑还不普及,所有学业都在学校里完成)。计算机房对面办公室的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见我精神可嘉,便去一家基金会为我申请到近万元奖学金。这在上学期间算是天文数字,可以维持一年生计。

过了几天,Kevin的工作意向书就寄到了。担任银行检查员(bank examiner),年薪6.5万美元。他同我又做了一番详尽的解释:这份工作按常规有半年试用期(probation period),转正后,有可能会重新考虑报酬待遇。纽约联储没有奖金之类额外收入,但有很好的福利、医疗保险、养老金制度;有非常受人欢迎的弹性星期五制度(flexible Friday),即平时每天多干一小时,每两周的一个星期五便可不用上班;除此之外,每年还有四周休假,几天的事假和病假,等等。另外,为避免有利害冲突的嫌疑,我不能同时在其他金融机构兼有工作或头衔;我如果持有美联储管辖的商业银行的股票,得马上清理掉;但我可以投资共同基金,即便共同基金里含有辖内银行股票也无妨,因为个人对基金的资产选择鲜有控制能力;我可以在这些辖内银行开办普通意义上的支票存款账户,但买房子的抵押贷款不能出自这些银行。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我基本上是马上接受了这份工作,没觉得有什么需要争议要求的,还觉得这些规则条例蛮新奇,从未经历过。比如假期,在大学里是没有固定假期的,时间安排上非常机动。你可以整个暑期、周末都休息,游山玩水,也可以继续做研究、写文章、算程序。对大部分学者来说,尤其是事业刚起步的年青学者来说,更有可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管身在何处,脑子依然像上紧的发条,想问题,做文章。而在商业界,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似乎泾渭分明,周一至周五专注于工作,周末便放松休息,白天上班,晚上下班,脑子就像开关一样,一开一关,张弛有致。总之,我现在就要去适应新的商业运转模式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