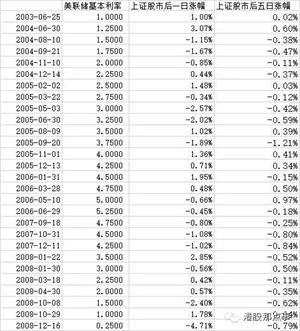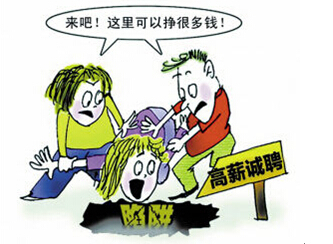央行近日宣布,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上调零点二七个百分点。专家普遍认为,此举大有必要,预计中国年内还将加息一次。据说这是“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中的一部分。央行表示,此举有利于引导企业和金融机构恰当地衡量风险。 其实,仅仅在上个月,就有金融专家明确反对小步快速上调基准利率。即将卸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的余永定在确认“中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投资率过高,经济增长速度偏高,有经济过热迹象”的情况下,更加强调要从经验的角度考察小幅加息对紧缩信贷的效果。 经济过热来自需求膨胀,构成需求的主要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购买需求和来自国外的需求。今年上半年,GDP增长10%,消费增长也就10%,但是投资需求增长达到30%,政府需求增长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但有飙升的税收为支撑,来自国外的需求增长20%以上。特别要注意的是,构成我国投资增长的主体,目前仍然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加息可以提高消费的机会成本,特别是本次加息是存、贷利率同时提高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存款利息上升的确可以提升储蓄的吸引力,但考虑到消费需求的增长并未突破GDP的增长速度,所以加息以抑制消费不应该是本次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

加息可以提高投资成本,加息会降低企业的利润水平和对利润的预期。问题是,目前作为投资主体的国有企业其较高的利润水平主要来自垄断性高,其流动性应该比较充足,对贷款的依赖性不高,对利率影响成本不敏感。而对贷款依赖程度高的是中小型非国有企业,他们所敏感的主要是获得贷款的可能性,而未必是利率水平对利润的压缩。 政府支出有税收支撑,对利率毫不敏感。招商引资是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为此不惜付出甚至越级减免税收和低价供地的代价。其实,自1996年到2004年连续8次下调利率以后,2004年10月首次提高利率水平,本来也是要约束投资的迅猛增长。但是那次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将投资打压下去,与其说是提高利率的结果,莫若说是行政指令发挥了更有效的作用。比如今年内蒙投资猛增,如果不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性指令,光靠利率“小步提升”,能在多大程度上抑制金融风险的作用,值得打个问号。 有人强调提高利率是为了有效打压房产投机形成的泡沫。在目前这几乎相当于无稽之谈。在银行已经形成的3万亿不良贷款中,来自房地产行业的比重非常低。实际上,房地产贷款目前还属于商业银行的优良资产。提高利率仅仅使得“房奴”们负担更重而已。 在我国,真正的金融风险来自银行产权国有,代理人和权力结合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取代了企业的利益最大化。而所产生的不良贷款却有父爱主义不停地买单。连剥离不良贷款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自身又成为新的不良资产。面对这样的机制,加息能减少多少金融风险?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