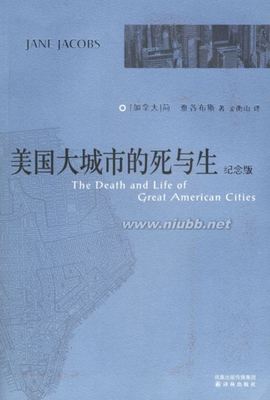同时涉及立法、行政、安全三个部门的重大政治事件,在美国现代史上并不鲜见。以1961年为起点,同一年的“猪湾事件”、1972年的“水门事件”、1986年的“伊朗门”乃至近期沸沸扬扬的斯诺登案都吸引了极大的公众关注。即使是在美苏冷战的高潮阶段,对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是否正当的讨论依然是公共生活中的重要话题。 仔细论之,这四个事件的逻辑并不相同:猪湾事件是中央情报局企图以单一机构的判断僭越外交政策与对外战略,甚至胁迫行政机关而导致的悲剧。水门事件是总统公器私用,以国家安全资源服务于党派利益、并企图欺瞒立法机关收致的教训。 伊朗门代表了行政机关与安全部门勾结、违抗既有法律的越轨。斯诺登泄密事件则显示了新的趋势:政府正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全面入侵私人领域,并把这种入侵变成了可盈利的产业。而美国公众舆论对这四个案例的反应却是如出一辙的—行政机关被置于遭质疑和检讨的位置,法制精神和公开性则一遍又一遍被重复和强调。 这种独特的行事逻辑和心理状态,早在独立战争前就已经扎根在了北美。乘坐“五月花”号前往新英格兰的第一批清教徒把自由的品质和道德感设定为新大陆的立国基础,老欧洲的专制君主、特务机关乃至贵族阶层在这里全无生存的土壤。在这种道德原则之上形成了著名的“美国例外论”,并被托克维尔写入他的巨著《论美国的民主》当中。 对那些真诚相信“美国例外论”的民众来说,新大陆的自由品质是它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国家政治生活需要长期护持的目标。尽管托克维尔曾怀疑美国人爱平等胜过自由,但从《独立宣言》、《反联邦党人文集》到《葛底斯堡演说》,保护公民自由免遭侵害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乃是最重要的话题。 进入新帝国主义时代,伴随国家间冲突的升级,自由之目标与手段间的冲突开始浮现,美国人被迫反复自问:如果自由要靠无孔不入的监控和甄别来捍卫,它是否本身也会发生堕落和变质?冷战期间美国知识界对国家安全活动的批评,就是基于这种恐惧:如果美国被迫采用与它最厌恶的对手全无二致的手段来保卫自身的安全,那么对手也许会被消灭,但美国也会堕落成下一个苏联。自由不仅会被来自外部的敌人摧毁,它在国内遭到弱化和堕落的可能性同样存在,美国公众对权力制衡、监督权和知情权的反复强调,便是基于这一逻辑。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