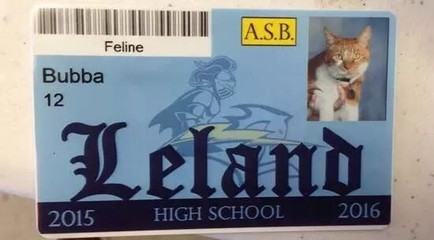1918年秋,鲁迅先生在一篇随感录中谈到自己的大恐惧:“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那是针对“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论而言的。不料这种名目消灭论现在表现为对新的一波移民潮的担忧,即精英外逃说和资产外流论。精英外逃、资产外流,岂非国将不国?所以各项政策还是不能从紧。据说房地产调控的从紧已经使得有些开发商走投无路,所以他们只好“在国外做二等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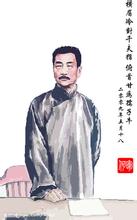
如果说“在国外做二等公民”是大恐惧;那么政策的从紧更是大恐惧。问题在于,哪一种大恐惧在前?如果说“在国外做二等公民”是一种切身的感受,那一定是移民在前,是他们自己申请改变了个人(往往妻、小在先)的“中国人”这名目。只不过政策从紧,他们正好借题发挥罢了。 也就是说,是精英外逃、资产外流导致政策从紧,还是政策从紧导致精英外逃、资产外流,两者绝非像追问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那样扯不清。因为能够伴随着资产外流的外逃的精英们往往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或者是富二代、官二代之类。他们之所以恐惧,是他们先富起来的路径不正当,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一旦政策从紧,他们的先富或者不具有可持续性,或者会露出破绽,所以他们早营造了一条后路,办了绿卡,成了裸官。 其实,他们所感受到的政策从紧,只不过相对于过去鼓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更强调民生一些。当然,他们不会公然反对强调民生的政策从紧,而是在要求另一种放松:提供更优裕的融资、开辟更容易发财的领域、释放出更多的“红利”,以便他们做大做强。总之,政府不要仅仅做“垄断企业的政府”,要做所有先富起来的那些人的政府,不必论先富起来的路径是否正当。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把更多的资金投向国内”,否则就对不起了。这话再明白不过,是在威胁,拿他们的“中国人”这名目进行威胁。 过去,海外游子强调“中国心”;现在,国内的“华人”强调的是“中国人”这名目。历史真是具有三十年三十年河西的反讽意义。然而,既然明白了精英外逃、资产外流在政策从紧之前就已经存在,那么就应当该从紧时就从紧。既然他们没有了“中国心”,要他们“中国人”这名目有何用。至于他们以“在国外做二等公民”的委屈抱怨政策从紧,那是在试图维护他们在国内一等公民的既得利益,是一种忽悠民生的圈套。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靴子至今仍未落地,个中原因,就是太过照顾了既得利益群体一等公民的渗透力。如同鲁迅先生当年所言:“——这便是我的大恐惧”。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