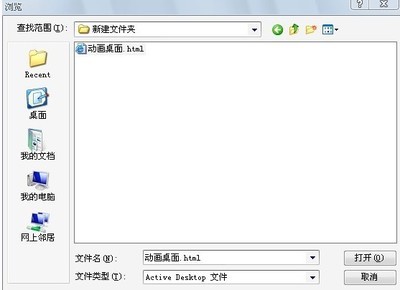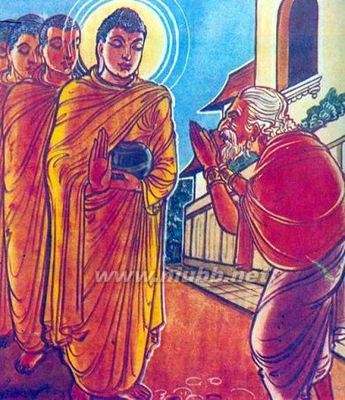京都是千年古都,游京都少不了逛庙,而庙里最可看的是庭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园林。似乎中国园林主要是文人的、世俗的,这一点与西方相近,而日本庭园大都在寺院里,进了门,便置身于宗教。尤其所谓枯山水,那是把从南宋拿来的水墨画加以立体化,好像用笔墨在纸上画不来才想出的法子,也显得简单。水墨画跟禅前后脚传入,禅敷衍在枯山水上,这种庭园更独具了日本特色。面对一片枯山水,即使冥想不出来什么,也仿佛被禅过了一水,莫名其妙,又似有所悟。

说来日本庭园一开始就带有宗教色彩。凡事追本溯源,概念越宽泛,越不着边际,那事物越源远流长,乃至追溯到混沌未开之中。庭园亦如是。若据以史料,不妨抄一段《日本书纪》,本来是汉文:公元612年,“是岁,自百济国有化来者。其面身皆斑白,若有白癞者乎。恶其异于人,欲弃海中岛。然其人曰:若恶臣之斑皮者,白斑牛马不可畜于国中。亦臣有小才,能构山岳之形。其留臣而用,则为国有利,何空之弃海岛耶。于是,听其辞以不弃,仍令构须弥山及吴桥于南庭。”这就是造园之始。既有中国南方的桥,又有佛教的须弥山,兼收并蓄是日本人的天性。甚至可以说,宗教意识更先于审美意识。这种宗教意识基本是佛教的。神道为日本所固有,本来是一种自然信仰,没有偶像,没有殿堂,也就没有庭园。即便崇拜的是山林,用稻草绳之类圈起来当作圣地,也扯不上庭园的概念。受佛教刺激,神道这才有样学样,建神社,塑神像,也有修园子的。神社庭园不可能比寺院庭园更久远。或许也因其缺乏可附会的思想,神社的庭园几乎没什么看头儿。 枯山水庭园独领风骚之前,兴盛的是净土庭园。中国自隋代勃兴阿弥陀信仰,唐初发展为净土宗。7世纪的佛像,阿弥陀远远多过释迦和弥勒。这种信仰传到日本,盛行于8世纪末至12世纪末的平安时代。11世纪末王朝秩序衰败,朝廷政争演进为武力争斗,武士势力进入了政权中心。中央权力分裂,地方闹独立,世道混乱,呈末世之相。佛祖灭于公元前949年,从此正法衰微,分为正法、像法、末法三个时代。正法一千年,像法二千年,日本人掐指一算,1052年正好是末法伊始。推波助澜的是源信,此和尚编撰《往生要集》,教说“欣求净土、厌离秽土”,劝人念佛。口诵阿弥陀,心想佛尊容,临终之际阿弥陀来接引,去他所居的极乐净土,否则下地狱。净土思想对平安王朝的文学、美术等影响甚巨。人是急于行乐的,等不到死后,动手修建世上净土。汉诗文家庆滋保胤与源信有交往,所撰《池亭记》称,他在自家地界“高处构小山,洼处掘小池,池西置小堂,供奉阿弥陀”;“此外,青松岛、白砂汀、红鲤白鹰,小桥小船,平生所好,尽在其中”。这个有阿弥陀堂的庭园是净土式庭园的雏形。平安时代中叶有个叫藤原道长的,先后把三个女儿嫁入天皇家。像当时的贵族一样,他也皈依佛教,把《往生要集》常置座右,晚年修建法成寺。记述道长生涯的史话《荣花物语》中描写那庭园,“七宝桥横于金玉之池,杂宝船游于植木之荫”。道长就死在法成寺的阿弥陀堂,但有否往生西方的极乐净土就不为人知了。京都府宇治市的平等院有一座凤凰堂,它就是阿弥陀堂。11世纪初藤原道长之子赖通用家传别墅改建的,“水石幽奇,风流胜绝”,阿弥陀堂和园池大致完好地保存下来,被刻画在十日元硬币的表面,也列为世界遗产。藤原赖通的次子橘俊纲(给橘姓人家作养子)写了一本《作庭记》,是日本营造庭园的最古老著作。 远离京都的东北地方有一处净土庭园的遗迹。平安时代那里是陆奥国,盛产黄金,繁荣一百年,可能马可?波罗向往的黄金之国就是这陆奥。平泉是它的中心,在岩手县,2011年3月经受东日本大震灾,6月以“表现净土的建筑、庭园及考古学遗迹群”列为世界遗产。中尊寺有一座金色堂,金壁辉煌,是阿弥陀堂。凤凰堂与金色堂并为平安时代净土建筑的双璧。附近又有毛越寺,迦蓝已烧毁无存,但苑池、庭石历经八百余年,依稀可见平安时代净土式庭园的样态。从山林间引水入池,蛇行逶迤,每年5月里新绿怡人,在水边举行仿古活动,曲水流觞。水边列坐古装男女,一觞一咏,咏的是和歌。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