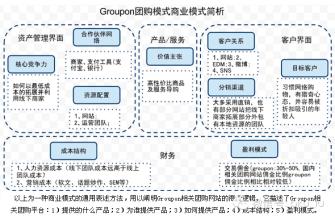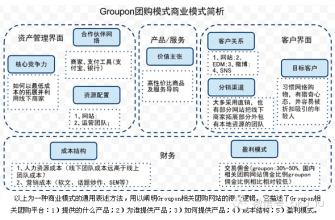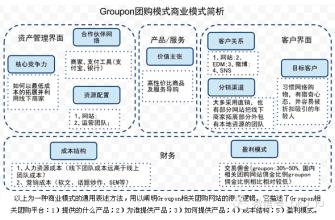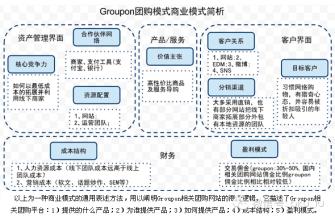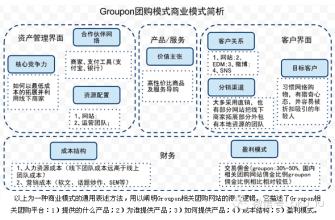不管是市场交易,还是所有权交易,企业家都是为了获取最大化的利润,因此,降低总交易成本是最现实的做法。但是,由于企业涉及多方利益相关者,把所有权配置给哪一方,就成了考验所有权交易结构设计师的最大难题。
一般而言,如果某一方利益相关者承担的市场交易成本最高,同时在企业涉及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当中他们的所有权交易成本又最低,这类利益相关者无疑是最有效率的所有人。用商业模式的框架诠释则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拥有关键资源能力,其中市场交易成本低廉的采取市场购买,市场交易成本过高的则要评估其所有权成本,必要时可以把它设计进所有权交易结构。
所有权涉及控制权和剩余收益索取权,后者只要按照贡献份额按比例分红,分歧就会比较小;前者则需要多方的博弈达成共识,对利益相关者的同质性要求较高,因此一般要求所有权只配置给同一类利益相关者。如上文所示,蒙德拉贡的所有权只配置给雇员,居马的所有权只配置给购买农业机械的农场主。
晋商把财股(管理权、部分剩余收益索取权)牢牢攥在手中,而把身股(经营权、剩余收益索取权)作为激励掌柜和伙计的方式,近年来大受推崇。
从纸面上看,这的确是天衣无缝的所有权交易结构:投资方、管理层和雇员都在为企业的蒸蒸日上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正如前面所言,本质上投资方、管理层和雇员的利益不会是完全一致的,其利益斗争的结果就是不能长久。
(1)东家和掌柜的利益不平衡。实际控制权和一部分剩余收益索取权都配置给了管理层,也就是大掌柜。虽然东家有辞大掌柜的权力,但掌柜已经掌握了全部的生意来往。因此从长期来说,极有可能形成“仆大欺主”的现象。
(2)掌柜和伙计的利益不平衡。同样是身股,掌柜的权力远远大于伙计,虽然说这对伙计是种激励:“做好了你可以上去!”而对掌柜是一种警示:“做不好你要下来!”但实际上,这种制衡把握不好就会变成斗争。虽然不会出现一群叛军出逃,但一两个叛将出逃也足以动其根基。
晋商有一个流传久远的故事。日升昌号的大掌柜雷履泰生病了,东家听从二掌柜毛鸿 的建议让其回家养病,毛鸿 则乘机掌握店号实权。几天后,东家在雷履泰的桌上发现了准备让全国各地分号停业撤回的信件。雷履泰的解释是:字号是你的,但分号是我经营布置的,你要用新人,我只好收回分号,让新人重新安排。东家怎么办?立刻下跪请求雷履泰回到日升昌。雷履泰回号前夜,毛鸿 辞号,到隔壁的蔚泰厚当掌柜,大抢日升昌的生意,形成了票号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联号。其后,雷、毛两人更互相诋毁,甚至以给儿子、孙子起对方名字报复,真叫人扼腕叹息。
(3)身股和财股的风险收益不平衡。掌柜和伙计的身股在盈利的时候可以分红,亏损的时候只是收益降低,仍然有一定的应支银,可谓有收益无风险;掌柜的财股盈利的时候自然可以分更多的红,但是亏损时不但要负担应支银,还无限责任地赔上全部身家,可谓大收益巨风险。
陈其田在《山西票庄考略》里面如此记录:晋商票号兴盛时,“票庄的经理交结官僚,穷奢极侈,以示阔绰”,衰落时,即“卷款潜逃,伪造账目”。待到大势已去“索偿者不得不讼及号东”的时候,这些“平日养尊处优,不问号事,且无一不有鸦片嗜好”的东家,才明白他们原来要承担“无限责任”,“昔以豪富自雄,至是悉遭破产,变卖家产及贵重物件以偿债务。不足,则为阶下囚”。
(4)身股扩大有极限。一开始,身股只有掌柜有,后来扩大到了比较有能力的伙计,最后又衍生出了其他养老分红、故身股(人死后家人仍可分红七八年)等。因此,有分红权的身股不断扩大。一开始,财股比身股多,身股只相当于财股的一半左右,到后来,身股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财股。据历史记载,光绪三十二年(即1906年),协成乾票号1/3的职工有顶身股,其总数量达到财股的130%。1908年,大德通票号身股的数量是财股的120%。僧多粥少,激励作用有限,风险却成倍增加。
山西票号的最终覆灭综合体现了以上的所有弊端。
压倒山西票号的最后一根稻草是银行。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到1911年,我国已经有30家银行。在这两个时间之间,是山西票号的最后一次挣扎,然而,身股财股的制度死结浇灭了最后一点希望的火星。
1904年,李宏龄拟联合各地分号向蔚泰厚的山西总部请命,联合设立股份制银行。当时的清政府已颁布《试办银行章程》,应该说这个建议并非异想天开,若真办成,也许山西票号的历史将会得到重写。但是,决定权不在李宏龄,而在大掌柜毛鸿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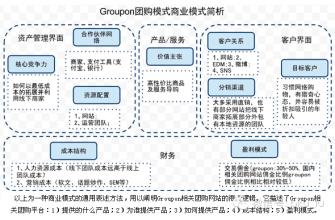
毛鸿翰怕在合组后的银行中自己失势,也对引入外来合作者的股权分散不满,更对推动票号维新的李宏龄心存猜忌。于是,一封回信成了山西票号这个商业王朝的最后一个背影:“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迳束高阁可也。”
后来,李宏龄在《山西票商成败记》中发出感叹:“果天数乎,抑人事乎!”身股财股为晋商带来了辉煌,也导致了晋商的覆灭。不能真正理解所有权交易结构背后的逻辑,“天数乎”?“人事乎”?“愿以质诸世之有识者”!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