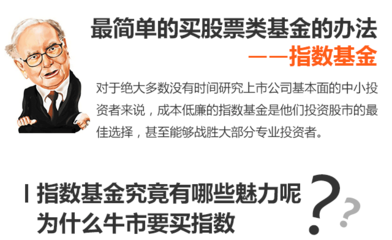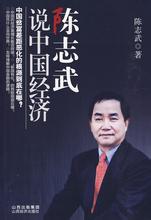2008年12月2日《同舟共进》:在我看来,改革开放的最大变化或者说意义,是自1978年以来,中国民众的财产权和自由权至少得到了部分尊重。有些文章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时,说我们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的条件下启动市场经济改革,是一种成功模式,比苏联更加高明。对此我不敢苟同。首先我们要明白改革路径的选择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效率的选择,而且是涉及非常复杂的政治博弈的决策。中国和苏联面临的具体环境很不一样,但两个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冲破僵化的旧体制的束缚。中国当时的教育水平比不上苏联,但劳动力实在太充沛了,这是有利条件,可以在国内体制不做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先把外资吸引进来,拿外国人的钱和技术帮中国人发财。当国内经济发育起来,社会呼声强烈,保守力量也衰落后,再搞政治体制改革水到渠成——这是那一代领导人中的英明者的设想,应该说是很有政治智慧的。苏联当时无法这样做,他们劳动力稀缺,除了出卖自然资源很难吸引外资,且那时苏联人均GDP已达到8000美元,门槛相当高,靠开放来推动改革没有可能,所以只能走改革这条路。 但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利好几乎已充分释放,下一阶段要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更深入地推进改革开放。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结构性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政府的征税能力过于强大,对于经济资源的垄断过于强势,造成人民的消费能力受到抑制。产业发展严重畸形,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占有大量国家资源和国有银行贷款,又在证券市场圈钱,管理效率却极其低下——这些都是损害中国人民福利并会抑制经济长远发展的。可以说,中国已再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能否闯过这个关口,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这些年政府税收增长了那么多,而老百姓收入的增速远低于GDP,让民间消费怎么也上不来。国内的老百姓没钱增加消费,那么,这么多的工业产能给谁生产、东西有谁买?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政府投资是否过头的办法,就是看政府的奢侈大楼、形象工程是否越来越多。80年代,没有几个地方政府盖奢侈大楼,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近几年则到处都是,这说明,不能由政府继续掌握那么多投资的钱了,是扭转“国富民穷”局面的时候了。 aihuau.com因为,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把资源用在“生产建设”和“基础建设”上,这次经济刺激方案还是以投资为重点,主要是政策惯性,必须掌握靠刺激消费带动增长的调控手段。中国经济改革未来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我认为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第一,国有资产和国有土地应该私有化,否则,中国的内需难以上升、产业结构难以“软化”。道理很简单,如果中国的资产性财富76%继续掌握在国家手里,一方面老百姓无法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资产升值好处;另一方面,这些资产由官员配置的结果是必然偏重形象工程、“重化工业”工程,只会继续偏重高资源消耗、高能耗的工业,而忽视第三产业。第二,在法治方面必须有实质性的进展。因为契约经济、金融经济对法治的要求高。 如果这些改革不到位或者说改革的方向出现问题的话,中国经济是否将会面临发展困难甚至出现危机,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一、如果契约经济难以发展,产业结构转型就难以实现。二、商品出口市场会越来越难以扩大,外贸增长空间会越来越小,这使得中国难以继续靠制造业和其他工业来发展。其他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今后会愈演愈烈,类似西班牙烧鞋、美国反毒玩具和日本反毒饺子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出口依赖型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第三,正因为国内的金融行业还欠发达,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被卡得很紧,这就导致大量热钱以各种方式进入中国。因人民币升值太慢而引发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等问题,实际上是两种因素间的矛盾所致,一方面,中国经济因需求原因已越来越契约化、金融化,另一方面,整个制度架构和监管架构又没跟上,这两方面间矛盾的结果是使许多政策左右为难、寸步难行。到最后,通货膨胀、资产泡沫破裂只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