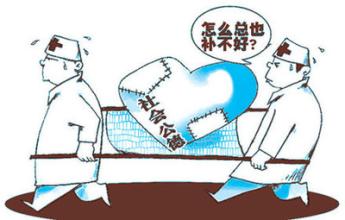在最近的经济学研究案例中,“郎顾公案”牵扯了国内全部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士,不论你是否情愿,主动或被动你都将被拉入某个阵营,被贴上或左或右或其他什么派别的标签。

这个公案及其引起的国内经济学界广泛的“失语”或“失态”,核心在公案所指涉及我国国有资产及国有企业改革命运这一重大命题,与此相关的种种讨论行将上升为立场路线的是是非非,但随着网络传播的扩大化及情势的变迁,焦点正逐步远离国有企业改革与否及如何改革的主题,大部分争论已转变成为经济学研究领域内争夺国有企业改革话语权的无形之战。 经济学研究成果及经济改革方案(措施)或多或少地在影响着政府职能部门的决策。这种公共权力对理论成果的推行比市场施行要强大和迅捷许多,比如证券市场改革、投资领域开放,中小企业融资、社会信用体系等市场经济现象的改革和实行方案都是如此。通常正是由于那些拥有强势话语权的类官僚经济学研究人士的市场推论研究和官学结合所致,使得一些自由市场研究的观点很容易会被淹没。我国的经济学研究的文论渊源一是西方成熟的自由经济理论和经济体系,一是国有经济理论和公有制经济改革趋势;或者是两种理论的拼盘。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经十数年的经济学研究,其中强势话语权带来给政府信息资讯的不对称(主要症像为决策层取得信息误导;市场环境对公共权力的盲从),造成这部份理论中许多已为大众熟知的事实和理论体系就成为其当然的创造。这种影响决策的经济学理论是否导致社会和资源的损失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缺失,或许需要由时间和历史来检讨。 但事实已经是,这种官学结合的经济理论一旦依傍上政府权力并成为公共利益代表而得以实施,就会成为本该高度自由和开放的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主宰势力。此时,这种经济学研究的强势话语权实际上已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暴力。 经济学者必须具有独立性。不论研究者理论研究的方向和方案的对与错,只有拥有独立人格的经济学者才真正有资格担当经济领域发展的“社会良心”。在“郎顾公案”的争辩中至今没有建立基于客观事实(而非各位学者主张的事实)和科学理论(而非各们学者的结论)的研究过程让公众明白坚持国有企业改革没有或不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经济学者必须有公平性。经济学者获得大众的信任与尊重正是其经济研究的方法与结果具有不同于追逐利益的学术上的公正与公平,而经济学研究形成官学、商学结合,势必丧失学术基本的信用价值。 经济学者必须有宽容性。市场经济的复杂性,要求经济学者能从中寻找、发现并接受那些哪怕与自己观点相反却是市场经济真正动力的事件,否则这种经济研究最终仍将会被市场遗弃。 公众欢迎的经济学研究不是一家专有的理论话语权,公众需要的是开放的多层次的市场经济研究指出市场经济不同的可能的发展方向。因为对公众而言,选择越多,机会越多。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