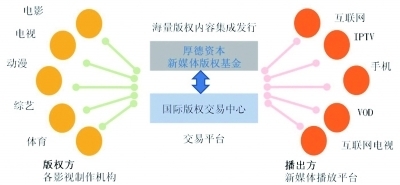本文虽然写于前年,但所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今天再发表,以作为《CCSTT》一文的补充。
中国智库之现状
原题为《关于中国智库现状之我见》,2006年8月21日

玉福兄:
与完成上述课题相关的是另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是能够进入上述课题(超个人功利的)者的组织形式和团队效率问题,即所谓“智库”(NGO)问题。说到智库,其实我是深有体会的。早在1984年7月,因我写了篇《关于理论思维的内部机制》,有幸入选并应邀出席钱学森先生发起的“第一届全国思维科学研讨会”(钱先生当时与于光远先生就思维科学与灵学问题争吵得很激烈)期间,到会的一批青年学者(多数是搞理、工、医、IT、哲学的),由于对会议组织安排和对问题的意识形态性争执多于思维科学本身的建设性那样的会场氛围不满,而自动聚集在一起发起组织一个名叫“中国青年思维科学院”,由于我的发言得到大家认同,我也被戏称为“我们的钱老”,还被推举为“中国青年思维科学院临时院长”,后来我们准备办一份期刊叫《科学中国人》(刊名由五四运动名宿、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许德衍先生亲笔题签)。当然,那时的政策没有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提供这种生存空间(甚至钱学森先生还亲笔给我写信,明确表示不能支持这件事),结果,我那一批朋友除了我全部陆续出了国而至今无一人回来,1988年底在黄浦江畔握别最后一位去美国加州大学的朋友后,渐渐联系也少而至无——在此顺便借贵报一隅,让我再次祝他们平安、好运和幸福!我想,那应是我和朋友们在这方面的最早的一次努力吧。我知道,即使是今天,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仍然是解决不了的(加上不具备权、钱、社会知名度这些必备外在条件)。但我知道玉福兄比较关心中国这方面的情况,就顺便在此报告一下有关“中国智库”的现状及我的看法。
记得2003年我们(你、我还有齐鲁兄)刚认识的时候,我们曾热烈地讨论过是否也要成立一家为中央政策决策服务的民间智库(Think Tank NGO)的问题,我还为此起草了一份《中国经济社会十大战略课题刍议》。那时,我只知道北京有个“天则经济研究所”,直到最近,有朋友给我推荐了“北京大军经济研究中心”,又看了一些专题调研报告,原来中国智库有2500个之多,研究人员3.5万人,属于民办性质的不到5%。最大的天则研究所专职人员不到20人,2003年运营费用200万人民币。这与你曾提到的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专职研究人员有400多人、年运营资金15亿美元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不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提醒,实际上政府对民间智库的需求其实非常强烈,“一方面从今年开始,其实从去年开始,对于社会团体,或者说对于思想的管制在趋紧,这就使得我们思想的自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另一方面,党中央、政府又在积极的寻求社会的声音。”现在的改革改到了政府头上,看来,政府确实需要购买NGO的服务。
只是中国Think Tank NGO自身的发展还存在比较大的问题,除了政府严格限制登记注册及其活动外,我看还存在着以下问题:
第一,是在建立与政府的和解信任关系,以及远近距离度的把握上,还有太多问题(这本身也是提出“和解哲学”必要性的一个方面)。
第二,是组织松散力量分散,各说各话,没有统一而明确的“议案”、“提案”方向和系统的研究计划,大家莫衷一是,比较自由,但效率不足,效果不佳。
第三,是不管国家机构抑或仅有的几家民间机构,组织者都是一种“篮里挑瓜”(非大田挑瓜)的办法,即基本上只把眼睛盯在不同领域已经成名的人士身上,须知,这些人士如果有好的建设性突破性的IDEA或议案、提案、规划、设计,一般来说“上达天听”的通道还是比较方便,用不着以民间方式出现,这些人当然比较可靠(不是指政治上),但创新不够——把中国刚刚发布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与《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两部集中了中国官方机构成名人士智慧的“十一五规划”作一比较,很明显,在主导思想、规划分类、各学科重点研究方向和重点研究课题等等方面,前者较后者不但平庸而逊色,而且毫无创见(尽管前者也提到了要在七个方面“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这样的语汇),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把“自主创新”作为工作指导方针的“首要方针”的提法只会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第四,是作为一个机构本身需要生存,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像中国的大部分研究者需要靠研究本身获得生存资料(职称、职务、房子、车子、“博导”、“特殊津贴者”及各种报告费、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样的“出场费”等等)一样,这就带来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即难以真正超脱地、独立自主地面对“真问题”、“硬问题”(现在都唱“老鼠爱大米”,“真问题”、“假问题”可能往往与“大米”无缘,甚至会导致丢失“大米”!),而“假问题”、“软问题”则又往往可以哗众取宠于一时,由此,轻取名利,在这种环境氛围下,中国学者往往容易把正常的学术观点之争变成实际利益摩擦,弄得大家火气很大甚至不共戴天(这也是过去长期奉行“斗争哲学”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有时,争论各方与政客无异,让人简直难以把“学养”两字与之挂钩。可以想象,在一个应当“讲理的世界”里“不讲理”会是一种什么结果?而这是中国的“学界”的通病。
第五,是中国式学者的思维方式,知识有余,思想不足,专长有余,通晓不够,思维守成,尤其是理论思维能力比较欠缺(这也是中国长期自用前苏联的“专才教育”制度的和“独尊一统”传统的一种后果)而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状态,专才教育下的学者,他们可以搞“工程”,却很少有“创意”。
第六,是研究者往往缺乏现实历练,其所关注的问题与现实严重脱节,与人合作的协调性也比较差,团队精神不足,人人都是自己象牙塔里的大王。
因此,我以为,中国智库欠发展的问题,主要原因不在政府,而在“中国智库”自身!当然,还有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中国的职称、职务晋升评价制度以及相关的学术媒体运行机制和选文标准都存在着很大问题——中国的一切人、事、物选择标准都趋于取平均值。但这终归是外在因素,作为从事精神生产者或忠于良知的知识分子,理应超越、超脱一些。
鉴于上述情况,我宁可自己独立思考与少数朋友一道去完成一些我自己认为有价值的课题。但我相信中国的智库在未来一定会有长足发展。
枭阳子2006年8月21日凌晨于上海开关居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