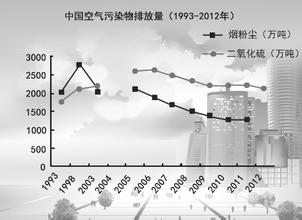你设想过60岁退休那天,牵手你的另一半进行一次犒劳人生的旅行吗?
旅途或近或远,或朴素或奢华,对于彼时已经失去工作能力(机会)的人来说,答案很大程度上将仰仗于你积累的财富。
一段体面而有尊严的晚年生活,谁来为它买单?你所服务过的企业,你置身的社会,你的家人,抑或自己?
这道熟悉又陌生的选择题,每天都在有形或无形地牵绊着都市里的茫茫众生,牵动着你的职业选择、进修计划,甚至是生儿育女的时间节点。
房子、车子、位子、票子……“茫一代”就像过冬前的松鼠,拼命储存过冬时的粮食,却是存多少都觉得不够。
他们的潜意识里有着深深的隐忧:失去了挣钱的能力就几乎失去了一切。
谁,拿什么,来保障这一代人的未来?
一段体面而有尊严的晚年生活,谁来为它买单?你所服务过的企业,你置身的社会,你的家人,抑或自己?房子、车子、位子、票子……“茫一代”就像过冬前的松鼠,拼命储存过冬时的粮食,却是存多少都觉得不够。
对于“茫一代”,未来生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仰仗于积累的财富。
我把青春献给了你
企业不能承受“终身雇佣”之重
三万块钱的解雇赔偿金拿在手里,36岁的沈丽愣在了原地。
这个她工作了十年,自以为可以养老的大公司,把自己解雇了,就在她期望着可以像前辈一样签订无限期劳动合同的当口。
公司内和沈丽同期的同事还有十多位,最后只有三位获得了无限期劳动合同的“尚方宝剑”。
这是发生在2008年时的职业变故。这一年也是新劳动法实施元年,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企业不签劳动合同须支付劳动者双倍工资等内容都写入了劳动合同法。
当时沈丽是那家大型快餐连锁企业东北区域公司的品牌推广经理,她觉得自己所在的公司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她希望能按部就班地工作直至退休,她不愿意把自己置身于随时动荡的状态下。
那次解雇几乎改变了沈丽之后的工作轨迹。这期间,性格求稳的她也试着应聘过两三次,但都无果而终。现在她已经40岁,是一个一岁大孩子的妈妈。
虽然家庭状况不错,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老公在一家大型IT经销公司做销售,不需要为生存担忧,但是沈丽很迷茫,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
让珠珠头疼的,同样是几个四十岁上下的朋友兼同事。之前她一直倾向于招聘“有经验的、不用从头培训的,在这个行业里职位不低、具有一定管理水平”的员工,这样的人基本上都是33~45岁之间。而现在她的想法是“把这样的人开掉”。
珠珠在一家美国广告公司在华子公司做销售主管,虽然硬性的销售额指标给她很大压力,感觉自己就“和出租车司机一样”,每天都至少要有多少收入进账,必须“像动物一样出去找目标”,但这在她看来都不是压力最大的,让她特别累心的是人才问题。
“33岁之前的人虽然对钱看得很重,但是这一代人接受、掌握新事物的能力比年龄大的、有丰富经验的人要强很多。”珠珠越来越喜欢重用年轻人,还在于这个“非常聪明,不保守”的人群,一旦遇到好的向心力,会爆发比前辈要“高出好几倍”的作用。相反,年龄偏大、从业和管理经验都相对丰富的“前辈”们,不仅掌握新事物可能要慢一些、保守一些,另外就是家庭的拖累太严重了。
“对我来说,可能他做不了的工作,就得让其他人额外付出时间去帮他做,但他却拿着高额的薪水,这不仅没有相应地控制成本,反而有更多的额外付出。”
是用刚毕业三年的年轻人,还是工作15年但是结婚有孩子、上有老下有小的“顶梁柱”?多数企业在实际操作中选择了向前者倾斜:工作经验3~10年,这个阶段可能是员工产出最高的时候,这对企业来说无疑是“最优的选择”。
终身雇佣制,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更多时候是“水中月镜中花”。
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昔日女首富、全国政协委员张茵公开主张,向全国政协建议取消“签订无限期合同”,称“大锅饭劳动条例要不得”,她认为,劳动合同法最该做的,是怎么样让人才流动,因为有流动才有竞争,有竞争才有发展。
2008年1月1日起,历经四次审议的劳动合同法正式开始施行。新法新举措被舆论解读为,企业将不能只用员工的“青春期”。
在新劳动法实施之际,台商投资企业富士康科技集团宣布积极执行《劳动合同法》,与数万名已连续工作8年以上的员工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其余员工将以签订长期劳动合同为主,高调表示要做“好孩子”。
与此同时,包括华为在内的众多企业则上演了一出“劝辞”大戏,比如深圳华为公司在2007年年底前后,组织共计7000多名工作满8年的老员工相继向公司提交请辞自愿离职,辞职员工随后即可以竞聘上岗,职位和待遇基本不变,惟一的变化就是再次签署的劳动合同和工龄。此举被媒体解读为规避新劳动合同法而为之。
“我是一个有良心、有责任感的企业家,我的2000个员工都是工作20年了,薪水也都高高的,但是我的竞争对手招了2000个人都是二十五六岁的,成本也低,反而效率、竞争力比我高很多。最后我的企业倒闭了,我还怎么终身雇佣呢?”科锐国际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业务总监刘峰这样反问记者。
在他看来,企业就像一棵大树,活着的时候才能制造氧气、制造树荫,终身雇佣制有时候对快速发展中的企业来说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背了大量的包袱”。
刘峰的观点是中国企业界对“终身雇佣制”比较主流的看法,担心这将使企业支付更高成本或限制其用工“灵活度”。
“我们过去按照西方公司制的做法把员工的福利降到最低,然后都推向社会,实际上造成了各种对立,本来企业是一个稳定器,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如果承担了社会重任,它就是一个小社会。”
高速路上成功换轮胎
一纸保单何以保障后半生?
文敏今年40岁,仅她自己一年用于各类保险的费用支出就小十万元,连她的闺蜜都感叹“买得猛”。
大病、养老、医疗、投资分红等,做过行政副总的她,给自己规划了一份严谨周密的商业保险保障计划。即便手里握着年支出十万元的各类保单,文敏仍旧没有十足的安全感。
在外人看来,文敏和她老公都应该是衣食无忧的那类人。
老公在银行工作20年,是国内某大型商业银行旗下支行的副行长,在朋友看来,文敏老公的工作“特别轻松,特别自由,早上不用按点上班,下午4点多钟就下班,然后就跟朋友去喝酒,一点压力都没有”。
文敏会计出身,三十出头时做到一家物流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后来经朋友介绍在一家大型家居公司担任副总,主管人事、行政和财务,现在是在朋友开的公司做财务总监,月薪8000块钱。
起初文敏出于“以家庭为主”的考虑,想找个薪水差不多的工作就行。一段时间后,看着自己周围那些不如她的人月薪全都一万二、一万五,文敏心里又不平衡了。现在除了财务总监的正业外,文敏还做了三份兼职,月薪2000~5000元不等。现在虽然薪水加起来不少,但是文敏又开始抱怨工作太累。
与很多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同龄人一样,购置房产成为文敏他们为财富保值增值的重要手段。文敏和老公一共有三处房产,一个房贷3000多块,一个2000多块,一处自住、一处是为了升值出售购置的,另外一处以租还贷。

文敏还是最早一批做股票的“老股民”,只是现在“被套住”的股票居多。
文敏和她的老公特别害怕的是,哪天文敏不工作了。有两三个月里,文敏辞职后想调整休息一段时间,当时她老公特别担心,又不敢跟文敏直说,直到文敏重新上班时,老公掩饰不住高兴地跟朋友说,“我老婆又有工作了”。
为替自己的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早作打算,未雨绸缪,买保险、投资理财、购置房产等方式,成为文敏这个年龄段的人来给未来保险的主要方式。
有保险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35~49岁的人群最爱买保险。上有老下有小,还要供房供车,供养子女上学,为父母提供医药费补贴,这个人群的生活压力主要集中在未来十年至二十年。意外险、重大疾病险、定期寿险、养老保险、教育金保障、终身保险等险种,成为他们比较热衷的保险品。
过去十年,亦是中国保险业高速增长的十年,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7.3%,成为作为全球保险业增长最快的市场。
尴尬的是,中国保险业“跑马圈地”粗放发展的十年,以赢利为目的的林林种种的商业性保险产品,并不能给投保人群以百分百的安全感。在坊间,保险业更被列入十大消费投诉排行榜的“黑名单”。
有十余年人力资源管理经验的公司高管这样分享自己的体会:保险公司的理财产品不能碰;养老保险现在行业内公认不划算;大病保险第一次发病后赔完了,合同就结束了,如若再复发,已经是“高危人群”,想再买保险就很难了。
买保险、投资理财、购置房产,成为“茫一代”保障未来的主要方式。
“家文化”是药方还是负累?
觅寻安放幸福的桃花源
“高铁、动车让城市间的距离拉近了,可是我觉得高速发展的城市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疏远了。尽管身处闹市,我还是会觉得很孤独,缺少幸福感。”网民高昂Helena在微博上这样写道。
对中国经济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增长,海外经济学家们总是不吝用“奇迹”这个词。在讲求速度、绩效导向的社会价值体系里,“高速度、高成长、高积累”已成为当下人奉行的准则。
经济的高速发展原本应该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福祉,如今却正在挤压人们的生活空间。有研究显示,中国当代人的幸福感呈U形,20岁出头和老年时期幸福感最强,中间年龄段的感觉最糟糕。
2010年,“幸福”二字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随后,“提升幸福感”逐渐取代GDP成为各级政府反复强调的热词。
到底什么是幸福?什么会影响我们的幸福感?幸福在哪里?
资深产业经济学家白益民在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三井物产”工作了12年。离开三井物产后,白益民陆续出版了《三井帝国启示录》、《三井帝国在行动》、《瞄准日本财团》等一系列研究日本综合商社和财团组织、文化和历史的著作,后来创立了“白益民产业经济研究所”,并一直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经济学理事。
他深入研究了二战后至今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一直很推崇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三大神器”: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以及企业工会。
日本把人力视作资本而非成本,这与“美国经济模式”是截然不同的。日本企业会给员工投入,给你机会,对你进行培养。
白益民当时所在的三井物产中国公司里面,100多名员工里有30多名日本人,他们中绝大多数来中国时一句中文都不会讲,这些人先被派到语言学院学习半年,然后在北京的办公室跟着中国员工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年,都会说了以后再跟着做两三年业务,这样下来,“中国的法律法规、业务环境、人脉都熟悉,变成一个小中国通”。
即使出现经济大萧条,日本企业的主要做法也是普遍降薪,而非裁人。即使裁人,要么是提前退休,补偿员工一笔丰厚的提前退休金,要么将员工转移到关联企业进行分流。
在日本,终身雇佣制并不是法律制度,也不是公司规定,而是在实践中约定俗成的。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日企的终身雇佣制出现了一些变化,通过外派公司给企业介绍临时工,出现了人才市场。不过,白益民介绍,这种方式最多占到日企用工的30%。
日本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工会”和欧美的也不一样。欧美的企业工会和老板之间是对立关系,但在日本,企业工会的人甚至就是老板。“在美国,你要问这个企业属于谁,他一定回答属于股东。但在日本,回答一定是属于员工的。”
白益民解释,日本企业既不是私有企业,也不是政府出资的,而是民间资本股东在扩大过程中通过交叉持股形成的,某种程度上是社会持有,白益民把它定义为集体所有。企业的社长、老板都是从大学毕业生做起,一级一级按照年功序列制做到公司的最高层级,而且老板和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就几倍,不像美国公司的CEO差了几十倍、几百倍。
在白益民看来,日本社会经济这种趋于稳定的结构更适合人才的沉淀、技术的集成,这种稳定结构“可能造成日本在发明上的确不如美国,但是在技术集成、技术应用上要强于美国”。
日本社会经济体系的一些架构特点,是否适合中国?白益民认为,问题不在于可不可借鉴,而在于中国需不需要。
有很多人曾经问过白益民,在日企工作累不累。“一点儿也不感觉累”的他,后来反复琢磨,悟出来中国人所谓的累是“心累”、“不安全感”。“恨不得把下辈子的钱都挣出来,就怕后头没人养。但是在日本企业就没这个感觉。”日企员工加班是家常便饭,但他们却是一种“非常愉悦的感觉,为集体做贡献,不感觉心累”。
在白益民看来,一个体系的幸福指数其实取决于对国民或员工起到的安全感。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日本,企业担当社会责任,企业就是社会,就是家庭。“我们过去按照西方公司制的做法把员工的福利降到最低,然后都推向社会,实际上造成了各种对立,本来企业是一个稳定器,特别是大型企业集团,如果承担了社会重任,它就是一个小社会。”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