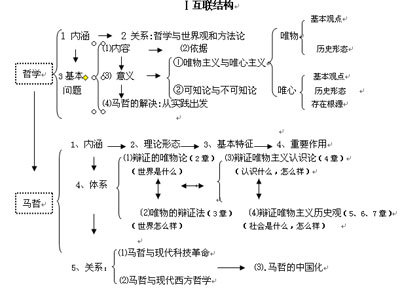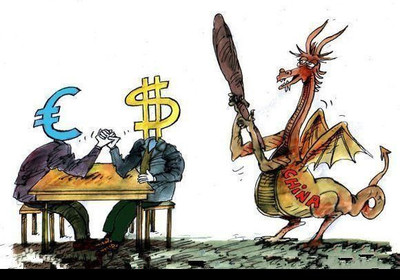西方哲学无疑是以启蒙运动作为分水岭的,启蒙之前,上帝是至高无上的,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上帝,启蒙的现代主义推翻了基督教的上帝,把人构造为至高无上的主体,这种主体是实现启蒙伟大理想(获得永恒真理和达到普遍的人类解放)的保证。启蒙之后,用尼采的话说:上帝死了,人自立为王,成为历史的主体和客体。作为历史的主体,人是立法者,并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起正义的制度;作为历史的客体,人是服从法律的公民,并自愿地遵守法律。在启蒙哲学中,人既是历史的主体又是历史的客体,这意味着立法者的意志和公民的意志永远是一致的,而这种一致是正义制度最可靠的保证。
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主义都是启蒙的产物,现代社会的整个形象都是由启蒙塑造的。但是,现代化创造了空前繁荣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起了人们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后现代主义就是对现代主义思想的批判、抗议和反叛,其批判的核心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后现代主义终结了现代主义关于人的“神话”,用福柯的思想来描述后现代主义的实质就是:作为主体的人死了!
后现代主义在管理领域的作用是“消解、破坏和批判现代管理思想,尤其是科学主义模式的思想和方法。主要表现为对管理的理性主义和管理的普遍主义的否定,反对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和方式来阐释和衡量现实世界,在方法论上反对管理学研究的独断论和实证技术方法的霸权。”
但是,“后现代主义消解主体之后,任何标准都没有了,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由此必然陷入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是一种关于知识(真理)的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关于实践(解放)的相对主义。”(姚大志,2000)具体到管理领域的表现就是,“他们各自从不同方面对管理启蒙以来的管理理性主义传统提出了不同性质的问题,有些是建设性的,有些是挑战性的、解构性的和颠覆性的,但是其中没有任何一位管理学家把自己的理论视为彻底瓦解这一传统的‘思想武器’,也从未声称能够全面取代管理理性主义在组织及其管理等各个方面的实践。”(罗珉,2006)
实际上,主体与其说是被后现代主义“杀死”的,还不如说是现代主义“自杀”的。因为在启蒙哲学家那里,从笛卡儿到康德,都视主体自我为思维的前提,在他们看来,主体自我没有一个生成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不能追问其根由的绝对实体,其结果是,一方面使主体自我永无可能走出自身以达外部事物和“他人”,从而无法摆脱不可知论和唯我论的结局;另一方面也使原本能动自由的主体性成为一套固定不变的先验框架。

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将主体“解救”出来,从科学的实践观来看,主体和主体性是在实践中生成并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中不断进化发展着的。“主体”首先是一个对象性范畴,只有在对象性关系中才能获得自己的规定,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没有客体也就无所谓主体,反之亦然。因此,对象性意识的确立恰恰是主体意识和主体性生存的先决条件,或者说,人对外部世界的发现和意识乃是人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意识的前提条件。对象这一“非我”的确立,使“自我”(主体)与对象之间的界限得以显现,“自我”(主体)由先前自我中心化时期那种绝对的、无限的规定,转化为相对的(与客体相对)、有限的(受客体制约)规定。这样,与对象既相区别和对立,又相互规定和依存的主体及其特性才得以发生和显现。(王义军,2002)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前面一系列抽象的概念。比如一个成年男子可以被称为“人”,但是他如果希望进入“夫妻关系”中取得“丈夫”这样一个主体地位的话,那么“妻子”的存在就是他成为“丈夫”的先决条件,没有“妻子”这个对象,即使他本事再大也成为不了“丈夫”。而且,成为“丈夫”的现实是经历找对象、谈恋爱、结婚这样一个过程才“演化生成”的,而不是“先天给定”的。同时,在做“丈夫”的过程中,既可以充分发挥丈夫的“主体性”,争取丈夫的权利,但是也要充分尊重妻子的“客体性”,尽到做丈夫的责任和义务,并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使主客体之间(夫妻关系)达到最大程度的统一,否则有可能失去做丈夫的主体资格。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