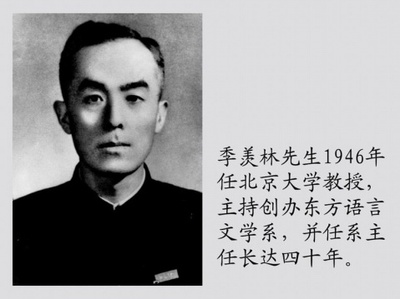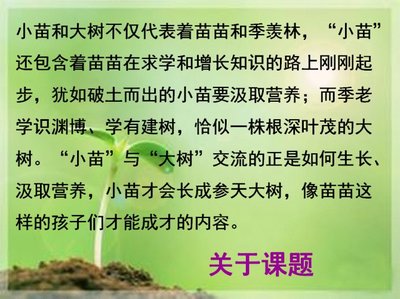转折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交战各国给杜邦的火药订单是惊人的,企业出现了膨胀,短短的三四年时间,杜邦公司员工从五千多人增加到八万多人,产量增加了五十多倍。在这个过程中,皮埃尔·杜邦,居安思危,他给堂兄写信,说这个仗不可能永远打下去,这绝对不是一个好事,虽然赚了很多钱。他最在乎的已经不是赚钱了,他担心杜邦这个家族事业能不能延续。然后想了许多未雨绸缪的办法,也派了很多的研究人员。同时他找了各个部门的负责人,这些人干久了,习惯于遵循常规,想不出来什么办法。后来决定要找新业务,通过兼并,介入了化工业,介入了和火药相关的一些化学原料的生产。多元化了,可是公司的利润表现越来越差。在战争结束以后,杜邦满足了现有人员都有活干的基本要求,有新的事情做,但是盈利降到最低,甚至亏损。他们不明白怎么回事,有人认为领导不懂这些新企业,只会生产火药。有人说生产和销售是割裂的。后来有几个年轻人通过研究认为症结出现在组织结构形式上,必须变革。提出报告后,当时的老板伊雷内(皮埃尔的亲弟弟)否决了提案,皮埃尔也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当时的企业管理模式没有错,中央集权没有错。但是底下人不这样看,他们觉得信息传递不到位,责任不清晰是最大的问题。
于是,各职能单位私下里就组织了一些跨部门的研讨会,信息沟通的问题得到初步解决。最终的经营绩效还是不行。这个时候,杜邦总裁就痛下决心,他终于意识到问题就出在组织上,于是就干脆按照产品分成很多个事业部,这些事业部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等于把原来总部的那些职能部门分别复制到事业部中,就像一个完整的企业,而不是一个部门。原来总部中的那些职能部门全成了参谋,而且只管宏观的,因为企业太大了,必须要考虑宏观的问题。实际上,他们是在整个企业的结构上做了变化。战略决定结构中的“结构” 应该是指组织结构的形式。 王吉鹏: 慕先生认为这里的结构是指采取的组织结构形式,例如事业部制或矩阵制等等的这样一个结构。这让我的观点更加清晰,我今天谈的“结构”不是组织结构的概念,而是可以分为两层:一是产业结构,二是组织形式。战略决定了产业结构,产业结构通过组织形式来实现产业设想,因此今天所说的结构决定战略主要是在产业结构这块。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业已形成的产业布局就决定了战略,组织形式对战略只是影响和制约,它的决定作用是很小的。以上讨论是放在一个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里,是结构决定战略。那么对于一个单一业务的企业会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用价值链的观点去讨论。对于一个单一业务的企业来说,做战略要进行价值链的攫取,即在价值链上企业选择做哪些环节,不做哪些环节,这里结构决定战略也存在。例如仁达方略是做管理咨询的公司,我的战略是要么选择自己做研发,要么购买人家的方法论,我们只做咨询,两者不同。现实情况是,我们现在已经在研发投入了很多,同时拥有很强的咨询能力,假定我现在开始做发展战略,只截取价值链的终端,就做咨询,不做研发了,要切掉研发这块。能行吗?很少有这样的企业。比如我聘任总经理来,肯定是要结合我的研发能力和咨询能力来做战略的,这就是结构决定了战略。
这几个核心观点说清楚就是,结构是两层,对多元化企业适用,对单一业务的企业同样适用,只不过运用的方法论不一样。一个从是产业布局和产业集群的角度考虑,另一个是从价值链的角度考虑,核心观点就是这个。 总结一下,我今天主要有两个观点,第一个,结构决定战略是在市场化程度发育不完全的市场环境下出现的,它是个偶然,但它毕竟是存在的。第二个,我们尽可能要正向地运用这个理论,即战略决定结构,这是对的,这是最终的落脚点,但不能因为理论是对的,我们在实践中就必须去做,对的事情太多了,关键要适用。
杨钢: 这次谈话,我觉得很有收益。第一,大师的话是没错的,结构决定战略还是战略决定结构的问题,就好比钱币的正反面。第二,中国与美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整个经济环境以及管理的成熟度都不相同。第三,中国人的思维是跳跃性的,中国企业的发展也是跳跃性的,也许我们很多思路是超过了他,补充了他的理论。所以,讨论这个话题还是有意义的。我真诚地希望,中国的企业家能够意识到毕竟我们资源有限,要重视财务绩效,首先还是考虑战略、定位,然后建设团队,完善能力、文化、流程的支撑。这才是我们创建一个可信赖的组织的基础。 [题外话] 主题交流之后,大家又在这个话题的启发下,随意讨论了很多其他的问题,“生意和企业”这个题目相对更有意思,作为本次论坛的题外话一并收入。 生意和企业 做生意不等于做企业,做企业需要职业经理人阶层的成熟以及企业家对管理的信仰 王吉鹏: 我有一个观点,做生意不等于做企业,改革开放初期的思维主要是一种贸易思维,本质是做生意,不是做企业。做生意是什么呢?快进快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如果有机会我就多做几年,资产性投入很少,随时可以转型。做生意跟做企业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做生意是做机会,做企业是做能力,差别非常大。 战略能力就是企业能力的一个核心构成。举个例子,我当年在中关村办企业,卖电脑。号称高科技,其实就是倒买倒卖,到深圳那边“走水货”。从IBM的PC机开始的,把电脑散件弄过来,在这边组装,其实就是装个台式机,然后销售,最好的时候一台电脑就可以挣两三万块。当时就是逮机会,有很多人赚了钱。和中关村那批人相比,现在挣多少钱都不算发财。 柳传志也是从做生意开始的,卖旱冰鞋,后来弄个汉卡,实际上汉卡也没挣上钱,他赚钱还是靠做代理,挣钱之后的柳传志就琢磨以后干什么,当时的生意人没人想这个,他决定做电脑。这就是战略能力,因为他在产业上做了选择和取舍。原来是拿着订单,抓贸工技,做贸易的,受汇率影响很大,另外也不可能保证外资厂商永远供货,哪天一掐脖子,就没法装电脑了。现在作技工贸也好、工贸技也好需要加工能力,就要建厂。加工能力有了,发现营销模式整个变了,原来是不需要库存的,也不需要什么推销,拿着订单就装货,现在品控、通道建设、品牌都需要。这样一步步积累能力,成了现在的联想。 西部某投资集团的老板投资了当地省会城市最好的商务写字楼,第一家奢侈品店,投资有色金属,煤矿,还有物流。他的经理们很困惑,他们大都是跟着老板从做贸易开始就在一起的,可是老板觉得他们总是跟不上趟,说他们不加强学习。于是就来找我,我说很简单,就是原来老板是做生意的,把一个煤矿弄过来,本来应该倒手卖给中煤集团或者电力集团的,他应该是把矿作为产品来销售的。但是煤炭行情好,天天涨钱,他不卖了,就变成经营矿山了。原来把企业当做产品来经营的时候,需要的是法律人员、财务人员、投资银行以及资本运作的人,这些人用着很顺手,但是突然经营矿山了,物流怎么控制,铁路怎么打交道,成本怎么算,这些人确实不会。它从一家投资集团变成了产业集团,现在需要积累企业的能力。 杨钢: 还是因为机会市场,很多都是生意人起家,骨子里是生意人,只不过恰巧坐在企业家的位置。除了缺乏战略思维能力,中国现在缺乏成熟的职业经理人,也是生意人老板不能变成企业家的原因。钱德勒在他的名著《看得见的手》中就讲到职业经理人的重要。 慕云五: 钱德勒认为职业经理人阶层成就了美国,和这句话等价的是大企业成就了美国。钱德勒偏爱职业经理人、偏爱大企业,他的结论就是管理资本主义。尹明善的说法可以为您的话注脚,他的话大意是:我不请经理人,或许企业会慢慢死掉,请了会死得更快。 王吉鹏: 可遗憾的是,往往不请也得请,在天津有个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厂,他的老板对我说,本来我想请一个师爷,结果请了一个老爷来。刘永好对职业经理人的评价非常低。他有一次很激动地说,我们中国的企业用最低的平均工资,消耗了最多的人力总成本。代价是企业增长很少,但是对企业破坏力很强。 做企业,有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有些事情你信就好办了,要是不信就麻烦了。战略弄起来是很麻烦的,很多企业都是走到哪算哪。我们给他做战略咨询,他听听而已,从骨子里不相信。我是搞管理的,我信,我干什么都要先定方向,各种因素尽力都想到,想到了然后再做。当初我创办仁达方略,跑完注册,三个月内什么都没有动,没有做业务,我一直在思考,我的盈利模型怎么支撑这个战略,整整三个月的思考,支撑了我们到现在整整10年的经营。 杨钢: 成功的战略就应该这样。 慕云五: 给我们很大启发,看来我们杂志要关注管理信仰教育的问题。 杨钢: 电影《功夫熊猫》其实也在说这个问题,师傅觉得笨熊猫没有可能成为武士,乌龟大师就说最重要的是你信不信他,你相信他一定是负有使命的,如果你不信我也没有办法。师傅逐渐开窍了,他开始信了。信,则生信心,继而有信念,而信念铸就成功。 王吉鹏: 现在很多企业没有把管理作为增长要素之一,他认为是锦上添花,有更好,没有拉倒。还是不信管理。除了信自己,就是信灵丹妙药,我们出去做咨询,他们最希望得到的就是一剂灵丹妙药,今天听了,明天就见效。可是,我这里没有这个玩意儿。再说了,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何必给他,自己做岂不更好。 慕云五: 不仅您没有,德鲁克也没有啊。当年杰克·韦尔奇刚当上GE董事长,向德鲁克求教,德鲁克反而向他提了几个问题,没有灵丹妙药。当然韦尔奇悟性太高,后来就有了只做行业冠军的战略。这个故事在美国《商业周刊》2005年11月纪念德鲁克栏目中特别提到过。 杨钢: 我们的企业家不信管理,也不信职业经理人,其实也是有原因的。我曾经和一个老总聊天,他是台湾人,常年在美国,他的班子都是美国的。他讲了一个小故事,让我突然间醍醐灌顶。他说,在美国如果我有技术,就一门心思把我的技术开发好就完了,可以卖掉,可以办企业。如果办企业,会有人来投资,会很容易找到一个总经理,他也绝不会把我的公司偷偷卖掉,或者干着干着自己另起炉灶。所以企业能做大,各司其职。在中国不行,我有了技术要防着别人偷,最好我自己有钱自己干,自己没钱我要向亲戚借点钱,企业稍微大点了,我干不过来了,招亲戚,亲戚不够了,招外人,这个人进来了,先学,学好了以后,自己出去再做一个小公司,再和你干,永远也干不大。就这么一个小故事,好多东西都在里面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