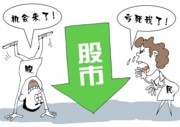就基本规律而言,政策影响股市短期运行当然是有可能的(只是有可能,并非必然);但大的趋势根本不是由政策或某些“有份量”的人意愿决定的。
在中国股市诞生初期,市场规模很小,参与者寡,没有几个像样的机构投资者,更没有QFII或QDII,参与者都带有深深的计划经济思维烙印且都是“新手”,那时的股市对政策比较敏感是自然的。而如今的中国股市,除了不讲诚信、报表造假、拼命“圈钱”、“铁公鸡”等深层次的老毛病尚未彻底根治之外,其他各个方面早已今非昔比。
尤其是,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的融合度与关联度大大提高了,中国股市与外部股市的联动性大大提升了。而且,中国股市的规模达到了世界前列,机构投资者数量及其握有的资金规模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散户不仅数量大增而且也非常关心经济形势和企业效益了,热钱既可推门而入又可翻墙而出了,内资也可以不费力气地出海了。尽管投机氛围依然浓厚,但“价值投机”已成为主流;纯概念投机和纯消息投机所占的份额还是少多了。由于
很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完全用“老眼光”观察中国股市,那肯定是看不懂了。
退一步讲,即便是中国早期的股市,也从未摆脱经济基本面的决定性影响。例如,1992年5月之前的急剧拉升和1993年2月形成第一个大顶,实际上分别体现了1992年初“小平南巡”对中国经济运行所产生的强大推动,以及1993年经济过热之后所迎来的长期经济调整。
1999年的“5.19行情”一直延续到2001年6月。表面看,此轮牛市是新华社一篇“社论”引起的。其实,它是全球网络股泡沫的一部分。而且在“社论”降世之前,中国股市从1997年9月(从那时起指数就没有再创新低)就开始构筑长期底部(即在5.19行情之前,市场用了21个月的时间构筑大底)。从技术指标看,即使当时没有什么“社论”,中国股市也照样会跟随全球“网络股行情”的脚步走出一轮像样的牛市。实际上,在“社论”出笼之前,股市已经开始上涨。由于互联网技术在中国的广泛应用相对滞后,中国股市网络股行情的启动也是相对滞后的。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再想一想:如果“社论”或领导人讲话就能左右股市的话,今年的中国股市还会这么惨吗?
从2001年7月一直延续到2005年6月的大熊市,很多人认为它是“国有股减持”的恐慌引起的,而实际上它是全球“网络股泡沫”破裂的一部分。当然,由于中国股市“网络股行情”的启动相对滞后,“网络股泡沫”的破裂也相应晚一些。同时,由于“网络股泡沫”破裂相对滞后,这轮大熊市最终见底也是滞后的。
2005年7月至2007年9月的大牛市,表面上是“欢庆”股权分置改革“成果”,而实际上它是全球资产价格膨胀的一个局部,同时也得到了企业盈利加速增长的支撑。外围股市的这轮牛市基本上是从2003年中期启动的,当时中国股市从2003年11月到2004年4月也走出了超越2002年“6.24”高点的小牛市。这在技术上已经意味着反转,而且当时的经济环境也足以支撑股市反转,可是上证指数还是从2004年4月最高的1783点下跌到2005年6月最低的998点。
怎么来解释这个现象呢?我的看法是:一个基本面本来可以延续的牛市突然夭折,实际上是因为那时的市场对于即将推出的股权分置改革尚缺乏足够的信心;一旦改革的方向和模式都变得明朗化,市场就立即以报复性上涨的方式追赶全球性资产价格膨胀的脚步。同时,998点实际上含有“10送3”的权益,相当于1300点。从这种意义上讲,市场是有某种“灵性”的(这种灵性,实际上就是“价值均衡”),它并未真正跌破1300点。
由上述可见,过去几年中,“政策”对股市最大的影响,就是股权分置改革操作模式没有完全明朗化之前,牛市的真正“发威”被耽误了一段时间;但在被耽误的这段时间里,指数并未实质性跌破1300点大底。
说到这里,如果仍然有人认为“政策决定股市”,我就得请他回答几个问题:

1.在2001年7月至2005年6月的大熊市中,是否每一次“利好政策”发布,市场都“买账”了呢?哪一次“利好政策”对股市的刺激又不是昙花一现呢?哪一次“利好政策”彻底消除了“熊”性呢?
2.在2005年6月至2007年9月的大牛市中,哪一次“利空政策”(包括提高准备金率、提高利率、提高印花税率)发布对股市的负面冲击不是短暂的呢?哪一次“利空政策”彻底消除了“牛”性呢?
3.今年4月份跌至3000点的时候,也有“利好政策”出台,可股市反弹维持了多久呢?市场的“熊”性被消除了吗?
4.如果政府能救市,中外历史上怎么会有一次又次的经济金融危机?
5.如果政府真的能救市,那么美国政府7000亿救市方案通过之后,其股市为什么不破涕为笑呢?
6.不少人强调,中国政府调控能力强。对此,我不想否认。但是,你能说爆发过或正爆发大危机的美国、日本、欧洲的政府都很笨?
7.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府的调控能力比现在更强,前苏联的政府调控能力可能最强,但当时的中苏政府能消除经济运行大起大落的波动吗?
2007年10月份以来,中国股市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快速、深幅调整,不少人将其简单地归罪于“大小非解禁”。我认为,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和思维方式(详见本博客“大小非解禁不是影响股市运行的本质因素”)。如果观察全球股市的话,你会发现,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尤其是2007年4季度开始,全球的股市都在下跌。越南不存在“大小非解禁”问题,但它的股市见顶比中国还早,调整的深度也毫不逊色。原因是什么呢?是全球金融经济形势发生了历史罕见的大逆转,而且中越两国经济潜在的隐患和股市泡沫度最大。
为什么偏偏是中越两国潜在的隐患和泡沫度最大呢?这个问题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理解:
其一,中越两国都是在保持原有政治制度基本不变的前提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由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借此谋求快速发展并创造了增长奇迹的新兴经济体。这种极其相似的命运和几乎相同的道路必然带来高度相似的问题。突出表现在:过度依赖出口,对欧美经济形势的变化高度敏感;资本账户脆弱的防线阻挡不住“热钱”的冲击;居民长期积累的高储蓄集中释放和货币升值预期,推动股市和楼市疯狂式“繁荣”。
其二,过度依赖外部市场、资本账户开放不慎、货币升值幅度过大、居民长期积累的高储蓄集中释放、市场参与者“赌性”过重,几乎是亚洲“儒教地区”或称“筷子地区”主要经济体共有的教训。日本和“四小龙””早在1990年代就付出了昂贵的“学费”,中国和越南也该有个“补交”的时候吧。
所以,把中国股市仍然看作“政策市”、指望政府来“救市”,实际上是对历史的无知或浅薄解读,是不观察全球的坐井观天,是对股市内在规律的漠视或无知,更是一种肤浅的主观唯心主义思维。当然,“股市运行看政策之类的话”也是一些不研究规律、搞不清规律的所谓“专业人士”自保脸面的遮羞布和永远混迹江湖的护身符。
我一直认为,真正遇到大的危机,政府不能乱忙乎;应从战略层面冷静应对,努力找病根、治病根,为长远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面对百年不遇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中国需要以大国博弈、长远博弈的思维来设计应对策略,而不是局限于常规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同时,在大危机之中,如果政府过度“勇敢”,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可能使自己陷入财政危机等困境。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