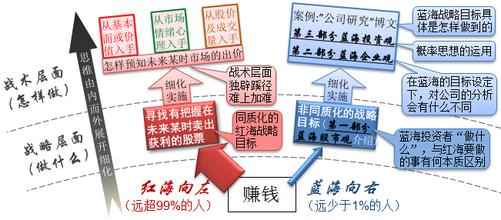文章节选自作者出版作品《制药业的真相》
制药业的巨人们会做些什么呢?只要有可能,它们就会为所欲为。 它不是一台创新的机器,而只是一台巨大的营销机器。我们花的钱一点都不值。美国不能再支撑制药业的现状了。问题在于,制药业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否愿意实行真正的改革来约束自己的胃口,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aihuau.com此话正是描述制药业的。它已经渐渐习惯了为所欲为。1980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它是一个很好的行业,但此后,它成了一个丑陋的庞大行业。从1960年到1980年,处方药的销售额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保持稳定,但是从1980年到2000年,这个比例增至三倍。现在,处方药的销售额每年超过2 000亿美元。而且,从1980年初开始,制药业一直是美国最赚钱的行业(只是在2003年,它在列入财富500强的47个行业中排名降到了第三名)。与该行业突如其来的暴利相关的事件中,没有一件与这些公司销售的药物的质量有关。在本章中,我将带你回顾一下制药业的历史——它辉煌而短暂的崛起,以及即将到来的衰落(或许是一次彻底大检修)的一些迹象。我在本章并不准备深入到细节中去,只是想瞥一眼岩石被举起后下面有些什么东西。那景色可能会不堪入目。开始之前,先介绍一下我在全书中要使用的一些事实和数据。我使用的绝大多数数据是2001年的,因为这是我所考虑的该行业各个方面的数据都较为完备的年份中最近的一年。坚持使用某一特定年份的数据,有利于读者清楚地了解整个局面。但是,对于一些特别重要的事实,我会使用2002年或者2003年的数据。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会指明我所引用的数据是哪个年份的。
我还需要解释一下,当我说这是一个2 000亿美元的行业时,我指的是什么。根据政府的资料,这大致是美国人2002年在处方药上的消费总额。该数字包括消费者直接在药店买药的开支,以及邮购药物定单的总额(不论最后是否掏钱购买了),其中包括了批发商、药剂师以及其他中间人和零售商所赚取的将近25%的价格涨幅。但是,它并不包括在医院、疗养院或是医生诊所里开的药物的价格总额,许多抗癌药也不包括在内。在大多数分析中,这些药费支出都被分配到这些机构的成本中去了。制药公司的收入(或者说销售额)有点与众不同,至少体现在公司年度报告的摘要中。它通常指的是一个公司的全球销售额,包括卖给医疗保健机构的销售额,但是不包括中间人和零售商的收入。或许关于制药业引用最多的统计资料是爱美仕市场调研咨询有限公司(IMS Health)的数据,它估计2002年全球处方药的销售额大约是4 000亿美元,其中约有一半来自美国。因此,2 000亿美元的巨人其实应当是一个4 000亿美元的超大巨人,但是本书主要关注制药公司在美国的经营。读者应该能够理解,大多数的数字要想做到绝对准确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药物到达消费者手中以前,已经经过多级销售渠道,并且支付方式非常复杂,有时还十分隐蔽。如果不知情,那么比较苹果和橘子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在这里,你需要知道,一个数字是否仅仅包括处方药,还是也包括了非处方药以及该制药公司生产的其他药物;它是否包括中间人和零售商的收入;它仅仅是指门诊病人的消费额,还是也包含医疗保健机构的购买额;以及它是否包括邮购药品定单。重现昔日辉煌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的当选可能是大型制药公司崛起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里根政府不仅在政府政策上而且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大力促进商业发展。随着这种政策导向,公众对财富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那之前,人们对巨额财富的态度还有些不屑。你可以选择致富,或者选择做正确的事,但是大多数人认为同时做到这两点是很难的。这一信念在科学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当中尤其强烈。他们可以选择在学术界过一种舒服但是并不奢华的生活,寄希望于能够进行最尖端的科研,或者他们可以选择“下海”,做那些不是十分重要但是报酬优厚的工作。从里根时期开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逐渐改变了论调。有钱开始变得不仅受人尊敬,而且近乎一种美德。商业竞争中有“赢家”也有“输家”,赢家富有被认为理所当然。二战以来不断缩小的贫富差距,突然又开始扩大,到如今差距巨大。政府的很多促进商业发展的举措使得制药业及其首席执行官们很快就加入到了“赢家”的行列中去。有两项举措十分重要。从1980年开始,议会颁布了一系列法案,以促进财政资金资助的基础研究更快地转化为有用的新产品——这一过程有时被称为“技术转让”,目的同样是为了提高美国的高技术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些法案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贝赫—多尔法案》(Bayh-Dole Act),其主要的发起人是参议员伯奇·贝赫[Birch Bayh(D-Ind.)]和罗伯特·多尔[Robert Dole(R-Kans.)]。《贝赫—多尔法案》规定大学和小公司有权为得到国家卫生研究所(NIH)资助的研究成果申请专利,然后将这些垄断性专利让渡给制药公司。到那时为止,财政资助的研发成果还是不受专利保护的,哪家公司都可以用。但是现在大学——国家卫生研究所资助的绝大多数项目都在此进行——可以为其发现申请专利,并且收取专利权税。类似的法规还允许国家卫生研究所自己与制药公司打交道,直接将其发现应用到制药业。《贝赫—多尔法案》极大地推动了新生的生物科技行业以及大型制药公司的发展。许多大学的研究人员为了将自己的发现付诸实践设立了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很快就涌现出了大批这样的小公司。它们围绕着主要的学术研究机构,进行早期的药物开发工作,希望能和大型制药公司达成有利可图的交易,将新药推向市场。通常,学术研究人员及其机构都在其参与的生物科技公司中拥有股份。因此,如果一个大学或者小型生物科技公司拥有的专利最终授权给一家大型制药公司的话,所有的参与者都在财政资助的研究项目上获得了好处。这些法律意味着制药公司不再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新药的研发,事实上也很少有公司这样做。它们在新药的研发上越来越依赖学术界、小型生物科技公司和国家卫生研究所。至少现在大型制药公司所推销药物的三分之一都是大学和小型生物科技公司授权的,并且通常是那些最具创新意义的药物。对大型制药公司和生物科技行业来说,《贝赫—多尔法案》显然是个福音,但它是否给公众带来了福利却是值得商榷的。
里根时期和《贝赫—多尔法案》还改变了医学院和教学医院的风气。这些非营利机构开始将自己视作制药业的“合伙人”,他们变得像企业家一样,急于抓住一切机会将自己的发现转化为财政收益。研究人员被鼓励将他们的工作申请专利(专利将授予其所在学校),并且他们可以分享专利权税。许多医学院和教学医院设立了“技术转让”办公室来操作此事,将员工的发现变成资本。与此同时,医学院的员工也与制药公司建立了其他有利可图的合作关系。后果之一就是医药研究开始重视商用化,而这本是不应该的。早先那些对“虽然清贫但很绅士”的生活方式感到满足的员工们,开始问自己, “如果你真那么聪明的话,为什么你不富有呢?”医学院和教学医院于是就将更多的资源用于那些有商机的研究。
从1984年的《哈奇—维克斯曼法案》(Hatch-Waxman Act)开始,议会又通过了一系列对制药业是福音的法规。这些法规将垄断权扩展到了品牌药中。垄断权对制药业而言,就像人体的血液一样重要,因为它意味着其他公司在一段时期内都不能销售与之相同的药物。当市场垄断权到期之后,复制品(被称为“通用名药”)进入市场,通常价格会下降至原来的20%。药物可以粗分为两种,一种是制药公司经过研究开发新的药物成分,再实施严格的试验,包括动物试验、人体临床实验等,再经过各国药政单位审核之后,才能上市的品牌药(brand drug),又名原厂药;另一种是所谓的通用名药(generic drug),又称副厂药、仿制药,即指品牌药的专利权过期之后,通用名药公司仿造原来品牌药的成分,加上一些简单的临床试验,或直接使用原来品牌药药厂所作的试验资料,而向药政单位申请审核上市的药品,通用名药的好处在于节省了开发新药所需花费的各种动物或临床试验的费用,所以可以大幅降低通用名药的价格,且因为药物成分类似,所以基本有一样的药效。有两种形式的垄断权——由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授予的专利权以及由FDA授予的垄断权。二者尽管相关,但它们一般是独立运作、互为补充的。《哈奇—维克斯曼法案》,以参议员奥林·哈奇(Orrin Hatch(R-Utah))和众议院议员亨利·维克斯曼(Henry Waxman(D-Calif.))的名字来命名,旨在通过绕过FDA对将通用名药推向市场的一些审核流程,来刺激通用名药行业的繁荣。《哈奇—维克斯曼法案》达到了它的预期目标,但由于其中的一些条款被制药业的律师所利用,延长了品牌药的专利权期限,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20世纪90年代,议会制定了其他一些法案,进一步延长了品牌药的专利权期限。制药公司现在雇佣了一些律师团来从这些法规中寻找可利用的空子——这些空子确实非常有价值。其结果就是品牌药的专利期限从1980年的8年延长到了2000年的14年。对某种非常畅销的药物而言——通常指一年内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药物(例如,Lipitor、 Celebrex或是Zoloft)——这多出来的6年时间就像金子一样值钱。它能使销售额增加数十亿美元——足够雇佣很多律师并且还能剩下很多。很自然地,大型制药公司会不惜代价去保护它们的市场垄断权,尽管这样做公然挑战了它们口口声声标榜的自由市场体系。飞上云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制药业的利润暴涨的时候,它的政治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到了1990年,该行业自认为对自己的财富有着空前的控制力。例如,如果它对FDA(本应是监管该行业的机构)的什么规定不满意的话,它就会通过直接施压或是通过议会里的朋友,改变这些规定。十大制药公司(包括了欧洲公司)1990年的销售额包含了大约25%的利润,并且除了克林顿政府提议进行卫生保健改革期间,该比例骤降之外,整个90年代,该比例几乎一直保持不变(当然,从绝对数额上看,当销售额增加的时候,利润额也在增加)。到2001年,在财富500强的名单中出现的十家美国制药公司(与前面提到的世界十大制药公司有所不同,但是它们的利润率基本一致)与名单上其他行业的美国公司相比,其净收益率遥遥领先,销售利润率为185%。这样的利润率非常惊人。相比之下,财富500强中所有其他行业的平均净收益率仅是其销售额的33%。虽然商业银行也是一个十分具有“攻击性”的行业,但是,它排名第二,其销售利润率远低于制药业,为135%。2002年,当宏观经济仍然持续下滑时,大型制药公司的利润率仅仅是轻微地下滑了一点——销售利润率从185%降至17%。最令人惊讶的是,2002年财富500强名单中的十家制药公司的利润总和(359亿美元)竟然超过了其他所有490家企业的利润总和(337亿美元)。2003年,财富500强名单中的制药公司的销售利润率降到了143%,但是仍然比当年所有行业的平均水平46%高出许多。制药业真的很赚钱。很难想象制药公司到底有多少钱。制药业为研究和开发支付的费用,尽管数额也很大,但是与其利润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十大制药公司1990年将销售额的11%用于研发,这一数字到2000年略有提高,为14%。预算表中最大的一项既不是研发也不是利润,而是我们通常所称的“销售和管理费用”——这一名称在不同公司可能会有不同的叫法。1990年,销售收入的36%都用在了这个方面,并且这一比例在接下来的十年内几乎保持不变。要知道,这可是研发费用的25倍呀。这些数字来自制药公司给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及其股东的年度报告,但是这些分类具体包含了哪些内容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制药公司牢牢地将这些信息控制在自己手中。例如,很有可能在研发费用中包含了那些很多人认为是销售的活动,但是却没有人能够明确地指出来。对这些公司而言,“销售和管理费用”就是一个巨大的黑箱,其中可能包括了该行业所宣称的“教育费用”、广告和促销费用、律师费用、以及管理人员的工资——其数字之大令人咋舌。根据一个非营利团体美国家庭(Families USA)的报告,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前主席和首席执行官查尔斯·海姆保德(Charles A. Heimbold, Jr.)2001年赚了7 400多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他价值7 600多万美元的未执行的股票期权。惠氏公司(Wyeth)的总裁赚了4 052万美元,不包括他价值4 063万美元的股票期权,不胜枚举。这是一个有足够的钱来犒劳自己的行业。近几年,十大制药公司中挤进来五个欧洲的制药巨子——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 阿斯利康(AstraZeneca)、 诺华(Novartis)、 罗氏(Roche) 和安万特(Aventis)。这些公司的利润率与它们的美国竞争对手的利润率相似,同样它们的研发费用和销售管理费用也呈现与美国公司相似的特征。此外,它们还是行业商贸联盟的成员,该联盟有一个易让人误解的名字——美国药物研究与制造商协会(PhRMA)。最近我听到诺华公司(Notartis)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丹尼尔·魏思乐(Daniel Vasella)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他对美国的商业和研究环境感到十分满意。他说:“这里有自由定价的权利并且可以没有限额地迅速获准得到创新成果。”除了他迷人的瑞士口音外,这话听起来就像任何一个精力充沛的美国人所说的一样。他的公司现在将研究中心转到了麻省理工学院(MIT)附近,那里有许多生物科技公司,是基础研究的温床。我怀疑它们将研究中心转移到此与所谓的“自由定价和迅速获准”无关,而只是为了从《贝赫—多尔法案》支持下美国财政资金资助的研究中获得好处,以及为了亲近那些做研究的美国医药科学家们。麻烦接踵而至如果说1980年是制药业的一个分水岭的话,2000年可以说就是另外一个——这一年一切都开始向坏的方向发展。当20世纪90年代后期急速发展的经济开始减速的时候,许多成功的企业都发现自己陷入了麻烦中。随着税收的减少,政府自己也遇到了麻烦。一方面,制药业面对经济下滑自我保护得很好,毕竟它们是那么富有和有权力。但另一方面,它又显得特别脆弱,因为它的收入依赖其他公司的雇主们支付的医疗保险和政府运作的公共医疗补助计划。当雇主和政府都陷入麻烦中时,制药业显然不能独善其身。可以肯定的是,在刚过去的几年中,雇主和他们与之签约的私营健康保险公司都开始在药物成本上缩减支出。大多数保健计划组织都开始为得到较大的价格折扣而讨价还价,并开始实行对处方药的三重保险——对通用名药的全面保险、对有用的品牌药的部分保险和对昂贵但药效未必好的药物不予保险。可受保险的药物名单就构成了处方集,它成为控制药物成本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方法。大型制药公司发现这些措施有一定效果,自然地,它们开始熟练地运用这个手段——主要是说服医生或健康计划组织将那些昂贵的品牌药加入到处方集中来。州政府部门也在想方设法缩减它们的药物成本。一些州立法机构正在起草一些规章,以便监管涉及州雇员、公共医疗补助接受者以及无保险者的处方药的价格。同样,它们也正在制定可以享受优惠的药物的处方集。制药业正在通过游说议员的说客和律师团不遗余力地与这些行为进行斗争。斗争从缅因州一直到美国最高法院,最终在2003年,法院支持了缅因州为更低的价格与制药公司讨价还价的权利,但是还有许多细节悬而未决。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我敢肯定它在今后数年仍会继续,并且会越来越引人注目。近来,公众表现出了厌烦情绪。众所周知,美国人在处方药上支付的费用比欧洲人或加拿大人多很多。据估计,大约有100万到200万的美国人通过互联网从加拿大的药店买药,尽管由于该行业的极力游说。1987年议会制定了法案认定除制造商外任何人从国外进口处方药都是非法的。此外,边境居民越来越多地选择乘坐公共汽车去加拿大或者墨西哥购买处方药。这些人多数是老年人,为了购买药物,他们花的钱不仅比邻国的人多,而且比本国的年轻人也多。老年人显然有愤恨情绪,他们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投票人集团——对这一点,议会或州立法机构心知肚明。该行业还面临其他一些不为人知的问题。也许是巧合,事实上,每年的总销售额约合350亿美元的一些最畅销的药物,其专利权将在几年之内陆续到期。这个从顶峰开始下跌的过程始于2001年,当时礼来公司(Eli Lilly)借以一举成名的抗抑郁药百忧解(Prozac)的专利到期了。同年,阿斯利康公司(AstraZeneca)失去了Prilosec的专利,这个治疗胃痛的“紫色药丸”在其顶峰时期曾给公司带来每年高达60亿美元的收入。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失去了它最畅销的抗糖尿病药物格华止(Glucophage)的专利权。近几年内,会有多种药物专利期满,这种现象非同寻常。对制药业而言,这意味着巨大的损失;对个别公司而言,可能是灭顶之灾。2002年,先灵葆雅公司的畅销抗过敏药克拉瑞汀(Claritin)专利权到期之时,该药物的收入占整个公司收入的三分之一。克拉瑞汀现在作为非处方药,价格大大降低。迄今为止,该公司仍无法弥补这个损失,它正试图让克拉瑞汀的使用者去使用Clarinex——这种药与克拉瑞汀本质上完全一样,只不过仍然可以享受专利罢了。更糟的是,当畅销药物专利期满之后,流水线上几乎没有别的药物可以取代它们。这正是制药业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也是它最不为人知的秘密。对公众宣扬的所有创新只不过是为了掩盖这个事实。新药已经根本接不上趟,而且就算是新药也根本没有丝毫创新之处。相反,绝大多数是对旧的畅销药的改造——模仿性创新药。制药公司将生产线进行整合,或是对同种药物进行共同推销,同时不断地从政府、大学和生物科技公司那里攫取获得专利的新药。但是这些源头本身也面临着推出新药的困难。2002年,FDA批准的78种新药中,只有17种包含了新的有效成分,并且只有7种被FDA认为是对旧药有所改进的。剩下的71种新药仅仅是旧药的改造,并且与已上市的旧药相比,疗效不会更好。换句话说,它们是模仿性创新药。78∶7的比例可不算高。此外,这7种中没有一种是美国大型制药公司研发出来的。失去支持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行业巨人感到了自身面临着严重困难。就像该行业的一个发言人声称的那样,它正面临“一场完美风暴”。自然,其利润仍比其他行业高出许多,但是近来确实有所下降,并且对某些公司来说利润下降非常之大。这对投资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华尔街并不关心你今天的利润有多高,它只看你明天的利润会有多高。一些公司的股价已经直线下跌。不过,制药业仍在不断吹嘘其光辉灿烂的明天。它寄希望于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以及遗传学研究的突破能够催生出大量重要的新药。不用说,大型制药公司的创新依赖于政府、大学和小型生物科技公司。这样的预言听起来就像是塞谬尔·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一样,两个男人坐等着某事的发生,不断地告诉对方下一分钟事情就会发生了。尽管我们承认遗传学上的发现会对治疗产生影响,但事实上,从基础研究到制成新药期间要经过许多年。与此同时,大型制药公司曾经坚固的基石正在动摇。随着麻烦不断出现以及公众对高价药物不满情绪的高涨,华盛顿对制药业的坚定支持开始动摇。2000年,议会通过法案弥补了《哈奇—维克斯曼法案》的一些漏洞,并且允许美国的药店和个人从几个药价较低的指定国家进口药物。特别是,它们可以从加拿大回购那些出口到那里的、FDA批准的药物。“再进口”美国市场上已有的药物,这听起来十分愚蠢,但是,即使加上运输成本,这样做也比在美国本土买药便宜。但是,该法案要求美国卫生与公共事业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简称HHS)部长证明这一行为不会给公众带来“额外的风险”,而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的部长们在制药业施加的压力之下,都拒绝做出这样的声明。2003年,白宫提交了一项草案,其中不包括上述规定,有很多保守的共和党人都支持这项草案。众议院议员丹·伯顿[Dan Burton(R-Ind.)]指出他的妻子每个月治疗乳腺癌需要花360美元的药费,而同样的药物在德国只需要60美元,他告诉《纽约时报》,“每一个美国妇女都有权对美国的制药业憎恶万分,你可以在报纸上引用我说的话。”但是,该项法案并没有在参议院上获得通过。制药业还时不时地受到政府的调查以及遭遇民事和刑事诉讼。被控的内容包括非法对公共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收取更高价格、给医生回扣、参与到反竞争活动中、与其他公司共谋阻止通用名药物上市、非法鼓励药物的不正当用途、在广告中误导消费者以及藏匿证据。有些处罚决定十分严厉。例如,制药商TAP由于在其治疗前列腺癌的药物Lupron的营销上对公共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的欺诈,被判处支付8亿7千5百万美元的罚金。本书写作之时,此类诉讼仍在不断增加。所有的这些努力可以总结为制药公司在销售和专利上越来越陷入窘境,打法律擦边球的行为有时正好撞到了枪眼上。制药业如何应对这种行业危机?人们可能会想制药公司应当停止攫取不当利润——降低它们的价格,或者至少使价格看起来较为公正,并且将大部分钱用来研发真正创新的药物上,而不仅是嘴上说说而已。但是,人们希望的情况并没有发生。相反,制药公司仍在重复那些将其推至困境的种种举动。它们开始更加疯狂地推销模仿性创新药,更加不遗余力地加强对畅销药的垄断权,将更多的钱花在游说和政治献金上。至于创新,它们仍在等待戈多。不过,对制药业而言,并非只有坏消息。2003年,医疗保险关于处方药的福利计划获得批准,将于2006年实施。大型制药公司必定会凭空发一笔横财,因为它禁止政府在买药的时候与制药公司谈判价格。该法案通过之后,制药业的股票猛涨,可见该行业和投资者都意识到了这是一笔横财。但是,该法案也只有一个暂时的推动作用。随着成本的上升,议会将不得不重新考虑允许制药公司自己定价。可能还不止这些。制药业看上去就像绿野仙踪里的神奇之地——虽然仍十分嚣张但是现在也显露出了一些与其外表不一致的东西。它不是一台创新的机器,而只是一台巨大的营销机器。它不是自由市场成功的典范,而只是依赖政府赞助的研究和专利权过活的行当。尽管如此,如果单从药物生产和销售的角度来看,它在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中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并且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大型制药公司因为这点贡献而得到了过多的回报。我们花的钱一点都不值。美国不能再支撑制药业的现状了。问题在于,制药业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否愿意实行真正的改革来约束自己的胃口,同时保存自己的实力呢?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