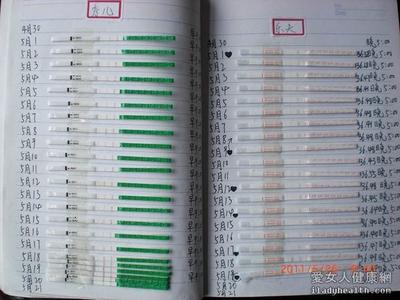乔治·奥威尔在批评西方人的道德局限时,用了一个不错的论证,大意是,如果英国本土突然建了一个苏联式的劳改营,公众和媒体都肯定会炸了锅。然而事实上,这些劳改营在苏联土地上比比皆是,绝大部分英国人却并没有感到太多不快。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西方所津津乐道的民主、自由、和平、人道等大词,中国人眼下正补习得正酣。同时,奥威尔的批评仍旧适用:我们在援引一些巍然不可侵犯的大词时,必须诚实地审视我们的局限,尤其当援引是为了论证现实问题。 奥威尔所述的英人局限,原因我想大致有三:苏联离英国太遥远,信息传播又受限,眼不见为净;苏联再坏也不敢劳改英国人,对普通英国人没有造成实质威胁;苏联劳改营问题太复杂,且早已存在,即使反对也无济于事。 人们对不直接损害自身利益和安全,目测又老大难的问题——即使那问题让无数人家破人亡一般都比较宽容,不好听地说是漠视。毕竟,那是遥远的陌生人,遥远的不公。转发个微博表示声援,可能就是大多数人所能做到的极限了。公允地说,这不能算是一种罪错。人不是神,无法做到全知全能。普通人也没义务把自己活成道德规尺,每天忙于丈量这个世界。但是,至少在一国之内,并不存在绝对的遥远。他人遭遇非法强拆和司法不公求告无门,其他人自认为安全也只能是幻想。更何况,全社会的不公累积得太多又无法有效疏解,肯定就会像洪水一样,在社会的堤坝上随时冲挤出一条缝,或一个缺口出来。 这让对底层暴力的评判变得含糊和困难。袭击幼儿园,纵火公交车之类,因其酷烈野蛮,是非很明显。而对于冀中星这样的,恐怕就不能简单地以是非论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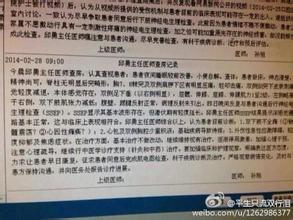
在冀中星的老家,我见到的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很冤”。一个健壮的青年,在26岁时与治安员的一次遭遇,脊椎体受伤骨折致瘫,肚脐以下失去知觉,腿骨骨折都无法察觉。每天大小便,得靠父亲手接手抠。冀中星的口头禅是,“我已经死了一次,还怕再死吗?” 对这样一个连监狱恐怕都怯于收监的人,指责他蠢,批评他坏,有意义吗?那些对冀中星表示同情的人,被一些人批评为“煽动底层暴力”。可不难发现,这种事发后的评判,并不能偷换为事前的煽动。你说我煽动底层暴力,我说你压制底层诉求。大家互相诛心,并不属于有效的讨论。 也有人接着反驳称,对冀中星的同情,将导致其他效仿者。既然将现实演绎带入讨论,那么就回到现实。条件允许的朋友可以去北京南站附近,不允许的可以就近问问老上访户,媒体对冀中星的批评,会不会触动这些上访户,打消他们心中不时涌动的铤而走险的念头?答案很简单。想知道的话,自己去调查下吧。 再回到伦理层面。无论是评判冀中星,还是评判陈水总,都得结合其具体行为。陈水总不用赘言,拿冀中星来说,我个人认为他并没有去首都机场伤害他人的故意。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确实危害了公共场所的安全,尤其是给社会造成了恐慌。而此举激起了公共舆论对其8年来遭的广泛关注,也同样不能否认。 公共讨论却需要基本的准则。当我们使用伦理标准臧否人事时,就不能剪裁地使用事实素材。也就是说,你之前可以不关注东莞治安员和司法问题,但你批评冀中星事件时,不能割裂他的遭遇,不能割裂整个社会背景。进而言之,如果你认可漠视其他人的遭遇无可厚非,那么其他人因此到公共场所,你的面前,或者你的屏幕内做出让你不快和恐慌的事件后,你好像也不能全然把自己当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所以我斗胆说一句,冀中星事件引出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像他这样的人,有无权侵入像机场这种高端场所,逼迫相对高知识高收入阶层,关注他的遭遇。这当然也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我所能确认的是,如果不走出那间弥漫着恶臭的简易房,把事情搞大,冀中星几乎可以注定会在愤恨和抑郁中死去。天下之大,何止一个冀中星呢?当非法强拆遍地开工,当司法不公司空见惯,一部分人的遭遇早已被视作常态—即使不理所当然,也用不着大惊小怪。这一部分人做点什么,却被要求必须考虑全社会的心理安全,对不对先不说,至少这是徒劳的。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