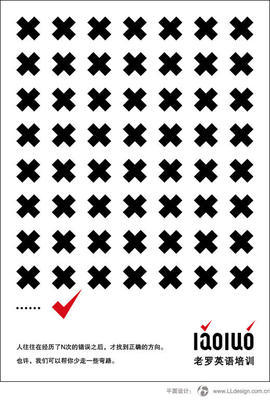众所周知,方舟子是著名的反伪斗士。也许"职业习惯"之故,他对一切"科学发现"几乎都首先持质疑态度,首先要看这些发现是不是假冒伪劣。这本来也是正常的,带有批判性的眼光去观察审视一切,是必须的。不过方舟子的"批判眼光"似乎发展到了"偏激"的程度。比如他对"民间科学研究"的批判就建立在不太正确的观念上。因为在他看来,所谓"科学研究"是有一套形式并且经过严格"科学主义"训练,才有资格进行的,并不是一般人随随便便搞的活动,特别是某些人,形式上说是科学研究,但实质上是借科学研究之名,搞沽名钓誉之实,更值得人们警惕。确实,科学研究具有一套形式上的训练,具有严格的逻辑思维性。但是,科学研究也并不仅仅于此,一切成熟的形式,都是从初级幼稚的形式上发展起来的,我们不应该在获得成熟形式后便反过来指责过去科学的幼稚性、不成熟性,说其是"非科学"的。那么,人类科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我们知道,是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思考中发展起来的,接触自然现象,并且思考它的原因,这就是人类的科学活动,虽然当今人类已经可以依靠各种复杂的仪器设备去发现与思考现象,但这并不等于说,过去和当今的科学活动必须要有复杂的仪器设备,必须要通过某些人制订的一套形式来活动,才算是科学研究。而方舟子的错误则在于此,他认为当今科学研究,只有后者才算是,前者则不算是。这种观念的荒谬性就相当于在一个热爱足球的国家,只有按"正规"形式进行足球比赛的人才算是进行足球运动,其他人热爱足球运动,经常一个人练球就不算是足球运动了。这样的话,就把这个国家热爱足球的全民性运动一概否定了。比如巴西人很热爱足球运动,这种几乎全民性的运动是造就巴西足球强国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个"民间基础",很难想象今天巴西足球王国的地位。没有每个人对足球的热爱,及各种不拘一格的各种形式的足球运动与训练,巴西能产生出世界级球星吗?不可能!而方舟子的错误就在于,他否认这种足球运动的群众基础,只承认在正式比赛中的足球运动是真正的足球运动。对于科学研究道理也是一样,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许多人热爱于探索自然,就不可能造就出科学研究大师。象目前的中国,民众的科学素质仍相当低,一般人基本上不看科学性著作,对科学事件没有什么兴趣。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少数人的"正规"科学研究难以得到人们的理解与支持,人们热衷于各种明星,但却对科学家并不太感兴趣。比如曾有一件事情:中国第一个航天人杨利伟到某地与大学生们见面,一同前往的还有研制"神舟六号"的科学家们,但是令人可悲的是,大学生们只热衷于见到杨利伟,而对科学家们的科学布告没有什么热情。这样的社会氛围对中国的科学研究事业显然是非常不利的。一个国家能够搞出世界一流的尖端科技,并且经常在各个科技领域领先于全球,那是有高素质的国民作为基础的,而不单纯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事情。而"民间科学研究"的意义,正在于它是造就高科学素质国民的活动,这种活动并不一定要具备严格正规的形式,但它却具有科学行为的根本意义,即:对大自然的探索兴趣,喜欢留心观察自然现象并且追究其中原因。这样的活动,能够造就人们的科学精神,即凡事都要追究其中的客观原因,凡理都要具有客观根据。如果中国人具有这样的科学精神,那么某些邪教的东西就不会得到广泛传播,假冒伪劣就不会如此猖狂;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邪教很容易传播,假冒伪劣商品泛滥,那么就说明人们的科学精神还很不足,还很薄弱。而象方舟子那样,以科学研究需要严格形式与训练为由,将广大民众的科学活动完全排斥在外,那正好给予伪科学以生存的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方舟子的作为,不是在消除邪教,反而无形中助长了邪教的存在与流传。今天,经济与社会领域的信息不对称如此严重,假冒伪劣商品仍然难以杜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民众缺乏相应的科学素质与科学精神,没有起码的能力观察与审视到这些坏东西。而"民间科学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提高民众的科学素质,创造他们的科学精神,使他们能够以科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与世界。
所以,方舟子应该说:民间科学研究应该鼓励,但对借科学研究之名搞沽名钓誉之实,败坏科学研究名誉的行为,应该根据科学精神加以严厉批判!附1:
"民间科学研究"应该鼓励吗?
·方舟子·
科学家本无所谓官方和民间之分,国内媒体经常提到的"民间科学家"其
实应该称为"科学妄想家"更合适,指的是一些在科学共同体之外的业余研究者,没有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又不屑于从事像采集标本、观测天象之类小打小闹的业余科学爱好,而是固执地相信自己做出了重大的科学发现,比如证明了歌德巴赫猜想之类的重大数学难题,推翻了相对论、进化论之类的重大科学理论,提出了玄之又玄的"科学理论",发明了永动机等等。这种人在国外自然也有,但是中国如此众多,恐怕就是绝无仅有了。以前在大学、研究所门口经常能见到他们热情推销的身影,而现在在网络论坛上,更是充斥着他们狂热的声音。专业的科学工作者因为对科研研究的方法、规律和现实有切身的体会,深
知在科学事业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业余研究者要做出重大发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对这些"民间科学家"大抵持否定、冷淡、蔑视的态度,最多觉得可怜。当然例外总是有的。比如,"民间科学家"去年11月份在长沙开了一次"全国民间科技发展研讨会",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应邀出席捧场,并声称自己也是"民间科技研究者",虽然我不知道从农学院毕业,并一直在农校、农科院搞农学研究的袁院士究竟"民间"在何处。一些人文学者的态度则相反,他们由于对科学研究缺乏第一手的了解,并
且由于人文学科的专业性不像科学那么强,业余研究者有时也能独创新论,这使得他们对陌生的科学研究也抱有一种浪漫的想法,支持、赞赏"民间科学家"的所作所为,甚至表示"敬意",并且呼吁要"鼓励民间科学研究"(梁子民、毕文昌《鼓励民间科学研究》,《中国青年报》2006年1月11日)。据说"现代科学研究体制建立以后,如果对民间科学研究不能持理解和宽
容态度,对于科学发展是不利的",但是对如此重大的命题,却没有见到具体的论证,好让科学共同体明白为什么科学发展离不开"民间科学家"的贡献。中国"民间科学家"人数之多可谓世界第一,也没见中国的科学发展也是世界第一。有人举山西农民王衡因发明地下工程水害防治新技术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为例说明民间科学研究的重要性,乃是把技术发明和科学研究混为一谈了。有些技术发明并不需要用到高深的科学知识,靠长期的摸索、经验累积甚至灵机一动也可以做到,如果要鼓励的是"民间技术发明",恐怕没有什么人会反对。经常被拿来为"民间科学家"鼓气的另一个不幸人物是爱因斯坦。且不说
动不动就拿爱因斯坦这种一百年也未必能出一个的天才人物说事很不地道,爱因斯坦也不是什么"民间科学家"。爱因斯坦既是天才,也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他大学上的是著名的苏黎世工业大学物理专业,导师是大物理学家韦伯。大学毕业后爱因斯坦想要留校任教,未能如愿。为了养家糊口,不得已先暂时当中学数学教师,后又去了伯尔尼专利局当职员。1905年,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工作期间,"在职读博",完成一篇物理学论文,获得了苏黎世大学的博士学位。同年发表了狭义相对论。1908年爱因斯坦成为伯尔尼大学的讲师,第二年正式辞去专利局的工作,担任苏黎世大学物理学教授,从此回到学术界。可见爱因斯坦在专利局的工作,只是其学术生涯中一个短暂的小插曲而已。批评"民间科学家"的人大概没有人主张要以思想定罪、禁止"民间科学
研究",所以"民间科学家"的支持者大谈什么思想自由,纯属无的放矢。但是,我们应该在法律上宽容"民间科学家",却不应该在学术上也宽容他们。在学术上科学家们彼此之间也相互不宽容,为什么要特地去放民间科学家一马呢?他们既然自称在研究科学问题,那么人们当然也应该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其研究。有人说这是"科学主义",莫非想说对科学问题不用科学的标准,反而该用玄学的标准?更有趣的是,还有这么要求人们宽容荒谬的:"荒谬挑战科学的勇气,在
知识上也不是毫无意义,科学澄清了荒谬,更能显示科学的力量。"按照这个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罪犯挑战警察的勇气,在社会上也不是毫无意义,警察肃清了罪犯,更能显示警察的力量?"民间科学研究"也不是完全无害的。"民间科学家"往往过于痴迷而影
响了个人和家庭生活,这且不说,他们往往还具有受迫害情结,利用各种机会控诉科学界如何压制、迫害他们,甚至号称科学界在制造"冤案"。这种声音如果被媒体放大,获得人文学者的支持,民间科学家真被当成了挑战黑暗的科学界的"英雄"、"烈士",让公众对科学界产生误解,难道不是一种会影响科学进步的社会公害?前沿的科学研究是最具专业化的。如果有人认为科学研究人人可做,号召
人人搞科研,大跃进便是前车之鉴。2006.1.12.
(北京科技报2006.1.18)
附2:
双城记鼓励民间科学研究2006年01月11日中国青年报
梁子民 毕文昌
梁:2004年,山西万荣农民王衡,以地下工程水害防治新技术获得国家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曾经轰动一时。他发明的产品和技术已在国内上千项工程中得到应用,至少为国家节约资金11亿元。但他的研究历程,十分艰难,最终能获奖,得益于几位院士的推荐。我经常听到关于民间科学工作者的一些遭遇,主要是他们的研究工作得不到专业科学人员的理解和评价。现代科学研究体制建立以后,如果对民间科学研究不能持理解和宽容态度,对于科学发展是不利的。我觉得,当今的主要问题是,受过严格科学训练掌握科学研究裁判权力的专业人员,应当对民间科学研究者多一点理解和同情。不能动不动就以严格的科学规范和学术训练为理由,来打击民间科学研究者的探索热情。
毕:所谓民间科学研究者,也就是非职业的科学研究者。他们大概有这样一
些特点:第一,对于探索未知世界有强烈的热情。第二,这些人一般属于偏才。第三,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依靠自学,对于自己的研究非常执著;或受过高等教育,但努力方向却并不在他所学的专业方面。第四,他们的研究完全是出于兴趣而不是功利。体制内的专家,往往从学科的角度,对他们的研究持保留意见。这本来不奇怪。问题在于,对他们探索科学的热情,往往缺少必要的宽容。梁:民间的科学研究者,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个人愿意为此投入一生的
精力,对社会一般没有坏处。只要他的研究不涉及欺诈,不触犯国家法律,不违背公共道德,就属于私人生活领域。在现行体制下,他们一般没有机会得到政府财政和研究经费。涉及欺诈,以研究名义敛财,是另一回事。只要没有以科学兴趣换来超值的物质利益,就算他们的研究方向和方法错了,也不会危害社会。对他们的探索精神,不妨抱以宽容,乃至几分敬意。毕: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的时候,也不是专业科学家,而是一个政府小职员。
他是先有成就,后进体制。当然,民间科学研究者成功的概率是极低的,但再低,也没有坏处。就是对那些痴迷发明永动机、推翻相对论等的想法的民间科学研究者,也不必简单地嘲笑和打击,只要是在知识领域,保持荒谬观点,也是个人的选择权利。近代科学体制完善后,成为强大的主流知识。但科学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知识问题,只要对知识真诚,就应当理解。就是所谓愚昧,也要看是不是对他人构成危害。退一步说,荒谬挑战科学的勇气,在知识上也不是毫无意义,科学澄清了荒谬,更能显示科学的力量。或者说,就是毫无意义,一个文明的社会也应当理解他们探索知识的兴趣。梁:我接触过一些科学工作者,他们说起伪科学,总很气愤,有一种必欲置
之死地而后快的劲头。我也主张尊重科学,不赞成伪科学。但在尊重科学之上还有一条更重要的价值,就是思想自由。你可以批评不科学的观点,但不能剥夺人家发表不科学观点的权利。毕:从民间科学研究者这一方面来说,也要给自己正确定位。在科学探索中,
民间明显的弱势地位是一个铁定的事实。所以民间科学研究者,也不必轻率地向主流挑战,不要急功近利,要从长计议,争取获得主流的承认。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殿堂里的位置,只留给对科学保持高度兴趣的人。当然,他们一般是执著的偏才,要求他们的心态永远保持理性,有时是一种苛求。再者,我们也不能以科学主义判断一切。在近代严格的科学体制完善后,更要对知识发展的多种渠道有一些理解。我记得张东荪早年在《知识与文化》一书中,有一个思路很清楚。他把人类的知识分为三种:一是常识的知识,二是科学的知识,三是玄学的知识。这三种知识系统各有它们的特性。现在常见的是用科学的知识系统,去讨论玄学的问题。因为这方面涉及信仰和宗教问题,其实是不同的知识体系。在不同的知识体系当中找到相互理解的地方,还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梁:今天强调鼓励和宽容民间科学研究,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体制内的科学
研究工作者要对体制自身的弱点有一种自省。前些时候,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在中国科学与人文论坛上说:现在从应试教育到应试科研,整个体系抹煞了个人创新能力。一个国家级的成果申请下来,要脱几层皮,只有到了一定的年纪,获得一定的学术地位,才有可能突破这种限制。但是,这个时候人的创新能力,已经与年轻时不可同日而语了。正当年富力强时,忙于应试;等到应试过了,年龄已大,成为强弩之末,力不从心。那么,中国的科技创新靠谁去?毕:现在,政府对科学研究投入的经费越来越多。与不花纳税人的钱的民间
科学研究相比,体制内科学研究的投入和产出是否成正比,也是一个大问题。正因为体制难以避免秦院士所说的这种弊端,来自民间的挑战才不容忽视。 爱华网
爱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