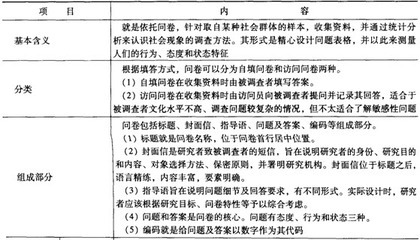征税是一个合法政府的基本权利。几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皆以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农业税赋之轻重一直是史家评说功过的重要标准之一。西汉文帝前十三年免田租,并将汉朝税制减半定为三十税一,由此开创四十年的“文景之治”赢得千古美誉。世易时移。公元2004年,中央政府刚作完5年内全面免征农业税的承诺,节前就有25个省市自治区应声而动,取消了农业税。这意味着什么?农业税收在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已经微不足道了,我们俨然已经进入工业社会。2004年开始的新一轮以“三农问题”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开启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 “三农问题”决不仅仅是个税收的问题,减负只是一小步,取消农业税可以说只是一个契机,是一个启动农村社会转型的机会。“三农问题”事关我国9亿农民的切身利益,也是我国进一步发展壮大面临的重要挑战,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非凡的智慧,我们将一直予以关注。对于化解三农难题而言,决不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如此简单。“黄老之治”的思想只是恢复农村生机的前奏,农村要想尽快缩小与城市间的差距,必须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实现转型。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角度出发,首先就应该理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和职能分配,把那些市场可以完成的职能剥离出去,交给市场来办。
2004年全国农民平均收入在八年之后再次实现两位数增长,“政策好、人努力、天帮忙”,成为农民增收的三大法宝。而好政策则是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新一轮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发轫,政府做出五年之内逐步取消农业税的承诺。去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是促进农民增收,今年则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两个文件最后都是落在要使农民富起来,缩小城乡差距,以化解三农难题。“减轻农民负担”提了很多年了,但庞大的基层政权设置,以及各种名目的“搭车收费”依旧让农民不堪重负,这也是前几年税费纠纷严重,以至于最后不得不启动税费改革的重要原因。农业税全面取消的政策效果固然很明显,但是一系列新的问题也接踵而至。对于化解三农难题而言,决不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如此简单。“黄老之治”的思想只是恢复农村生机的前奏,农村要想尽快缩小与城市间的差距,必须经历一场深层次的变革,实现转型。这个转型既包括农村自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也包括农村基层政权的转型。而后者对于未来的中国社会的建构和发展,则具有尤为特殊的意义。改革开放发韧于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在农村渐渐成型。取消农业税之后,基层政权———包括县乡两级政权以及村自治机构将面临巨大的财政和人事压力。有压力就有动力,这将是个契机,把政府职能的重心从经济建设转变到公共服务上来,通过发展农村社会,缓解农村官民矛盾,消除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均田地、轻税赋”是中国农民几千年的梦想。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上,政府收缴农业税、农民交纳农业税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各朝各代,只有过局部减轻包括农业税在内的税赋的举措,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先例。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取消农业税几乎可以算做是中国自盛唐之后关于税制的第四次重大改革。但是这第四次改革与前三次改革相比,具有本质性的差异。中国古代专制政权的经济权力,归根结底是建立在田制税法上的。秦代以后,每个王朝在田制税法上就进行着各色各样的斗争。譬如在魏晋时期,就先后出现曹魏的屯田制、晋代的占田制、北魏乃至其后隋唐的均田制。唐室建立之初,其中央集权的物质基础就是均田制和租庸调税法。这之前的传统税法一般只与人口挂钩,所以唐德宗元年,也就是公元780年,由宰相杨炎建议推行的两税法,由于确定以资产、田亩为课税对象,变相承认了地主和一些农户的土地所有权流转,以户税和地税来代替之前税法,实际上是此前由国家统制土地分配的规制,从根上取消了,因此,两税法可以说是对中国此前税赋征收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另一意义则在于,土地私有和土地所有权流转在事实上被政府承认。第二次则是明朝后期的“一条鞭法”。公元1581年,张居正把人头税、财产税以及各种杂税全部归到土地税里,统一征收。我国于2000年开始的税费改革试点,应该说,也能窥见一条鞭法的影子,譬如,取消“三提五统”,也就是国家规定的村提留(包括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五统筹(包括教育附加、计划生育费、优抚费、民兵训练费、乡村道路费),以及各种杂费,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义务工,建立以税率提高的农业税以及农业税附加为主体的农村税制,即所谓“费改税”,实际上就是与一条鞭法如出一辙。但是一条鞭法到了后期,出现了“黄宗羲定律”,各种收费在一段时期过后,又重新以各种名目收取,税增加了,费并没有减少,农民需缴纳的负担实际与改革前并没有太大区别,而且多数会更严重。从征税费成本上来分析,地方政府在征收“皇粮国税”时,往往会附加收取“费”,最后甚至可能演变成以征费为中心,征税为附属物的局面。取消农业税后,那些原本以征收农业税为名义而进行的收费行为,不得不改弦更张,这将有利于农民算明白账。第三次改革是雍正元年实行的“摊丁入亩”。1723年,雍正将丁税也就是人头税平均摊入田赋中,征收统一的地丁银,土地多的交税多,土地少的交税就少。“摊丁入亩”废除了编审制度,解除了许多世纪以来加在农民身上的一条锁链;政权通过赋役制度实现的人身控制削弱了;数千年的人头税基本废除。第四次重大改革即为当前正实施的税费改革,其主要政策即在“费改税”的基础上,再进一步,逐步取消农业税和除烟草之外的农业特产税。从去年3月国务院宣布5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在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11个粮食主产省区的农业税税率降低3个百分点,其余省份农业税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鼓励沿海及其它有条件的省份先行改革。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全面停征农业税。此外,中央政府从今年起免除全国59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农业税。
农业税取消之后,实际上,从税费改革试点开始,我们就发现,乡村两级的收入大大减少,加上财政转移支付滞后,导致了乡村基层机制运行面临困难。这个困难的典型表现就是财政来源问题。中国目前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在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下,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层层包干,收支层层是平衡的,中央负责中央,地方负责地方。但从1994年税制改革以后,“好税”、利大的税向上收,“坏税”、利小的向下放,财权上收了,事权就下放,其结果是越到基层,事权越大。而我国的乡镇一级政权有相对独立的财政,这就导致他们必然要寻求变通之道,也就是通过运用事权重新加强财政能力。举个例子,农业税没有办法征收,他还可以征收计划生育费,宅地费等,而征收标准,如何征收仍然是基层政府说了算。在我国县乡两级庞大的政府机构没有大的变动下,取消农业税,必然进一步加重地方财政危机。其一,乡镇机构精简下来的人要买断工龄,这部分钱只能从财政中开支;其二,吃财政饭的教师队伍也仍然由县乡财政出钱,这部分所占比例在很多地方超过乡镇财政总额的50%;其三,乡镇政权仍然在进人,尤其是新分配来的大学生、大专生,这也是干部年轻化、专业化的需要,这部分人也要吃财政饭。新旧干部加在一起,财政负担在有的地方不减反增。
另外一个因素是债务危机。前几年经济开发区等兴起,县乡政权为谋政绩,纷纷搞基建,圈地建开发区等,这些由政府主导的经济行为,不仅造成了大量资源浪费,而且由于不少是向银行贷款或是向私人借款,欠下了很多债务。再加上一些历史遗留,基层政权的负债现象已经十分突出,取消农业税之后,债务偿还能力更加虚弱。在村一级,多年来农村兴办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村基金合作会、农业开发等生产公益事业,以及兴办工商企业等原因也形成了乡村大量负债现象。农村税费改革前,乡村除从经营性收入外还要从收上来的“乡统筹、村提留”中拿出一部分来偿还债务。改革后,乡村可用财力下降,筹资数量和筹资数额减少,偿还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偿债压力非常大。目前在中西部地区,平均每个乡债务是500万,典型的乡超过1000万。据称,现在全国每个乡的平均债务是400万,村级是20万到100万不等。平摊到每个村民的人头上,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些财政和债务危机如何化解?在取消农业税和除烟叶之外的农业特产税之后,上级财政必须拿出办法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加快速度,否则,基层政权会通过不断变通的新方法来自行解决这些危机。那么,这就很容易走向税费改革本意的反面,重新加重农民负担。当然,另外一个措施就是基层政权自身的转变,取消农业税,消除基层政权以前较为核心的征税职能,正好给基层政府改革以一个新的契机。
我国即将取消的现行农业税制是1958年税制改革时建立的。我国的农业税是对从事农业生产取得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取得的常年产量或实际收入所征收的税,是对总收益额征税。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民缴纳的税费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期积累。近年来,随着工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税在国家财政中的比重逐步变小,全国财政收入中来自农业税的收入从1950年的41%下降到去年不到1%,充其量不会超过两百个亿,而去年的财政收入为26000多个亿。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到现在,取消农业税,反哺农业,作为我国总体经济战略性的一次大调整,也是水到渠成。农业税取消之后,中央财政还要在几年之内对农业继续扶助。中央领导人去年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时代已经来临,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指望企业法人对农业进行反哺不太现实,只有动用计划的手段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如果没有政策扶持,基于经济人理性,企业家不会主动去“献身农村”,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理想主义情绪只能是一种情怀,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让农民富裕起来的目标。因此,反哺的重任只能也只有政府财政才能承担得起。基于长期政策的考虑,城乡在未来统一税制是一条公平之路。农业税取消之前,城乡征税制度几乎性质完全不同。同样收入程度的两个中国人,由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身份之差,前者可以享受低保,每个月定期领取政府补助,而后者不仅无钱可发,还要缴纳税费。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基本上是生存性收入,包括口粮、种子、化肥、农药、看病、小孩上学都需要这部分农业产出,这种生存性收入按照国际惯例是不应收取税收的。关键的一个差异就是我国过去对农民不是按照收入水平来收税,而是以产量和人头来定量收税。这就造成了严重的城乡税制的不平等。然而,城乡统一税制不可能一蹴而就,现今时机尚不成熟。原因在于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需要几年的调整期。这也与农民总体收入水平紧密相连。以收取个人所得税为例,城里把800元作为起征点,工资卡上有注明,征税成本电子化,低廉快捷;而在农村,如何量化这个标准,一时都不好界定,何况,即使农民个人月收入超过800元,考虑到在农村约20%的征税成本,亦是“吃力不讨好”,且作为反哺时代的一种策略,也应该使这种对农民好不容易得来的税收福利持久一些,这其实就是以现今看似不公平的措施纠偏,以达到历史性的公平。

取消农业税的基本思路是,在农业生产环节一律免征,只对进入流通和消费环节的农产品征税,也就是说农产品不上市不征税。对上市的农产品征什么税,是征农产品税,征营业税,还是增值税,这是另一个大课题,有待纳入城乡统一税制的历程中加以衡量。统一城乡税制,最终还是要对农民征税。这主要是对富裕起来之后的农民征税,农民有缴税的能力了,该缴的仍然应该缴,不然这种政策的差异会引发大面积征税作弊现象,造成国家财政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但这至少需要几年的过程,如果马上统一城乡税制,恐会抵消取消农业税所带来的政策效应,影响农村政治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税制的转型对于未来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转得好,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坚冰,转得不好,又会孳生新的社会问题。但无论如何,统一城乡税制,消除歧视性政策,稳定农村福利,都是一条必经之路。
假如取消农业税的政策完全落实,据估测,农民因此将人均减负40元。考虑到城市整体经济发展速度仍然远高过农村的现实,这40元所带来的更多的是政治象征意义,而对于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因此,光取消农业税是远远不够的。免征农业税后,基层政府不再担当收税的职能,县乡两级政府空闲出大量精力,正好可以腾出手来着力促进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只有这样,取消农业税所增加的40元收入才能引发“乘数效应”。农民并非不需要政府,而是需要为他服务的政府。在农村搞“无政府主义”,并不利于农村的整体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对农村的引导。“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是中央政府提出来需要加强的四大职能。从总体上看,目前乡镇政府职能特点是仍然以经济管理职能为主体,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相对较少,而且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这些职能还难以有效履行。这种状况已经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中国社会转型的要求,应当充分利用税改的契机,加以改革。怎么改革?从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角度出发,首先就应该理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和职能分配,把那些市场可以完成的职能剥离出去,交给市场来办。比如说对乡镇七站八所中的农机站、种子站、兽医站等都可以独立出去,让他们在市场机制中靠满足农民需要来存活。第二,公共服务的一大块就是为农村提供公共品,包括公共医疗,水利、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等。目前农村公共品供给主要是以农民为主,国家补助的模式,因而供给出现严重缺位,也就是政府的缺位。对于公共品,农民需要,但又没有充分的实力和精力来从事,取消农业税和义务工后,如何整治农村的公共品更成为困扰农民的一道难题。因为这涉及到各个村庄之间的协调问题,政府出面是最有效率的解决方式。而且,这部分公共品,譬如纯公益性的,就应该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来做。学界有人提出要裁汰乡镇政权,其实质是没有看到农民对政府的需要。裁汰冗员、精兵简政当然是条明路,但更根本的还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为民服务。农民没有道理不欢迎以民为本的公仆式政府。经济的转型首先是税制的转型,政府的转型则以职能的转变为突破口。2006年作为中央确立的改革年,中国农村在税制改革和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上应有新举措。
 爱华网
爱华网